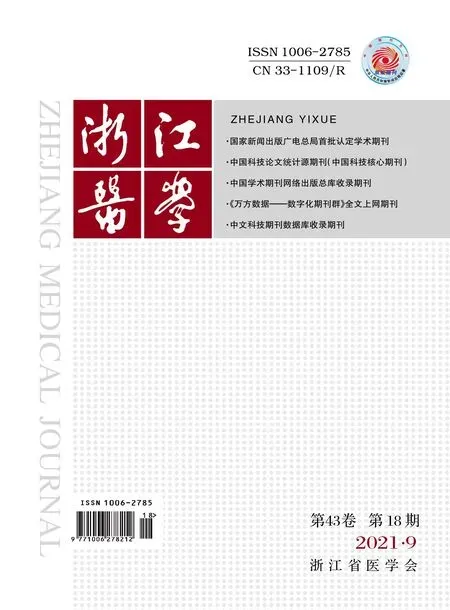二代测序辅助诊断鹦鹉热衣原体肺炎3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邱晨辉 叶健
例1男,45岁。因“头昏乏力5 d,行走不稳伴言语含糊3 d”于2019年2月19日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患者5 d前出现头昏思睡,伴乏力纳差,3 d前起床时家属发现患者言语含糊,伴行走不稳,并出现腹泻,当天解4次水样便,偶有咳嗽,咳白色黏痰,当时未重视未就诊。2 d前言语含糊、行走不稳症状加重,至当地医院就诊,予以抗感染补液后上述症状无明显好转,遂转至本院。既往无基础疾病史,查体:体温:34.9℃。神志清,言语含糊,双侧瞳孔0.25 cm,对光反射灵敏,双侧鼻唇沟对称,伸舌不偏,颈软,四肢肌力5级,肌张力正常,腱反射对称(++),巴氏征(-),肢体痛觉无减退,指鼻试验正常,心脏听诊无殊,左下肺可闻及少许湿啰音,肝脾肋下未及。辅助检查:2019年2月19日头颅MRI:胼胝体压部小片状异常信号,胼胝体压部脑白质病可能;胸部CT检查:左下叶肺炎(图1a-b)。腰穿脑脊液检查:脑脊液生化,蛋白42.2 mg/dl,葡萄糖6.75 mmol/L,氯化物125 mmol/L。脑脊液常规:潘氏试验阴性,脑脊液红细胞5 U/L,脑脊液有核细胞1/μl。血生化:ALT 75 U/L,AST 162 U/L,尿素 5.15 mmol/L,肌酐 122 μmol/L,β- 羟丁酸 682 μmol/L,肌酸激酶(CK)11 480 U/L,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145 U/L,乳酸脱氢酶 928U/L,血淀粉酶136 U/L,钠126 mmol/L,钾 2.83 mmol/L,氯 94 mmol/L,降钙素原0.15 ng/ml;动脉血气无异常。
入院后予以头孢哌酮舒巴坦针2.0 g,静脉滴注,1次/8 h经验性抗感染,并送检痰培养、血培养,治疗3 d后患者体温最高仍有40.1℃,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患者病情重,难以耐受支气管镜检查,予以抽血送宏基因二代测序(metagenomic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检查,复查胸部 CT(图1c-d):左下叶实变影,较 2019年2月19日胸部CT明显进展,仔细询问患者及家属得知有活鸡活鸭接触史,改用左氧氟沙星针0.5 g,1次/d覆盖非典型病原菌。2 d后mNGS报告提示:检出鹦鹉热衣原体序列数3;继续予以左氧氟沙星抗感染,患者体温及炎症指标逐渐下降,ALT、AST、CK、CKMB 恢复正常,头昏乏力症状消失,体温恢复正常,治疗10 d后顺利出院。嘱继续左氧氟沙星片0.5 g,1次/d口服治疗1周。1个月后当地医院复查胸部CT,两肺实变影基本消失,炎性渗出基本吸收。

图1 例1胸部CT检查所见(a-b:入院当天胸部CT检查提示左下肺实变渗出影,炎症考虑;c-d:入院4 d后胸部CT检查见左下肺实变渗出较2019年2月19日增多)
例2男,48岁。因“发热1周,胸闷5 d,咳嗽2 d”于2020年9月19日入本院。患者1周前着凉后出现畏寒、发热,伴乏力,自行服用布洛芬分散片退热治疗。5 d前逐渐出现胸闷气促,2 d前出现咳嗽,咳少量白色黏痰,不易咳出,时伴心悸,遂至当地医院就诊,胸部CT检查:右肺下叶大叶性实变。考虑社区获得性肺炎,予以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3.375 g,1次/8 h联合左氧氟沙星针100 ml静脉滴注抗感染、磷酸奥司他韦抗病毒、甲强龙抗炎、止咳化痰等治疗,症状无好转,转至本院。患者发病以来饮食、睡眠欠佳,体重下降7.5 kg。既往无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病,3年前摔倒后右足骨折,行骨折内固定术,现已痊愈。养鸭3年余。入院查体:血压:90/63 mmHg,体温:37.1℃。两肺呼吸音粗,右肺可闻及湿啰音,心脏听诊无殊,肝脾肋下未及,神经系统检查阴性。辅助检查:血气分析:pH 7.44,PCO230.50 mmHg,PO255.0 mmHg,剩余碱 -2.5 mmol/L,动脉氧饱和度90%。血常规:WBC正常,中性粒细胞96.2%,CRP 276 mg/L,降钙素原21.944 ng/ml。血 生 化 :ALT 82 U/L,AST 197 U/L,CK 501 U/L,肌钙蛋白0.45 μg/L。2020年9月19日胸部CT检查(图2a):两肺多发感染性病变,两下肺为主。两侧胸腔少许积液。B超检查提示肝脾肿大。
入院后考虑患者病情较重,外院多种抗生素治疗效果欠佳,选用美罗培南1.0 g,1次/8 h抗感染,患者血气分析提示Ⅰ型呼吸衰竭,予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high-flow nasal cannula oxygen therapy,HFNC)治疗,3 d后患者体温仍高,感染症状无明显改善,同时呼吸困难加重,复查胸部CT(图2b):两下肺实变渗出影,较2020年9月19日CT明显进展。由于患者病情进展迅速,予加用万古霉素针1.0 g,1次/12 h静脉滴注抗感染,同时抽血送mNGS检查,次日报告提示:检出鹦鹉热衣原体序列数64。停用美罗培南和万古霉素针,改左氧氟沙星片0.5 g,1次/d联合口服多西环素0.1 g,1次/12 h抗感染治疗,患者病情逐渐好转,2020年9月28日复查胸部CT(图2c):两肺多发感染性病变考虑,两下肺为主,较2020年9月22日好转,部分趋间质改变,两侧胸腔少许积液较前吸收。7 d后患者再次复查胸部CT(图2d):两下肺感染灶较2020年9月28日明显吸收,未见胸腔积液。顺利出院,继续左氧氟沙星片0.5 g,1次/d联合多西环素0.1 g,1次/12 h口服治疗2周,目前随访患者病情稳定,未再复发。

图2 例2胸部CT检查所见(a:入院当天胸部CT检查提示两肺多发感染,两下肺为主;b:入院3 d胸部CT检查提示感染较入院CT明显进展;c:多西环素联合左氧氟沙星片治疗4 d复查胸部CT,提示右肺感染略所吸收,部分趋间质改变,左肺感染吸收;d:联合治疗10 d复查胸部CT,提示双肺感染灶明显吸收)
例3男,53岁。因“左下腹痛半个月,发热5 d,咳嗽2 d”于 2019年 12月 11日入本院。患者半个月前出现左下腹痛,呈阵发性钝痛,程度可忍,未行治疗。5 d前患者出现发热,最高体温39.6℃,伴畏寒寒战,仍未治疗。2 d前出现咳嗽咳痰,无发热,来本院就诊,家中散养鸽子数年。入院体检:脉搏:69 次 /min,呼吸:19 次 /min,血压:95/63 mmHg,体温:39.2℃。神志清,精神软,皮肤无黄染,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2.5 mm,对光反射灵敏,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湿啰音,心律齐,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软,未见腹壁静脉曲张,未见肠型及蠕动波,左下腹压痛,无明显反跳痛及肌紧张,肝脾肋下未触及,神经系统查体阴性。辅助检查:血常规 WBC 4.5×109/L,中性粒细胞83.3%,CRP 142 mg/L;ESR 35 mm/h;血生化:ALT 72 U/L,AST 47 U/L,总胆红素30.2 μmol/L;降钙素原 0.8 ng/ml。
入院后予以头孢曲松2.0 g,1次/d静脉滴注抗感染治疗5 d后,患者仍有高热,查胸部CT(2019 年12月14日,图3a-b):右肺下叶大片实变影;复查血常规WBC17.3×109/L,中性粒细胞 95.2%,CRP 71 mg/L,提示抗感染效果不佳,予支气管镜检查(图4):常规镜下未见异常,径向超声探头见右肺下叶外基底段探及低回声区;并行支气管镜肺活检(transbronchil lung biopsy,TBLB),取肺组织送检mNGS;TBLB病理提示肺组织内多量纤维素性渗出及炎症细胞浸润、组织细胞反应(图5);2019年12月24日肺组织mNGS检出鹦鹉热衣原体序列数163,予以莫西沙星0.4 g,1次/d联合多西环素0.1 g,1次/12 h抗感染,1周后复查CRP恢复正常(<0.499 mg/L),3周后复查胸部CT(图3c-d):右肺下叶实变影较2019年12月14日明显吸收。

图3 例3胸部CT检查所见(a-b:入院3 d胸部CT检查提示右下肺实变渗出影,炎症考虑;c-d:莫西沙星治疗10 d后复查胸部CT,提示右下肺炎症较入院CT明显吸收)

图4 例3支气管镜检查所见(a:隆突常规镜下未见异常;b:右主支气管常规镜下未见异常;c:左主支气管常规镜下未见异常;d:径向超声探头见右肺下叶外基底段探及低回声区)

图5 例3肺组织病理学检查所见(a:肺组织内多量纤维素性渗出及炎症细胞浸润、组织细胞反应,HE染色,×40;b:为a放大后所示,HE染色,×100)
讨论鹦鹉热衣原体具有独特的二相型发育周期,革兰染色呈阴性。目前鹦鹉热衣原体分为 A~G、WC、E/B及 M56型 10个基因型[1],其中对人致病的主要为A型。鹦鹉热衣原体主要通过接触鹦鹉、鸽子、家禽等鸟类传播,有文献报道人际传播的案例,但较为罕见[2]。目前世界各地均有鹦鹉热衣原体感染的案例报道,但由于该病确诊困难,缺乏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国外有文献报道鹦鹉热衣原体肺炎约占社区获得性肺炎的l%[3]。
鹦鹉热衣原体的临床表现并不典型,症状由轻到重表现不等,可累及不同器官或组织,包括肺、皮肤、心脏、肝脾、肾脏等[4],其中肺是最常受累的器官。临床上最常见的症状包括发热、咳嗽、疲劳、头痛、肌肉酸痛等。鹦鹉热衣原体感染引起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比较罕见,但也有个案报道[5]。本文例1也出现CK、CKMB急剧升高,可能是鹦鹉热衣原体感染导致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以往认为鹦鹉热衣原体很少引起重症肺炎,而本文3例患者入院后均病情进展,例1和例2影像学表现快速进展,例1出现Ⅰ型呼吸衰竭,例2也有呼吸困难表现,因此,鹦鹉热衣原体引起的重症肺炎可能并不少。有文献指出,急性原发性非典型肺炎患者如短期内无法确定病原,患者的病情可能会加重,有10%的患者甚至有生命危险[6-7]。该病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胸部CT表现为肺部炎性浸润,累及肺段甚至整叶,部分可伴有胸腔积液[8-9]。本文3例患者CT检查均可见单侧或双侧下肺实变渗出影,符合上述表现。提示临床医生发现患者影像学表现为大叶性肺炎,常规抗感染治疗无效时,除军团菌肺炎以外还要考虑到鹦鹉热衣原体感染。
目前微免疫荧光实验(MIF)是最常用的检测手段。其诊断标准为:MIFIgG≥1∶512和(或)IgM≥1∶32,同时还要排除类风湿因子所致的假阳性[10]。MIF检测的缺点是容易受到基础免疫病影响出现假阳性,或者由于前期抗生素使用出现假阴性[11]。
mNGS是新一代的病原微生物鉴定方式,是指利用二代测序技术获取样本中所有核酸片段的序列信息,经过生物信息分析与比对,检测出所有微生物的种类及序列数量的方法[12-13]。相比传统的培养及血清学检测方法快速高效且无偏倚,可及早诊断病原并减少临床抗生素的过度使用,缩短住院时间。mNGS的缺陷在于缺乏公认的判读标准、测序结果与治疗关系不明确、耐药基因难以检测及检测费用明显高于传统检测手段[14]。因此权衡检测的时机及对象较为关键。国内专家共识[15]指出mNGS适用于以下任一情形:(1)患者病情危重需尽快明确病原体;(2)特殊患者如免疫抑制宿主、合并基础病的重症患者需尽快明确病原体;(3)传统检测技术反复阴性且治疗效果不佳;(4)疑似新发病原体,临床提示可能存在感染性;(5)疑似特殊病原感染;(6)长期发热和(或)伴有其他临床症状、病因不明的感染。本文3例患者均是在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无效,病情进展后采用mNGS辅助诊断,选择这一时机应当是合适的。
目前四环素类抗生素是鹦鹉热衣原体治疗的首选药物[2],包括多西环素或盐酸四环素。盐酸四环素的成人推荐剂量为250 mg,4 次 /d;多西环素 100 mg,2 次 /d;为避免复发疗程至少持续3周。当单用四环素类药物治疗效果欠佳时,大环内酯类可作为很好的替代选择。虽然喹诺酮类与四环素类和大环内酯类药物相比,对鹦鹉热衣原体的活性较低,但近年发现国内衣原体对四环素类及大环内酯类的耐药性明显增加[16],因此在我国临床治疗中喹诺酮类也逐渐成为选择之一。对于重症患者可四环素类联合大环内酯类或喹诺酮类药物治疗,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和呼吸衰竭的患者还需循环及呼吸支持治疗。由于大环内酯类联合喹诺酮类药物容易引起Q-T间期延长,故不推荐这两者的联合疗法。本文例1单用左氧氟沙星片抗感染;例2予以左氧氟沙星片联合多西环素治疗,并行HFNC呼吸支持;例3采用莫西沙星联合多西环素治疗,都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综上所述,mNGS是对传统检测方法的有效补充。当患者病情加重而又难以通过传统检测明确病原,尽早明确病原是诊疗的关键。如果有条件,用组织标本进行mNGS检测较血液和肺泡灌洗液标本阳性率更高。以往认为鹦鹉热衣原体很少引起重症肺炎,但本文3例患者均在入院后病情进展,其中2例有影像学表现快速进展和重症肺炎表现,需警惕此类感染有重症化趋势,对此需要进一步开展多样本、多中心监测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