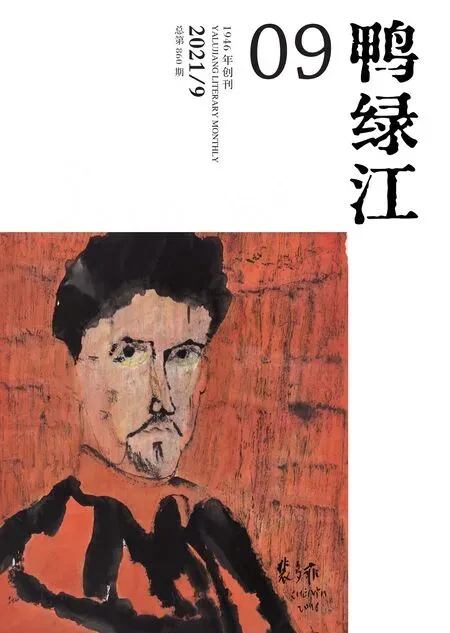自传与公传
2021-10-09 11:22:34刁斗
鸭绿江 2021年25期
刁 斗

我曾以《牛健哲再研究》为题,写过一篇近两万字的文学随笔,主要通过牛健哲,以及李月峰鬼金三位小说家风格迥异的创作特色,分析讨论相关问题,其间,提到了董学仁。这未免突兀,并且,不是简单地一笔带过,而是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地,在一篇关于小说家的文章里,分配出一千五百字的“巨大”篇幅给了这位诗人,还为烘托他的登场,先把夏多布里昂、赫尔岑、卡内蒂三位大神推举出来,让他们那浩如烟海的自传散文,理所当然地,把董学仁韧若涧溪的散文自传勾连出来。我不讳言,在我心中,董学仁那部既冥顽地迷恋自我又恺切地评骘人类的《自传与公传》,是关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最开人眼界更开人脑洞的平民史诗。
显然,前边我称董学仁“诗人”,并非对“散文家”的错植误用。我估计,一生都与所谓文坛保持距离的他,如果想要微醺一下,只能愿意醉于“诗人”。但坦白地说,尽管我知道他写诗多年,且与他相识四分之一世纪也不止了,可他的诗我好像从未读过,在我这里,他真正是“一本书主义”的标杆样板。他那很难终笔的未竟之作,那在《西湖》杂志连载十年暂时只能偃旗息鼓的一百几十万字“半成品”,那从面世之初就一直诱着我把玩不歇的他的我的也是所有人的“年月日”,是我所见到的他唯一的文学果实。但在我眼里,这部散文长卷,又从来都是一首一咏三叹而九曲回肠的绵绵长诗,它不仅无损于董学仁的诗人称号,还更以它反修饰反抒情反制式化的清洁的诗意,为当代中国文学和现代汉语保守了尊严,留存了骄傲。
它“对人性与社会,对耻辱与灾难,对疯狂,对暴虐,对悲和卑,对罪和丑,有着堪称完美的真实述说,而这一切,又成功地实现在他为洗涤汉语言的嚣张戾气和重塑汉语言的内敛品质的努力之中”。
在当年的文学随笔里,我如是说。
猜你喜欢
鸭绿江(2020年26期)2020-10-22 09:18:48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5期)2020-04-20 12:55:24
四川文学(2020年10期)2020-02-06 01:21:16
汉字汉语研究(2018年3期)2018-11-06 07:03:04
侨园(2016年5期)2016-12-01 05:23:50
新高考(英语进阶)(2016年12期)2016-02-28 21:58:06
语言与翻译(2015年2期)2015-07-18 11:09:55
现代企业(2015年5期)2015-02-28 18:51:04
消费导刊(2014年12期)2015-02-13 17:32:09
城市轨道交通(2014年2期)2014-03-20 13:2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