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气象事业自主建设的历程
■ 叶梦姝 孙楠 刘怀玉
最终,我国未能正式参加地球物理年活动,这既是中国地学界的遗憾,也是“地球物理年”国际合作计划的遗憾。即便如此,此番筹备工作还是大大加速了我国原计划开展的一系列科学研究工作,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友好合作的愿望,展示了中国气象科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大气无国界,近现代气象科学的诸多辉煌成就,都离不开国际合作。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气象活动多为外国教会开展,或由清政府聘用的外国海关官员主导,后期国人自主建设气象事业的意识逐渐觉醒,着手建设“国人自营气象事业”,并开始在世界气象舞台上崭露头角。
1 自主气象事业意识的觉醒
现存的近代气象要素定量观测记录,大多数由西方教会或外籍海关官员主导完成:例如最早在中国进行的气象观测,是1743 年法国传教士哥比神父记录的北京气温;中国近代最早的连续气象观测,来自1841 年起俄国教会在北京的观测活动;中国近代最早的气象观测站网,是1873 年前后由清朝总税务司赫徳(Robert Hart,1835—1911 年)建立。对清朝政府而言,气象作为国家事业和政府公共服务的属性尚未得到明确认识,也缺乏自主建设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意愿。
20世纪初前后,中国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其中既包括留学归国的青年学生,也包括开明进步的民族实业家。他们大多系统学习过近代科学技术,而且接受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冲破了旧思想和旧制度的藩篱,对科学技术在救亡图存和兴邦立国中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随着这批爱国知识分子走上历史舞台,国人自主建设气象事业的意识终于觉醒。
1911年,高鲁获得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工科博士学位,回国出任“中央观象台”首任台长;1913年,蒋丙然获得比利时双卜罗大学农业气象学博士学位,任北京“中央观象台”气象科科长;1918年,竺可桢从哈佛大学地学系博士毕业,回国后在东南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气象学专业……他们开创了一系列国人主导的气象活动,迫切希望为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建立自己的气象学术和气象事业。
1913年5月,召集东亚气象会议在日本东京,会议邀请了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法属)、香港天文台(英属)、青岛观象台(德属)台长参加,执掌“中央观象台”的高鲁却未收到邀请。临近会期,高鲁自费赶往东京旁听此会。时任徐家汇观象台台长劳积勋神父(Aloysius Froc,1858—1932年)出于公允之心,在会上主动说明了高鲁作为中国代表的官方身份,并建议主持人安排高鲁代表中国发言。
20世纪初,张謇在江苏经营的“通海垦牧公司”,曾数次遭台风、暴雨和大潮袭击,因缺少准确及时的气象观测资料,均未能提前防备,使公司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1916年,深受缺少气象保障之苦的张謇依靠自身力量,在南通建立了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民营气象台——军山气象台,在其撰写的《南通地方创设气象台呈卢知事》和《军山气象台概略》中明确提到:“窃农政系乎民时,民时关系气象。各国气象台之设,中央政府事也,我国当此时势,政府宁睱及此。若地方不自谋,将永不知气象为何事”,并切中要害地点出:“气象不明,不足以完全自治”。张謇从经济社会需求出发,对气象工作的国家政府职能定位和其公共服务属性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
1921年8月,时在南京师范学校地学系任教的竺可桢在《东方杂志》撰文《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分析了气象服务保障农业、航海、航空的重要作用,并从捍卫主权、为国雪耻的视角出发,系统阐明了独立自主发展气象事业的重大意义:“因风云之变更不常也,故设气象台以窥测之。德之割青岛,英之据香港,法之租徐家汇,其始焉即着手组织气象台……夫英法各国,非有爱于我也,徒以为其本国之海运谋安全计,不得不有气象台之设置耳,我国政府社会既无意经营,则英法各国即不能不越俎而代谋。欧美人士常訾我为半开化之民族,岂足怪哉……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
2 着手建设“国人自营气象事业”
“国人自营气象事业”之第一步,是要有自己的台站。“中央观象台”建立后,蒋丙然以一个开拓者的口吻自豪地说,“吾国人自营气象事业,自当以民国元年之中央观测台开始”,1928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近代气象研究的发祥地。此后,民国政府气象、民航、水文等部门,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逐步在各地建立测候所、气象台,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各地气象台站建设工作万兴未艾。竺可桢牵头“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制定了《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拟订了《气象观测实施规程》,规定气象单位,温度一律用摄氏度,气压一律用毫巴,以代替有些测候站所沿用的华氏度、毫米或英寸,扭转了20世纪初只在东部沿海地区有气象观测,而且均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窘况。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奔走收回被法日运行管理的徐家汇观象台、青岛观象台。1931年春,竺可桢和国际电讯局利用上海海岸无线电台,自行广播中国气象,并在全国各个无线电台内附设测候所,报告当地天气,逐步把外国人主持的顾家宅广播电台的气象广播业务纳入我国气象工作的轨道。1931年,蔡元培再次致函国民政府外交部,要求从速解决日本人从青岛观象台撤回问题,“以维主权而重学术”。
除了台站的日常观测外,中国辽阔疆域拥有气象科学研究的无穷宝藏,也应由中国人主导挖掘、完整保存、自主研究。1926年底,以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为首的德瑞科学家计划到我国西北做全面考察,原本与地质调查所签署了协定,规定只容中国二人参加,只能参与一年即须东返,采集到的历史文物要先送瑞典研究,该不平等协定遭到了我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强烈反对。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终于议决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明确中国境内考查团,必须由中国人主办,考查团组织定名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查团由中瑞双方各出团长一人,中方团长行使主人翁之权,外方团长以科学家身份参加,以我为主,平等合作;考查团所得遵循主权属我原则,在中国境内妥为保存,以供学者之研究,绝不许擅自运出境外。此《办法》制定,意味着我国的西北考察由外国人主导的时代结束,李宪之等人在我国西北开展的气象科学考察,也为日后中国气象学的研究积累了重要素材。
在现代气象仪器制造方面,中国古代有样式丰富、设计精巧的气象仪器,而近代以来,气象观测站所使用仪器中,仅有少量来自国产,例如上海徐家汇观象台使用的200 mm口径雨量器、双尾翼风向风速仪等,由教会所属上海土山湾孤儿院工厂手工制作,而大部分自计式气压计、水银温度计等均来自进口。1930年,为改变外国厂商垄断中国气象仪器市场的局面,蔡元培与丁西林等在上海创办了理工仪器制造工场,招收中国第一批近代仪器制造人员,并首次生产了水银温度表,虽然制造水平未达到台站使用标准,但迈出了自主生产气象仪器的第一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中国气象仪器的标准化生产能力,支撑全国气象台站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在气象学术语方面,逐渐在汉语中建立了规范的气象学术语体系(图1)。气象学术语的传入最早来自西方传教士等的译介。1853年出版的《航海金针》、1871年出版的《御风要术》、1877年的《测候丛谈》、1897年出版的《气学丛谈》等书,系统译介了近代气象知识。然而由玛高温、傅兰雅、金楷理等传教士口译,清末科学家、教育家华蘅芳等笔述的气象术语,依然存在文白混杂的现象,许多概念和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体系下的概念相互混淆,译法不统一,易导致交流不畅和概念混乱。通过多位气象学家的努力,1932年“国立中央研宄院气象研究所”出版了《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该表涉及汉英法德日等语言,按照英语字母顺序排列,其他语种以术语对译词的形式出现,初步具备辞典的功能。“教育部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在气象研究所工作的基础上,于1935年着手修订《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教育部公布气象学名词》,其中很多的气象学术语一直使用至今。为推动气象教育和学术交流规范有序,在汉语中建立一套规范的气象学术语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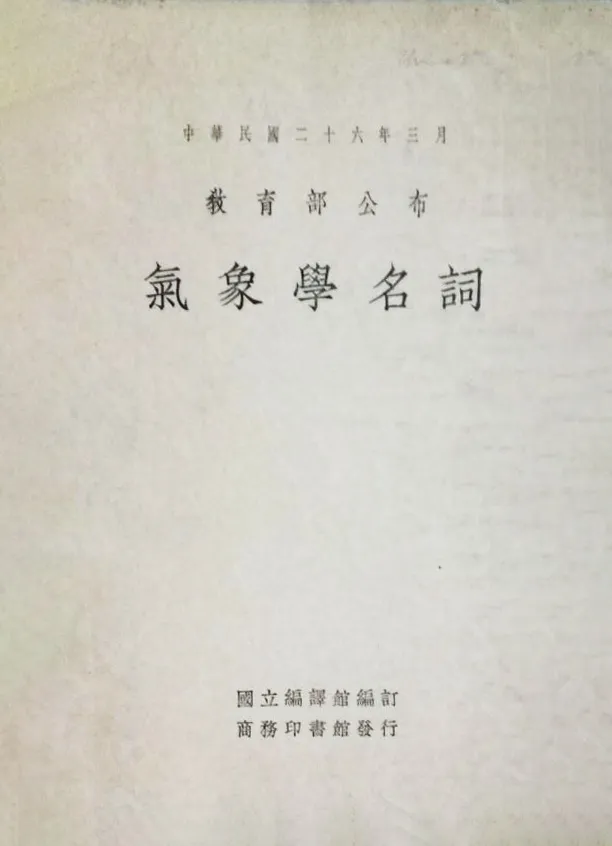
图1 《教育部公布气象学名词》(内文包括英名、法名、德名、决定名及多语种检索)
3 初登世界气象舞台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国际气象会议的相关资料中陆续可见中国的信息。例如1874年,在荷兰乌特勒支召开的国际气象组织(IMO)第二次常委会,有“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14个国家的24名专家参加”,1880年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的第一次IMC会议“促使一些缺少定时气象观测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增加定时气象观测”。亦有文献提到,英国人赫徳、金登干等,曾代表远东气象观测的具体实施者,参与国际气象交流。民国以来,随着“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中央观象台”等官方机构的建立,国人逐渐登上世界气象舞台,展现了独立自主的“中国气象”形象。
在20世纪20—30年代,我气象代表积极参加国际气象交流合作,除了1929年丹麦召开的第七届国际气象台台长会议,胡焕庸、卢鋈等最终因“中东路事件”未能参会之外,其余大多数国际场合都积极参加,并展现了独立自主的大国风貌。1930年4月,香港皇家天文台台长召集了远东气象台台长会议,邀请了远东各气象机构及轮船公司等代表出席,“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代表沈孝凰,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以及东沙岛气象台前任台长沈有基等出席了会议;1930年5月,第四次太平洋学术会议在荷属东印度爪哇开会,中国共有13位代表出席,共投稿论文16篇,“备受荷兰人欢迎,亦盛极一时事也”;我国还积极筹备参加了“第二次国际极年计划”,在峨嵋山、泰山日观峰(图2)及青岛崂山建立三个测候所,1932年8月至1933年8月,收集信风带季风区内高山及高空探测数据,“冀以阐发气象学上亟欲解决之问题,贡献於世”;在外交场合,竺可桢特别重视国家形象和维护国格尊严,1937年出席在香港远东气象会议期间,港督和会长两次设宴,都把中国席位排在末尾,竺可桢认为有损我国格,决定提前乘船返沪,不再出席会议,以示抵制;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海军上将柯克提出在国防部内成立气象局的建议,意图把原属政府系统的气象局归并于国防部,并公然提出正副局长的人选名单,这种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主权的行径令竺可桢十分愤慨:“美国海军贸然推荐人员,亦失体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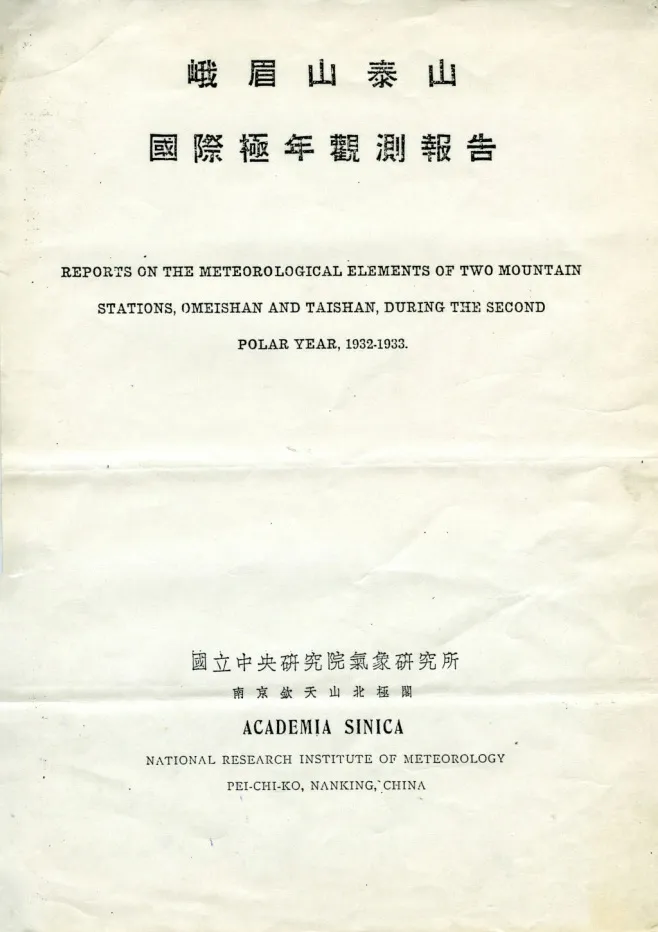
图2 峨眉山泰山国际极年观测报告(1932—1933年)
1944年,美国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开启了红色气象外交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与观察组成员频繁接触,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也希望藉由他们在国际社会上为中国共产党塑造朝气蓬勃的良好形象。气象方面的合作,是延安中美合作中最核心、最受到关注、最富有成效的部分之一。一方面坚持维护主权与民族尊严,拒绝了美方直接建设气象观测站的建议,提出由美方提供器材、中方派员建站,举办“清凉山气象训练队”,邀请美方人员主讲,培养了我党我军第一批气象工作者,为抗日战争提供气象保障;另一方面也开放合作,尽最大可能为盟军相关军事活动气象保障提供各种便利,据后来美军总部评价,延安气象站提供数据的可靠性,在中国十个气象站中名列第一。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由衷地称赞说:“你们的工作效率真高,这是重庆没有法子比的”。延安作为红色革命圣地,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信仰力量,征服了很多国际友人,包括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等等,在气象方面,共产党气象队伍也以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认真的科学精神,赢得了国际友人的认可。
4 解放初期捍卫“一个中国”
虽然中国是WMO的创始国和公约签字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其合法席位曾一度被台湾当局占据,1955年1月,我国外交部以涂长望局长的名义,向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区域协会主席巴苏发电报,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派代表正式参加会议……WMO应该立即将蒋介石国民党代表驱逐出去,以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机构的代表参加”。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1956年10月,我们首次作为气象国际会议主办方,组织了中国、苏联、蒙古、朝鲜、越南“五国水文气象局长和邮电部代表会议”,即“五国气象会议”(图3)。9天的会议开得很成功,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各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并就水文气象情报交换、高空气象台站网建设、民航气象服务、共同研究亚洲大气过程及交换水文气象出版物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在1955年周恩来总理批准的在国际航线上用国际简码进行气象通报、1956年批准的我国北京与苏联伯力之间的气象情报交换的基础上,又规划了北京—乌兰巴托—伯力、北京—平壤、北京—莫斯科、汉口—河内等国际有线电传线路,一方面用我们的气象信息为各国服务,一方面又保证了中国对周边国家气象信息的需求。

图3 1956年10月涂长望局长在五国气象会议上发言
1957年7月至1958年12月为国际科学界商定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是当时地球科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合作科学实验。从1953年起,竺可桢、涂长望、赵九章等人就开始积极争取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1955年苏联宣布加入并且建议中国也加入该活动后,我国正式开始了相关准备工作,建立了包括地质、地磁、天文、水文、气象等9个领域的工作组,参加了多次筹备会议。1957年2月19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达6000字的文章,详细介绍地球物理年的研究内容及意义。然而,在美国的怂恿下,原本未参加该计划的台湾当局,在1957年3月突然提出申请,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执行局,擅自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改成中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北京),并承认所谓“台北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台北)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专委会。对此,竺可桢致电国际地球物理年专委会,抗议它屈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并散发给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各国家委员会。最终,我国未能正式参加地球物理年活动,这既是中国地学界的遗憾,也是“地球物理年”国际合作计划的遗憾。即便如此,此番筹备工作还是大大加速了我国原计划开展的一系列科学研究工作,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友好合作的愿望,展示了中国气象科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至此,包括竺可桢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涂长望的《中国之气团》、赵九章提出的斜压不稳定概念、曾庆存提出的半隐式差分方法以及诸多中国第一代气象科学家做出的气象学研究及其理论探索,充分展示了华夏大地的天气气候现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辉煌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国际的学界认可。
5 结语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世界气象组织也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气象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深度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活动的部门之一,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外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中美建交后签署了中美大气科学合作协议书,中美气象合作成为了双边合作的典范;1987年和1991年,中国气象局局长邹竞蒙连任世界气象组织主席;20世纪90年代,中美两国领导人多次会谈,破除了冷战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影响,进口了用于数值天气预报等业务的巨型计算机,也是外交史上的一次胜利;2018年,我国成为世界气象中心,承担20多个WMO全球或区域中心,中国气象积极融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大政方针,聚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全球监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需求,共享风云气象卫星数据、组织多国别考察和教育培训、开展对外气象援助等,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优质气象保障服务,与20多个国家签署双边气象合作协议,不断开创中国特色气象国际合作工作新局面。
深入阅读
蒋丙然,1930.第四次太平洋学术会议纪略.气象学报,(5):106-123.
蒋丙然,1936.二十年来中国气象事业概况.科学杂志,(8):632.
卢鋈,1936.国际气象行政会议概况.气象杂志,(7):23-29.
宋杰,1993.在世界气象组织中任职的第一任中国官员.四川气象,(2):9.
孙楠,刘皓波,徐晨,2019.我国未参加1955年WMO亚洲区域协会会议始末.北京:第四届全国气象科技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王才芳,1993.加强国际气象合作促进气象事业现代化:纪念1993年世界气象日.气象,19(3):17-19.
许鑑明,1935.第八届国际气象会议近讯.气象杂志,(4):33-34.
许鑑明,1935.一九三五年九月华沙国际气象会议.气象学报,(6):34-35.
严振飞,1935.国际极年崂山测候报告.气象学报,(5):36-39.
佚名,1930.国际气象台台长会议略史.中国气象学会会刊,12(5):133-137.
佚名,1930.国际气象管理会章程.中国气象学会会刊,12(5):128-132.
于化民,2006.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中共领导人与延安美军观察组交往始末.史学研究,27(4):121-131.
张九辰,王作跃,2009.首次国际地球物理年与一个中国的原则.科学文化评论,(6):69-81.
张璇,焦俊霞,2016.民国时期中国气象学会成立考述.档案与建设,(4):55-59.
赵希友,1981.国际气象观测二百周年.气象科技,(3):42.
竺可桢,1930.第七次国际气象台台长会议纪略.气象学报,(5):124-131.
Daniel H,徐明,陆同文,1973.国际气象合作一百年(1873—1973).气象科技资料 (S3):17-29.
 Advances in Meteor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21年4期
Advances in Meteor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21年4期
- Advances in Meteor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其它文章
- 主编语
- 提升风云气象卫星服务能力,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2020年风云气象卫星用户大会综述 - 成于大气 信达天下
- AMS词汇
- 国际气象卫星协调组织(CGMS)统筹气象卫星系统建设的重要计划
- 致敬人民气象事业走过1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