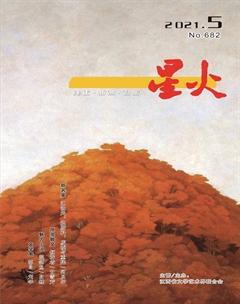白沙塘

莞城,这个城市空间在无限扩张后,我感觉,我的灵魂也在飘荡,城市越大,它越是让我感觉自己是无根的一叶漂萍。
我一直认为,我栖居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工作地点,一处是住宿地址。这两个地方,在东莞,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先说工作地,我工作的那家杂志社,是DM类型时尚杂志,是本地一家民营企业创办的,老板把杂志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无论盈亏,无论好赖,他都是一如既往地爱着这本杂志。这一点,倒是跟我很像。我也是一样,无论多难,无论多累,我也是一如既往地爱着它。但我们爱的方式,还是有所不同的。老板爱着它,是因为杂志更像他的又一个儿子,是他自己事业中的一部分,不说盈利,用来为公司打品牌,也是挺好的。而我一如既往地爱着它,那是因为我热爱写作,我也需要这样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从而让我的写作环境更好一些。
一
我的工作地点在东城大道往南的末端,骏达商业中心二楼。此楼靠近旗峰路与八达路交接十字路口。每天,大量的车辆在这里等候绿灯通行。这一带是莞城、东城、南城的分界点。以十字路口分界,脸朝正前方,是旗峰路,有福民广场、华康电器、岭南学校、国泰大厦,对面还有电脑城、家居城、旗峰邮局。国泰大厦的一楼店铺林立,美容店、美发店、教育培训机构、旅行社,还有各种美食店,以及如兰州拉面、桂林米粉一类的特色小吃店。回头看,是渡船澳、新华保险、中桥大厦、东远大厦、方中电脑城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里的周边还是一片坡地,种着荔枝、龙眼、芒果、黄皮之类的果树。再往上一点,到浩宇大厦附近却是荒地、鱼塘、农田,种有莞香树、橘树、橙树和各种农作物。往右,是骏达商业中心、金澳花园酒店、莞城实验中英文学校、中国银行、真功夫、百佳超市等。在百佳超市旁边,又如法炮制了一个十字路口。一直往前,这里最繁华,也最复杂,著名的雍华庭步行街就在这里了,还有美食一条街。再右拐是这一带的地标性建筑新城市花园、浩宇大厦、金澳大厦、东莞市法院。
自从进入这家杂志社,我上班的地方,就一直在骏达商业中心这座楼上,以前是九楼,现在是二楼。这栋楼,包括旗峰门诊、东莞市福利彩票中心、沃尔玛东莞总部、中国联通、新华保险,后来联通和新华保险搬到了三楼。以前这里还有一家很有名的美容美发培训机构,九十年代很流行,很红,电视里的广告,黄金时段都是这家培训机构的。往左是八达路,布满了极为夸张的各类光电五金设施。这里成为全市五金门店最多、城区光电污染最严重的地段之一。
仔细看去,我发现骏达商业中心其实也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建筑物,绿色的玻璃墙面,内部装修和设施不算太旧,是典型的复式写字楼。能在这里上班的人,大多数都是白领,还有一些业务员、促销员、行政人事文员之类。他们也算跟白领挨着边的,就是收入有时比白领少一些。我在这栋楼里工作了八年。这八年,我知道哪些公司搬进来了,哪些公司又搬出去了,虽然不是每一层的公司都很熟,但大体是了解的。
我在杂志社工作之余,曾经利用周末在六楼的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兼职,顶替一个临时有事回家的写作课老师。那些周末,我给孩子们正儿八经地上过几天作文课。记得那时我用了女儿读小学三年级时写的作文《最不快乐的一天》,作为范文给同学们讲述怎么写好作文。因为我女儿在写那篇作文时,年龄跟他们差不多。我说,你们不开心,就写不开心,开心就写开心,不要说假话,不要说空话,有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写,就不怕没东西写了,也不怕写不出来了,这样,你们才能尝到写作文的快乐。不过,这家教育培训机构在我进入这栋楼上班没多久,就搬走了。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反正是搬走了,而不是倒闭,这一点,我非常肯定。东莞的教育市场还是有得做,家长钱多了,就强迫孩子们要赢在起跑线上,逼孩子們学这个,学那个。钢琴、书画、音乐、写作,类似的培训曾风靡一时。
绕远了,言归正传。百佳超市后面,也就是从莞城中英文实验学校侧门这条路往里面直走,就是兴华路,再往前一点,就是白沙塘村。而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从兴华路这条主干道进来,到路边的小店,有一个上坡路,沿着坡走上去,大约是第四条巷口,左拐,拐入一条横巷,一直横着往里走,倒数第三栋,一横街二巷六号,就是我的小窝。
每次回来,我都是先解电子锁打开大门边的那扇小门,从小门进来,因为大门是卷闸门,只有三轮车进出时才打开,平时都是关着的。我们走旁边的小门,小门是铁门,以前出入要按门铃,后来门铃坏了,修了几次,也没好,于是老板叫保安换了电子锁。这下好了,谁要进来,都要开电子锁才行,如果是小偷,跟着住户混进来了,也是出不去的,相对安全了很多。
我住在二楼,202室,这是莞城区白沙塘兴华路一横街的一栋出租屋。是暂时属于我的小窝。简陋,安静,契合一切漂泊者的困窘、不稳定性。出租屋总是藏着太多的故事和秘密,但那些灰暗的、混沌的、红尘里的生活,怀抱梦、温暖和坚强,甚至是不屈的光芒。出租屋,承载着我的理想和梦,承载着我们夫妇的柴米油盐,以及逝去的青春爱恋。我从一个镇,搬到另一个镇,从一个屋檐下搬到另一个屋檐下,买不起房子,搬家是必然的。租屋,是权宜之计。
二十六年的漂泊生涯走过来,已经习惯了这种漂泊不定的日子。我的房间里,开始什么也没有,就一张廉价的席梦思床,连床垫都免了。后来住久了,就买了一台小彩电,十四英寸的,有时候好多雪花点。一台电脑,一张电脑桌,一个大衣柜,还有供老乡亲友过来住的上下二层的一张铁架床。现在没人跟我合租,铁架床我舍不得丢弃,也舍不得便宜卖掉,我在铁架上下层放满了书。房间里头是洗手间,外带一个灶,各种炊具,一张可以折起来的小小的旧桌子,一大堆书,一堆杂物。当我的书没地儿放的时候,我便打起了床的主意。我在床里头放了一排书,整整齐齐地叠放着。我喜欢睡在床上看书,尽管我知道,这个习惯不好,但我依然改不了。好在,我没有近视,也没有散光,更没有到老花的年龄,只要房间里有灯光,躺着看书,也就没问题。
这样的生活,散发着世俗的庸常生活的气息和寄居者漂的味道,还有困惑与迷茫。尽管这样,疲惫的我,依然可在夜里安然入睡。尽管蚊子在里头享受着它的美餐,当我睡着的时候,所有的梦想都开花了,一瓣一瓣的,从空中飘飞下来。
二
2004年4月的一天,我入职时尚杂志社,公司租的集体宿舍在白沙塘。
那是兴华路一横街的一栋民房,共四层。一楼存放单车,其余三层楼,每层只有二间房,都住满了人。男的,四人住一间,女的,也是四人一间。都是上下两层的铁架床,下面住人,上面存放行李。我们每个人的床上堆了衣服、书本、装满自己衣物的纸箱、背包,所有的家当,基本都放在床上,把床占了一小半。房间里连个桌椅也没有,更别谈衣柜什么的,说白了,公司租下来的时候,房间里一无所有,连床,都是公司买来临时安装的。
搬到宿舍那天,我带了一台电脑过去,还有一张电脑桌。一个同事说,你哪来这么多行李啊,怎么摆呀,放哪呢?我明白,她怕我占去大家太多的空间。我把箱子什么的,放在了我的床底下,还有一些放到上铺,再找到一个有开关插座的角落,把电脑安置好。我发现,整个宿舍,就我有一台私人电脑。看上去,感觉我还是同居一室的姐妹中最富有的一个。我大方地对室友们说:“以后,你们谁要是晚上加班写方案,或者写稿子,就用我的电脑吧,在宿舍加班也方便。”同事们这才报以些许微笑。此后,有同事晚上要写信,都在我的电脑桌上写。我在这个集体宿舍,度过了两年。我和她们几个打成了一片,我们成了新时代的同居女友。
后来,公司宿舍从这里搬走,换了一个地方,但还在白沙塘。白沙塘村庄很大,有三条路,把一个村庄分成三片。我们原来在中间这个村住着,后来搬到下坡路下边那个村庄。因为行李太多,也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作,所以,我就没跟着去住集体宿舍,与几个同事一起在附近合租了一套房。是在与白沙塘一墻之隔的余屋村。白沙塘和余屋村,巷挨着巷,房挨着房,两个村庄已然合成了一个大村庄。都属于白沙塘兴华小区。两个合租的女孩住进来一个月就先后离职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两个月后,我搬回到一墙之隔的白沙塘兴华路一横街二巷。一个人在外时间长了,买的书和物品多了,根本就不想老是搬家,搬回去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这里住得安全,有保安,还有路灯,从没丢过东西。至于房间小一点,巷子深一点,条件差一点,于我一个打工妹来说,有什么不可以忍受的呢?终于有一间自己独立的小屋。虽兜兜转转,但我一直没离开过白沙塘。
出租屋是我的一个生命站点,我是一只候鸟,注定要迁徙,要不停地漂泊与挪窝,那些从生活中飘落的,不是一些尚存体温的羽毛,而是我那飘零的心。对于下一个驿站和归宿,我实在不敢想象。
每天,我行走在兴华路上,走夜路已成习惯,感觉像在老家的小巷里行走一样,熟悉得很。偶尔也会在路边的小店里买瓶矿泉水,或到那两间很小的水果店的任意一家,买些苹果、香蕉、木枣、柚子、橘子之类的时令水果。这条路上,有湖南大碗菜、狗不理包子、龟苓膏凉茶店、大药房,以及大大小小的几个理发店、外贸服装店和鞋店,亦有诸如美宜佳、181便利店、万福、合家欢、一家亲等这些名字好听的杂货店。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杂货店,以及没任何招牌的小店,这些小店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了,附近还有个网吧。不过,这些年网吧也没啥生意,出租屋基本上都有宽带网络,只要买一台电脑,每月再交50元网费,就可以享受上网的便利。不过,出租屋的网速有点慢,因为一栋楼有好多住户拥有台式电脑,好多人家共用一条线,速度就慢下来了。不过没关系,这不影响我们上网聊天,看电视剧以及获取新闻资讯等。
三
老赵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同事,还是我的上司。老赵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他的诗写得好。他曾经也跟我们大家一起,寄居在白沙塘。这是在旗峰路、东城西路和东城大道之间的一个城中村。按老赵的话来说,这里的内部秩序就是一个字:乱。但这种乱是必须的。他曾经在自己的一首诗里,把这里形容成“章鱼社区”。这一比喻,确实恰到好处。可这还让他不过瘾。他还一个劲地说:“乱。很乱。是那种必须的乱。要用五十张嘴同时说出来的乱。人在这里,就像上万条大马哈鱼挤在一个渔网里。这个地方适合在河内的菜市场等待战争降临的杜拉斯的生活。”我认为他的话是很有诗意的,我非常认同他的这个观点。
我说,在白沙塘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店铺,这么多的出租屋,这么多的路边摊,像这样的城中村,在整个东莞是随处可见的,怎一个“乱”字了得。这里确实很乱,混乱不堪,一团糟。每到下班的时候,旁边的菜市场,以及走回来的路上,人头挨着人头,单车挨着单车,每个人都穿行在人群的缝隙间。像老赵这样的人,嗅觉灵敏,一定能闻得到烤羊肉、烤鸡腿、烤鸡翅的香味,闻到了肉香,就如小猫闻到鱼腥,他是一定要坐下来喝一些酒的。他高兴了要喝,郁闷了要喝,悲伤了更是要喝。经常,我晚上关在家里写作,或者正上网,被他催命一样的,一个电话就叫了出去喝酒。走出小巷,走过兴华路,我总能见到他跟几个大男人在一起喝酒。当然,这些男人,我认识的多。偶尔也有我不认识的人。或者有时干脆就他一个人在那里孤独地喝闷酒。他像是不喝一点酒就绕不过去一样。他绕不过这些酒和他自己,绕不开与他人的碰撞。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酒友,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老是要抢他的话,打击他的自信心,让他生气。正如他经常打击我的自信心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被他叫出去跟大家一起聊天喝酒。其实,我是讨厌酒的,我从小对酒就有心理阴影,可我又经常参与他们的酒会,从而让人感觉到,我对喝酒也乐此不疲。
四
兴华路的脏乱差,是出了名的。跟无数的城中村一样,这里也有路边大排档、旧货店、发廊、水果铺、自动取水机等。当然,这里也是小偷、抢劫者的乐园。兴华路是进入白沙塘村的主干道,很远就能闻到这里气味很浓的盒饭味,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水渍和垃圾,有人在这里遭遇过抢劫。我也是其中之一。
那一天,凌晨一点多,我在办公室陪美编做好了杂志版面后,一个人回家。走过一家美容护肤品店门口,看到三个男子,有一个像是在拐角处系鞋带,另两个像是在等候他,我没有太在意。结果我一走过去,他们就开着摩托车冲上来了。那天我背一个小小的女挎包,早上出门的时候,女包的肩带突然坏了,我打了个死结,还没来得及修好,包里除了信用卡、身份证、手机之外,还有一些钱。不多的几百元。突然就有人从后面一抓,将我的包给撸走了。我迅速反应过来,看到抢我包的人,就是刚才蹲着系鞋带的那家伙,他坐在摩托车的最后面。我一个激灵,飞奔上前,边跑边追上去狠狠地骂道:想死啊,我都到家了,你还敢抢我,没死过!之后我手一抓,把包给夺了回来,我抓到女包拖下来的长肩带。与此同时,我用尽全力把包狠狠地掷在那家伙身上,并重重地捶了他一拳。那辆车失去重心摇晃了一下,后面坐着的那个人就掉了下来了,又拼命地爬上去,摩托车拐个弯,往右边的小路跑了,一晃眼就跑得无影无踪。毕竟,邪不压正。他们其实也怕被抓。
在余屋,我住在一楼靠窗的一间屋子。我看中这间屋子,是因为它够大,采光好还通风,窗外是一片开阔水泥晒场,可以停车,这很难得。虽然我没有车,但在东莞的城中村,要找一处通风采光好的房子,价格还适中,是很难的。这间屋子,我们放了两张席梦思床,三个人住,杨莉莉和凯丽两个睡一床。一个月后,这两个80后女孩先后跳槽了,留下我一个人睡一个房间,我每天晚上都要把窗户关得紧紧的。
平时,我早上去上班,走过小路或穿过小巷时,偶尔能看到一些被丢弃的皮箱、裤子。这肯定是小偷干的。有个晚上,我把手机放在床边充电,我的床离窗户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早晨五点多,天都快擦亮了,我突然惊醒,发现窗口有一个人,远远地用一条长长的铁线,线的末端有一个长勾子,像钓鱼一样,把我的手机勾到窗户底下了,再晚一分钟,这手机就不归我了。我大喊,有小偷。这一叫,小偷就跑了。我赶紧走到窗户底下,把手机拿回来。好运气并不总能眷顾我,我那只非常漂亮、非常小巧的粉红色的诺基亚小手机,在一次充电中,半夜还是被小偷勾走了。这才刚充一百元话费没几天呢!我看到窗户被小偷用刀片撬开了一小片。很害怕。尽管这样,我还是没有搬离这间房子,因为交了一个月押金,我一定要租够三个月,找到适合的房子才搬离。除了手机,值钱的东西,我尽量放在办公室,不敢拿回出租屋。
最恐怖的还是入室偷盗。每次被盗,小偷都是从这栋房屋的三楼下来。因为一楼有一户人家住着老人和孩子,他们太警醒,小偷不敢来;二楼没入口。三楼是两个男同事合住,小偷每次都是先撬开三楼房间的门,没啥东西可偷,就跑到二楼,继而一路偷到一楼。太猖獗了,如入无人之境。
有一个中午,我们正在办公室休息。房東突然打电话过来,说我们这栋屋被盗了,让我们赶紧回去检查一下,看有没丢什么贵重物品。我们赶回家,屋门大开,满屋子衣物和书本零乱不堪。床,纸箱,小盒子,所有的地方,都被翻乱了。我们赶紧逃离了那家出租屋。
在余屋,我的损失是惨重的。我是一个打工妹,没赚多少钱,却在这个出租房里,损失一只四千多元的欧时殿手表。那是一次活动中,我的女友谢海英得到的奖励。那年海英和几个文友为我庆祝生日时,她把表送给了我,表是男式的,海英的意思是要我送给家人。盛情难却,我收下了。我家那位戴了几十天,以为坏了,拿回来让我去找商家修理。我也懒散,一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把表放在床上的一个盒子里。后来,这表啥时不见的,我都不太清楚,反正是在余屋村这个出租屋里弄丢的。
我在这个屋子一共住了三个月左右,丢了一块表,一只手机,还丢了其他一些小东西。我留下了后遗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睡觉不敢开窗,把窗子关得严严的;只要睡醒了,一个激灵就是看看身边的女包是否还在,看看身边的手机是否还在。直到很久,我都还是这样。尽管我后来住的地方很安全,但我还是不太敢放肆地开窗,不敢安心地睡觉。无论是外出住朋友家,还是住酒店,或是住出租屋,我都不敢把包放在显眼的地方,或者靠窗的地方。我一定要找个柜子把包藏起来,才敢放心睡。
五
搬离余屋,回到白沙塘,我住在兴华一横街二巷六栋。找这处房子,我没费什么力气。这个房子,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开始我选了六楼,采光好。后来,我还是听了同事高远的建议,选了二楼。一是行李和书籍太多,二是二楼这个房子,通风采光好。终于,我远离了那种因害怕被盗而心惊胆战的日子。
白沙塘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白天热闹,晚上安静。住在这里的,什么人都有,老人、孩子、中青年夫妇、热恋中同居的男女。我见得最多的,是业务员、促销员、超市营业员,也有沿街推着车卖水果的,踩着三轮车下苦力为别人搬家的,以及捡破烂为生的。搬家的人,往往兼职捡破烂,打扫卫生的人,也兼职捡破烂。每天下午至傍晚,小巷被租房的人丢出来的垃圾弄得脏兮兮、臭烘烘的,但到了第二天早上,小巷又干净起来,环卫工人清扫垃圾之后,很多时候,还要用水清洗一次,这样,再脏的小巷,也变得洁净如初。
当然,他们不白干,我们每户居住者,每个月都要掏五块钱,或者十块钱的垃圾处理费。这样,房屋走廊和小巷,都有专人清扫,我们只要把各自的房间打扫干净就行了。每天一大早,租客们各自从白沙塘的小巷里走出来,有提包的,有踩单车的,也有推三轮车卖水果的,有送孩子上学的,有开小店的。假如那一天是周日,早上九点起床,也是很安静的,因为所有的人都不用起大早上班了,包括踩三轮车卖水果的。
遮挡白沙塘的是一些外观华美、风格硬朗的高层建筑。他们华丽丽地立在四周,包围着白沙塘,以及租住在白沙塘的人们。在纸醉金迷的夜色下,在琳琅满目的超市里,在来来往往的人中间,你是否想象得到,被这些高大建筑包围着的里头,像白沙塘这样的城中村,是另一番光景?这里聚集的,是底层人物的小悲欢。
这里,是东莞乃至广东珠三角一带城中村的缩影。用诗人老赵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像“一锅不洁的汤”一样的社区。“被掩蔽的存在,也是东莞这座城市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最真实的横断面。”这些比喻虽然有一些新奇和夸张,但它是真实的。
几乎所有的城中村,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有些村子大,人多,有些村子小,人少,而且住着的人,有不同的面孔和不同的户籍,就这点区别而已。本地人很少,很多本地人都住进了别墅、花园小区里。
在莞城这些年,经常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好不容易跟那里的人混熟了,我又要搬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而后再和左邻右舍混熟。从一栋旧楼房,搬到另一栋旧楼房,常常这样搬家,让人身心疲惫。有的人,一床被褥,几件衣服,一个行礼;有的人,拖家带口的,行李很多。人在旅途,这样的漂泊生活是必须的,早已习以为常。好在同事们都住在附近,有个什么事,也有一个照应。白沙塘,它在我的漂泊生涯中,承载了我在莞城八年的青春岁月。这是一份深厚的情感。
诗人老赵有段时间搬到白沙塘的岗庆楼小区居住。岗庆楼是一栋老楼,村里很早盖起来的一栋集资房,墙体和楼道都破败不堪,一看就有些年头的了。但里头还是不错的,有一些人家装修得还不错,自己家还住着,没租出去。他在那栋楼没住几天,就丢掉了一台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和存在电脑里的长篇小说稿。这让他很痛心,那个长篇可是他花了不少时间弄出来的。因为这个原因,他花大钱下大决心搬进了离公司很近的花园小区。一个月的租金,是工资的五分之一。尽管这样,他还是乐呵呵搬进去了。搬家的那天,尽管他请了搬家公司,但还是需要有人帮忙。我帮他在旧楼看住搬到楼下等待装车的行李物品,他在新的出租屋整理房间,把已经搬过去的东西安放好。中途我跟了一趟车去他的新居,他的一个纸箱就弄丢了,里面放有电饭锅、插座、切菜的钢刀之类的东西。他晚上收拾好行李,想煮饭时,却找不到电饭锅了。他说,我们为什么总是在搬家,总是停不下来呢?就像卓别林电影中的凡尔杜先生,一年四季都在寻找一个藏身之处;或者像凯鲁亚克的小说在《在路上》中的那些人,在一个“人们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他们总是找借口四处奔波,事实上必须搬家的借口永远存在,根本无需寻找。
其实,白沙塘很美,以前还挺有故事的。听说下坡路那边那个村庄有一个庵堂,在“破四旧”的时候被拆除了,后来我去求证,专事挖掘东莞文史的女作家李翠微告诉我,白沙塘最有名的不是庵堂,也不是庙宇,而是一口泉眼,也就是一口老井。村里人就着泉眼挖了一口井,井水甘甜,冬暖夏凉,清清亮亮四季不枯,滋养着白沙塘人。有时,连邻村的人,也会到这口井来挑水,井水很甜,甜得像白沙糖般好喝。李翠微说她小时候到过白砂塘,大约六七岁吧,见到过这口老井,村里人都在井里挑水喝,井边一天到晚都很热闹,也不知道啥时候这井就没了。她这么一说,我感觉可信度高了,我明白了“白沙塘”这个村名的由来。
如今,一栋一栋的握手楼,高高立起,在小巷外边朝里向上看,就是一线天。我每次走过兴华路拐角的上坡处回住处,都会见到各色的小花。特别是簕杜鹃,还有五角梅,每到花期,就开得红艳艳的,从一家新楼二楼阳台的屋角倾泻而下,红灿灿的。看到这些花,我满心欢喜。到了金秋十月,金桂飘香,香满整条路、整个村子。
我的屋前走过去两条横巷,藏着一家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是公立的。这里也有派出所、村委会、妇联之类的单位,也有水果店、杂货店、小菜摊、快餐店。只要是人们日常需要的,在这个村子里都能买得到。
和南城塘贝、罗沙社区、罗一新村、步步高小区、东城涡岭、东城主山等这些地方比起来,白沙塘一间房子的房租至少要多出几十块至一百块,但很多人还是乐意租住在这里,不仅因为走出村庄大门楼就是繁华地段,更因为大多数商场、企业、店铺的老板,没给员工提供食宿,他们只好在离商场最近的白沙塘租房。这里交通便利。白沙塘往前,就是地王广场,有一个公交站台,往后走,是金澳花园公交站,往西走,是白沙塘公交站。差不多村庄的每个出口,都有一个公交站台。赶时间的话,打车也方便。这样住的人自然就多了,房租也随之水涨船高。
白沙塘一点也不吵,外面马路上的喇叭声,吵不到这里来。当然,小巷里也蛮多汽车的,但多是商务用车,大多数人都是早出晚归,也就听不到吵闹的车声。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尽管我现在租的房子,东西多了之后太挤,但我依然选择不折腾,不搬家。在广东这么些年,也不知道搬了多少回家了,每次搬家,都要丢掉一些绿豆芝麻一类的“家产”。搬一次家,至少要丢掉一个月的收入,还要累死累活地收拾行李,打包,装车,到另一个地方之后,再卸下来,再装上,甚至还要重新买床。每搬完一次家,铺好床,洗干净身子,把有灰尘的衣服换掉,我便一头把自己扔在床上,深深地舒一口气。
六
2010年的平安夜,一点儿也不平静,白沙塘很闹,每条小巷里都很闹。三三两两的人,邀约出去喝酒逛街,他们玩得很疯。手牽手的情侣,走在街头小巷。手捧红玫瑰,走路像站不稳似的青年女子靠在男友的怀抱里作幸福状,那含情脉脉的眼神,挺让人感动。黑色的夜晚,心境却是明亮的。上半夜还有人在小巷里走动,有人很晚从外面回到小巷的家,咚咚咚的脚步声响个不停。一忽儿这扇门咣地响了,一忽儿那扇门吱呀响了,一忽儿又从哪个窗子里飘来了炒花生的香味,鱼的香味,各种味儿填充着小巷,并飘荡得很远。也钻进我的鼻孔,容不得我装睡。这个时候,我才想到,有一群人,在一起热闹,也是一件好事。
次日早晨,九点半,我懒洋洋地起了床。在窗口,我看到对面窗子里的女人起来做早餐了。她冲我笑了一下,我也冲她笑了一下,就忙各自的事儿去了。我知道她曾经是一个白领,这阵子辞职在家带孩子,偶尔跑到东莞来,看望一下自己的男人,也或许是一种监督吧。说起来,他们夫妇还是我的江西老乡,只是隔得远,好像他们是赣北那边的。她有可能知道我是写东西的,有可能什么也不知道,如此而已。双方姓什么,叫什么,我们互相一概不知,只是偶尔说两句话,打声招呼,或者笑一下。她的厨房对着我的窗子,平时她炒什么菜,我闻得出香味。她那天在煮早餐,弄得厨房叮当作响,一下子是刷锅的声音,一下子是洗菜的声音,再不就是锅铲碰撞铁锅的声响。她愉快地哼着歌儿,做着这一切。一个幸福的小女人。她穿着普通,住着租来的小屋,但这并不妨碍她的幸福,不影响她的快乐。
我出去买早餐,充话费,行走在小巷里。小巷里静悄悄的,跟昨天平安夜的吵闹比,仿佛换了一个天地。小巷里的便利店,统统没开门,所有的人都似乎还在睡梦中。走了很远,到兴华路和聚福市场交界处,才看到美宜佳在开门做生意。我去充了话费,本想到周边水果店买些水果,结果,还是未开门。看来,平安夜根本就没让他们平安,把他们折腾得够呛。
回到家,我先打开电视。电视里演些什么,我不关注,我要的是一些热闹的声音。再打开电脑,上了线,群里的文友们,早就起床了,大家聊得火热。长安的文友塞壬说她今天早上可惨了,她在外面晒衣服,门被风关上了,她的钥匙留在屋里,进不去,费了好大的劲,才从房东那里拿来了备用钥匙,这让她在外面冻了半个小时,现在坐在电脑前,还感觉到冷。还有一个马大哈,出门称了菜,却发现兜里没钱,跑将回来,又发现钥匙丢在了菜市场,又折回去。如此往复,找回了钥匙,回到出租屋拿了钱,又跑回菜市场,来回折腾,累得够呛。他说,幸亏,菜市场离家还不太远。
我喜欢把出租屋称之为家,实在是想把栖居之地变成归宿,但它确实不是归宿,或许这就是宿命。我经常站在高处,仰望这座城市里的万家灯火,在高楼与高楼之间,在那些私自探出来的灯光里,我不敢奢望,能拥有一套房,我只希望在那些飘着灯光的窗户里,或许哪一天,可以有一张床是属于自己的,我可以在这里安放我的身子、思想,甚至灵魂。对于一个漂泊不定的人来说,出租屋意味着灵魂的自由。我的老乡、作家祝成明说,出租屋意味着夫妻俩还不敢放肆地做爱,恋人们亦不敢纵情地缠绵,随时会有人过来查水,查电,偶尔也会有临时性的查房这些打扰。出租屋也同时意味着青春的背影,半老的徐娘,挽留不住的日子,日渐消磨的拼劲和激情。他总结得很实在,也很贴切。可我,还是相信,明天会更好,幸福离我并不是很远,我还是心怀美好,对未来怀抱希望。
相对于城市的高楼大厦、奢华的灯光,还有宽阔的车道,城中村里的出租屋,是一个死角,是一个被人忽略的地带,但出租屋里的细枝末节,是真实的生活。那些像我一样,行走在城市边缘的人,经历过太多风吹落叶的伤感,日晒雨淋的悲怆后,无论再遇见什么样的风雨,都是闲庭信步。
汪雪英,江西省吉安市永新人,江西省作协会员。东莞文学院第五届签约作家。1991年始写作。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散文选刊·原创版》《星火》《飞天》《绿风》《中国诗歌》等刊。出版作品集、专著多部。《同在屋檐下:婆媳关系》《漂在东莞十八年》分别入选中国新农村建设和江西省新农村建设“农家书屋”工程。
——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