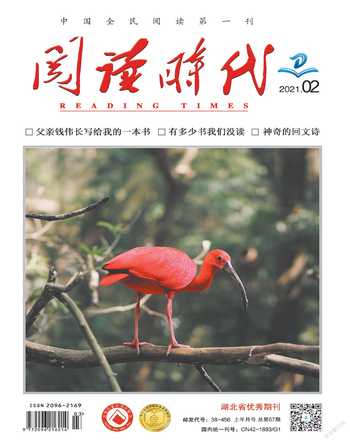谈谈本色美
郭小聪
有人说,本色是生命美的极致,这很让人深思。因为一些堪称绚烂归于平淡的作品,往往不是由作家,而是由圈外人写出来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写作是一种精神生活,当一個人把自己平凡而又非凡的一生变成文字,当他开口说话时,自然就有一种感人的力量和生命美感。
玛丽·居里的短文《我的信念》第一句:“生活对于任何一个男女都非易事,我们必须有坚忍不拔的精神。”这句话由她说出来和我们说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玛丽·居里是以她卓绝奉献的一生来为这篇文字做底色的,当我们回味她献身科学,甚至为了造福人类而自愿放弃了镭的专利权,谁能不肃然起敬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色美总是不经意地给人以震撼。玛丽·居里说:“我在生活中,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后来我要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侵扰和盛名的渲染。”一般人说这个话,恐怕有吹牛之嫌。玛丽·居里这样说就太谦虚了!朴素口吻中,有一种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高贵而谦逊的人格力量,所以她一开口,人们会静静倾听,喧闹的生活也即刻安静下来:“我年纪渐老了,我愈会欣赏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如栽花、植树、建筑,对诵诗和星辰,也有一点兴趣。”你看,那么壮阔的事物,在她却举重若轻,只说“也有一点兴趣”,却没有一点做作之嫌,因为对她而言,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享受生活了,只有伟大的心灵才能达到如此的安闲。
事实上,这种本色美是人如其文,文如其人的。据记载,当年玛丽·居里在丈夫去世后被聘为法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教授,她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教育部长、校长、教授、记者们都挤到教室里来,这位传奇妇女无论讲些什么都将是历史性的。可是谁也没料到,这位全身肃服、脸色苍白的知识女性,在长达5分钟的欢迎掌声过后,讲的第一句话是:“当我们考虑到19世纪开始以来的放射性理论所引起的进步时……”,没有繁文缛节和扯闲话,专注的是学术,这就是真正的学者风范,而让人折服的也正是这种朴素的本分,而非任何周旋。
一位当之无愧的杰出人士,理应是被仿效的榜样,而不仅仅是被谈论的对象。所以有时我想,究竟有没有一种专门的“公共知识分子”呢?那种公众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究竟是来自于在公共场合,以公众名义东鳞西爪地讲一些惊人之语?还是在长年探求中,宠辱不惊地默默推动人类思想行为的变革?这的确是个问题。最怕那种看似学者的沽名钓誉者,漂浮在水面上如泡沫般无足轻重,却占据了显眼的位置。而真正的学者身上都有一种磐石般的沉静,只尊重事实,不在乎别人的关注,既不轻易定论,也不隐藏结论。当年,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在写《寂静的春天》时已身患绝症,正在化疗,伴随这部书问世的则是商业大公司的诋毁和世间的冷落。两年后她便去世了,然而她的声音注定永不寂静,因为她第一次揭开了农药毒化大自然的可怕真相。她从未标榜过什么,默默为自己的超前思想付出代价,但也开启了人类环保意识的新时代。这正是专业知识分子的本分和本色!
个人忍辱负重,社会从中受益,他们坚忍的情怀,在于代表了人类不断进步的奋斗精神,努力把头脑风暴上升为建设性的智慧,而不是沦为发牢骚和玩世不恭,因而让人百读不厌。爱因斯坦在一篇感人的悼词中早就洞察到:像玛丽·居里这样的崇高人物,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于人类所做的贡献。因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的里程碑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要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更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至今会把玛丽·居里、爱因斯坦等人的文章列入世界散文名篇,因为这些无法仅凭风格技巧去获取的篇章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以不息的生命光辉昭示我们:在任何时代的人生戏剧里,人们活着的时候都平凡,只有谢幕后还活着才伟大。
(源自《中华读书报》)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