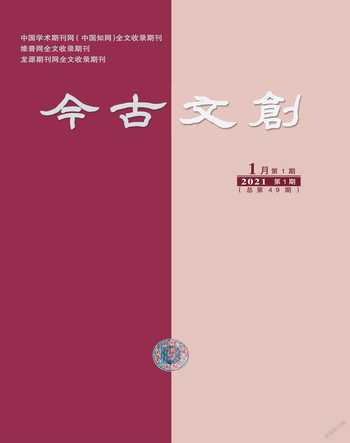天津民间舞蹈的仪式性特点
【摘要】 天津民间舞蹈种类繁多,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仪式性。本文以“津门法鼓”为例,浅析其中的仪式性特点,发现其仪式性和“法鼓”源起时的佛教思想、道教信仰、妈祖文化以及汉族传统的农耕文化密不可分。
【关键词】 天津民间舞蹈;仪式性;津门法鼓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1-0095-03
“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
说起天津,令人印象深刻当属天津的各色美食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天津的民间舞蹈也同样别具一格。天津民间舞蹈不同于北方的大多数民间舞蹈以手绢、扇子为长,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以及历史因素,产生了独具津门特色的“法鼓”,究其根源则源于其舞蹈中涵盖了大量的仪式性特征。“仪式”通常和宗教信仰密不可分,而所谓仪式,就是指表现或者传达这些信仰所采取的程式性或是带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津门法鼓”又称“法鼓”,是一种集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多种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的表演艺术形式,其在2008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列为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尤以挂甲寺庆音法鼓、杨家镇永音法鼓、刘园祥音法鼓为主要代表。“法鼓”由于其产生的年代以及其后的发展等原因,使之不仅蕴含了宗教文化的色彩,还因为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浸润了妈祖文化的特色,以及农耕文化的内涵。
一、佛、道文化的积淀
(一)佛教文化的熏染
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有史料记载最初可追溯至汉明帝时期。佛教在传入之初,并未在群众中普及,只汉朝少数王公贵族间流传。后来,为了佛教能够更加广泛的传播,就想到将佛教特色融入人民生活中去的做法。当时因为战争、饥荒等原因,百姓苦不堪言,而佛教恰好利用了这一点,将佛教中的教义—— “无常”“因果”等观念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而佛教的音乐、舞蹈仪式这些也随之走进百姓生活中,让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百姓从现实生活的桎梏中得以解脱出来。“法鼓”就是联结佛教文化与人民生活的代表之一。首先,“法鼓”一词源于佛经,最早可追溯至《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中,“唯愿天人尊,转无上法轮。击于大法鼓,而吹大法螺。”“法鼓”在形成初期还只是诵经时的一种法器,但可以看出“法鼓”必然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其次,从“法鼓”的音乐来看,现存的三家“法鼓”会的曲牌都不尽相同,但是仍旧可以将这些曲牌与其他地区的汉族民间舞蹈进行区分。大多数汉族的民间舞蹈中的音乐都是喜庆、跳跃充满活力的,“法鼓”中的曲牌则不同,它传达出的音色更洪亮、浑厚悠长,听后让人精神振奋的同时又平添一股宁静在其中。或许这正是佛教文化的内在影响。最后,从“法鼓”的舞蹈动作来看,“法鼓”的舞蹈动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行进的步伐,另一种是原地的动作。行进步伐,“法鼓”队又称其为“蹈(tāo)步”,动作时“法鼓”队的队员肩挑重达80~120斤的茶炊和样梢,脚下的步伐则像莲步一样,轻盈飘逸,真映衬出佛教所言说的“步步生莲”。原地动作又称武场动作,其动作主要依靠上身和手臂的旋、拧、翻、甩,而下身则扎起低沉坚实的马步。其基本动作“抱钹”和“捧钹”,其形象就好似佛像中的罗汉形象给人一种端庄、肃穆之感。还有的复合性動作则引用了佛教词汇,如:饿虎扑食、仙人指路等。“法鼓”从词源、曲牌、动作等多方面都渗透出了佛教思想,而这种润物细无声的仪式性特点,宣扬了佛教思想的同时,也提升了“法鼓”自身的价值属性。
(二)道教思想——崇道尚仙的隐喻
“法鼓”艺术的发展与道教思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思想与佛教不同,它讲求“长生不老、画符驱鬼”。而这种崇道尚仙的隐喻,首先体现在“法鼓”会祭拜之时。与许多华北地区的民众一样,天津郊区民众也有供奉地仙的习俗。根据的刘园祥音法鼓会的会头刘师傅介绍,他们村就信奉道教五大仙之一“柳四爷”,他们在每次出会时都会提前拜一拜柳四爷,保佑他们能够平安顺利地演出。五仙分别是“狐黄白柳灰”。狐是指狐仙,黄是黄鼠狼仙,白是指刺猬仙,柳是指蛇仙,灰是指老鼠仙。古人常常将蛇当作龙的化身,传说伏羲和女娲都是人首蛇身的仙人,蛇也就被认为是具有灵力的仙人,因此村民们常常将他供奉在家中。而刘园村的人之所以供奉柳四爷也有着一个传说:相传明朝永乐年间瘟疫频发,柳四爷恰在此时出世,帮助百姓驱逐瘟神,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而柳四爷的庙堂前有一棵柳树,人们病发时只要取其树叶、枝条和树皮将它们熬成水服用便能够药到病除。因此柳四爷被常年供奉在刘园村村民家中。刘园村的法鼓会还有一个习俗就是每年在冬三月时,祭拜东鼎娘娘。相传东鼎娘娘是碧霞元君座下的弟子,是专门下凡来保护天津四郊五县的这些群众。当地有一座东鼎娘娘庙,此庙建于明朝,明朝地方志记载“国朝四庙为四鼎”东鼎娘娘庙,西鼎天后宫,之所以祭拜东鼎娘娘也是当地的百姓希望通过祭拜能够求得平安、顺遂。此外,挂甲寺的庆音法鼓保存着半副銮驾,这幅銮驾是由明朝崇祯后妃所赐,距今约有400多年的历史。銮驾的器具中如日月龙凤扇、钺斧、朝天蹬、软对、硬对等,都描画着八仙过海和南极仙翁等图案。寓意不言而喻——求得长生、消灾解难。
二、妈祖文化的浸润
与内陆城市不同,天津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三会海口”、东临渤海,素有“九河下梢”之称。而这种海洋文化也造就天津地区人民的独特信仰—— “妈祖”。“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原名林默 ,宋代建隆元年农历三月二十三诞生于福建莆田湄洲岛,传说她能在渔民出海时保佑渔民安全返航、消灾解难,后来因为救助海难中的渔民,于宋太宗雍熙四年的农历九月初九去世,死后曾多次被分封。最初封号,是在宋朝的宣和五年,宋徽宗赐予“顺济庙额”。后来历经42次的封号,最后一次是在清朝的光绪元年,加上之前的加封,妈祖的封号共64个字: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祐敷仁天后之神。可见妈祖的地位在宋 、元、明、清时期日益壮大,但妈祖文化又与“法鼓”有何联系?这就要从天后宫开始说起了。天津的百姓为了纪念天后,同时也为了祈求海事顺利,就在每年天后诞辰之际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皇会”。因此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这一天,天后宫附近都会围堵得水泄不通。而“法鼓”就在这“皇会”中承担随驾和护驾的作用 。随驾“法鼓”就是娘娘出巡时的随驾法鼓会。现存的随驾“法鼓”有刘园的祥音法鼓会和杨家镇的永音法鼓会。随驾法鼓一般是跟天后队伍的后侧,履行侍奉的职责,提供娘娘出巡生活所用的必需品,或是供出会时“吃、喝、穿、用、梳洗打扮”的用品。因此,随驾“法鼓”的道具除了伴奏的乐器外,分别有:圆笼、八方盒子、软硬衣箱各、软硬茶梢、软硬样梢、软硬茶炊子、气死风灯等。护驾“法鼓”就是指履行保卫职责的法鼓会,现今留存最好的护驾法鼓会是挂甲寺的庆音法鼓会。与随驾法鼓所用器具不同,因为是起到保护娘娘的作用,所以器具为:九曲黄罗伞、日月龙凤扇、金瓜、钺斧、朝天蹬、花、罐、鱼、长、蝠、元、扇、庆、茹、艾、方、软对、硬对、高照、门旗、气死风灯,队伍的最后则是前后呼应八字摆开八对手旗,整个队伍的外围也有八十面手旗。 无论是随驾法鼓的道具抑或是护驾法鼓的道具,从其道具的精美程度、场面的恢宏壮阔来看,都显示出了妈祖文化对于天津“法鼓”的影响。
三、农耕文化的渲染
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也极为丰富,而在“法鼓”中的体现则主要分为:好事成双的概念、天圆地方的思想、鼓的应用。
(一)好事成双的概念
“法鼓”出会时,无论是随行人员、器物都是成双成对来出现的,这也就正好映衬了农耕文化中“好事成雙”的思想。如在随驾法鼓中,随驾法鼓的道具和队形排列由一般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头锣背着香袋打头充当领路人:后面依次跟着门旗一对,高照四个、大小软对和大小硬对各一对、大小灯牌各四面;灯牌的后面则是队伍的第二部分,由二锣也叫腰锣领头后面跟着:圆笼(一副)、八方盒子(一副)、软硬衣箱各一副、软硬茶梢各一副、软硬样梢各一副、软硬茶炊子各一副、气死风灯(两个);气死风灯后就是队伍的第三部分,由末锣带头后面跟着:铙和钹(五到八人)、镲歌(四人)、铛铛(四人)、鼓箱一个、大图、九莲灯、手旗(10-40人)、手灯(10-40人)队伍的最后是由十到四十个少年儿童扛着木凳子以备演员休息的所用。无论人数或道具的多少,最后的总数都要是双数,寓意“好事成双”。
(二)阴阳相合的思想
阴阳和合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法鼓”的舞蹈动作之中。“法鼓”从动作来分可以文法鼓和武法鼓两种。文法鼓和武法鼓是相对来说的。文法鼓更多是铙、钹、鼓等这五项乐器配合形成的古代版的“打击乐”,外加一些行会时的步伐,动作幅度小,力度轻。武法鼓则是铙、钹和鼓等这五种乐器配合形成的气势磅礴的音乐配以速起的板腰、折臂、缠头裹脑,双手强有力的击打铙和钹,给人以视觉的冲击,听觉的震撼。文、武“法鼓”是相对来说的,文法鼓不单单是安静舒缓,武法鼓也不只是有激烈昂扬,两者只是更偏向于“文”或更偏重于“武”,各有侧重。文武法鼓的形成与中国人长期形成的“天圆地方”的观念也有关联,中国人讲究和谐,阴阳相谐谓之和。所以有左就有右,有前必有后,有天必有地,有文也必然就会有武。文、武法鼓两者之间相生相伴,和谐共存。
(三)鼓的应用
“鼓”相传起源于原始社会。原始先民对于天地日月和宗教信仰的崇拜使他们把雷声融到“鼓”概念之中,认为鼓的声音可以沟通天地日月祈求农作物丰收。《周易》“鼓之舞之以尽神,变而通之以尽力”则是证明了鼓舞用于祈年祭祖的活动,鼓成了农耕民族的精神力量。而《周礼·地官·鼓人》也有解释说:“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证明鼓舞被作用于军事、农耕等一系列的活动之中。在“法鼓”中鼓是整个“法鼓”队的核心,有着号召全员的意思。此外,听三家的传承人说,每个“法鼓”队的会头,都必须会打鼓,只有鼓打得好,才能够得到队员的认可成为下一任的会头。“法鼓”中鼓的应用切实地证明了农耕文化在“法鼓”中的烙印。
四、结语
“法鼓”作为天津民间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天津人民千百年的智慧结晶,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民间舞蹈,它自身所涵盖的佛教的教义、道教思想、妈祖文化和农耕文化,使之变成了一种综合的艺术门类。这也是天津民间舞蹈共有的特点,舞蹈在用肢体传达情感的同时,还将其附着的文化也传递给了观赏者。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法鼓”中的仪式性特点正在慢慢被遗忘,也正是如此,才需要更多的艺术工作者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1]冯零,光军,永海.天津法鼓[M].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天津卷编委会,1988.
[2]史静,郭平.挂甲寺庆音法鼓銮驾老会——天津皇会[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
[3]冯骥才.刘家园祥音法鼓老会——天津皇会[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4]史静,蒲娇.杨家庄永音法鼓老会——天津皇会[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魏天慈,女,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三年级,中国民族民间舞教育理论方向,研究生学术培养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