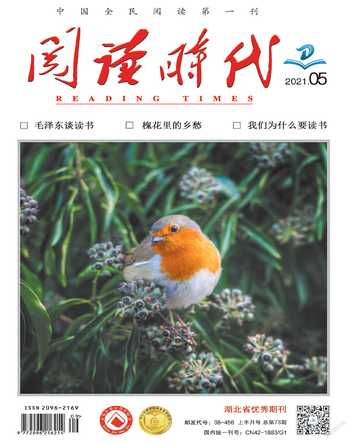韩愈奋斗30年终于在京城买了房
赵冬梅
于人而言,住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当今中国,住的问题困扰了许多人。那么,古人究竟是怎样解决住房问题的呢?住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短期旅行的住宿,一是长期在某地生活的住房。住房可租可买,买又包括买现房和买地自建房。
为短期旅行提供住宿的是两个系统:一个是官营的驿馆,一个是私營的旅店。驿馆设置在官路之上,唐代原则上每三十里设一驿,宋代改为“六十里有驿,驿有饩给”,但是每二十里有马铺、歇马亭。帝制中国历史上覆盖面积最广阔的驿站系统是元朝的,一直向西延伸到欧洲。驿站的“站”字来自蒙古语。“驿”的主要功能是向公差人员提供食宿补给。在驿站住宿需要“介绍信”,唐代的乘驿凭证分为铜传符和纸质驿券两种,铜传符需要皇帝亲批,适用范围很窄,大部分人出差用的都是纸质驿券,唐后期凭借“转牒”(节度使的批条)也可以住驿。朝堂上各路势力你争我夺,此起彼伏,在驿馆中也会上演。宪宗元和五年(810年),监察御史元稹夜宿华州华阴县敷水驿(今陕西渭南华阴市西敷水镇),刚在上房住下,宦官刘士元驾到,他非要让元稹腾让房子。元稹不从,刘士元大怒,破门而入,元稹鞋都来不及穿,穿着袜子往里屋跑,刘士元追上去用马鞭打破了元稹的脸。结果如何?“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唐后期宦官势力之猖獗,可见一斑。
驿馆的房子称为“驿舍”,驿舍按道理讲是临时居所,但也有人长期借住。比如北宋仁宗时的杜衍“不营生事”“不买田宅”,官至宰相,却连一所宅邸都没有。杜衍退休之后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养老,“无屋以居,寓于南京驿舍者久之”。一种说法甚至认为,杜衍死后,其夫人相里氏才拿出压箱底儿的钱买了一所小房子。杜衍身世坎坷,自幼贫穷,这位相里氏夫人却是富人之女,挨到丈夫过世才买房,可见杜家当家的还是杜衍。
除了官营馆驿,道路之上还有私营的旅店。战国时,已经有旅店业。《史记·商君列传》载,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诬谋反,仓皇出逃到秦国边境,“欲舍客舍”,想要住店,结果因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舍人无验者坐之”,收留无证旅行者有罪,遭到拒绝。荒村野店,往往罪案高发。《水浒传》将孙二娘的黑店选址在十字坡,很有眼光。北宋的张咏三十五岁中进士之前,主要靠骚扰已经做了官的朋友过活,这种谋生方式,清代叫作“打秋风”或者“打抽风”。汤阴县令赠给他一大笔钱财,张咏就用驴驮着东西,带着一个小书童往家赶,“行三十余里,日已晏,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张咏一看就知道是个黑店,又不能不住。结果怎么样呢?店主人图财,对张咏下手,遭张咏反制。次日天不亮,张咏一把火烧了黑店,带着书童赶着驴,走了——黑心的店主人已经被张咏用短剑解决。当然,大部分旅店是好的,提供食宿,赚取利润,我们不能像武松那样疑神疑鬼。
上面说的馆驿和旅店都在路上。城市的旅店业也相当繁荣。北宋开封的邸店分为官私两种。仁宗时,官营邸店有房26200间,年收入额约13万余贯。邸店利润极高,所获利润称为“痴钱”,意思是傻瓜都能挣的钱,所以达官贵人争相投资邸店业。
除了短期旅行的住宿问题,最主要的就是长期生活的住房问题。帝制时期官员的任命实行“避籍制”,多半是异地任职;隋炀帝之后,对官员携带父母、子女随行任职的规定不断放宽,古代社会又有投亲靠友的传统,再加上丫鬟仆妇,官员调动通常是一大家子人随行。这一大家子人怎么住?部分官员有公家提供的宿舍,大部分人则是租房住。比如程颐、程颢家,他们的高祖父程羽得到宋太宗的赏识——宋太宗在开封泰宁坊赐了一套宅子给程家。“二程”的父亲程珦就出生在京师泰宁坊的赐第中,但是这套宅子只住过程家三代人。“二程”兄弟小时候一直跟随父亲的调动到处搬家。他们在丹阳租住的是葛家的宅子,给葛家看守这套宅子的老王头夫妇非常不好说话,“前后居者无不苦之”,“二程”的母亲侯氏却很有办法,让这对老夫妇表现出了柔顺善良的一面,等到程家要搬走的时候,王老太太“涕恋不已”,很是舍不得。像丹阳葛家这样靠出租宅子“吃瓦片”的人家,首都和州城府县都应该有不少。
租房子最好租在哪里?同类相求,跟老朋友租在一起是个很好的选择。据说王安石从金陵奉调回开封,先派儿子王雱打前站来租房。人人都说房子不难找,王雱说:并非如此,我父亲认为司马十二丈(司马光)为人做事值得后辈效法,想要在司马家附近找一套房子,这就不容易了。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我抱怀疑态度。但是,司马光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范镇的确是在开封比邻而居。
传统时期的房源也和今天一样,第一看位置,第二看位置,第三还看位置。但位置绝佳的地段价格必然不菲——靠近官员上朝出入宫门的上风上水区域,贵。北宋仁宗时期,宋敏求家住春明坊,宋家藏书丰富且多善本,“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直常高一倍”。
租房住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很难接受一辈子租房住,哪怕土地使用期限只有七十年,还是要拼了老本买房。古人也并不比我们更有出息。只要条件具备,房子还是要买的。唐代的大文豪韩愈在二十六岁时生活还很窘迫,他写信哭穷说:“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无缊袍粝食之给。驱马出门,不知所之。”当然,韩愈的穷跟陶渊明的穷一样,是相对的穷,最起码他还有马,真穷就骑驴了。为了取得相对丰厚的经济收入,也为了积累资历,韩愈后来进入节度使幕府服务,收入大大增加。再加上给人写作碑文、志文所赚取的丰厚稿费,到四十九岁,韩愈终于在首都长安买了房。这座房子有中堂,这是祭祀和举行典礼的地方,“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有一个很宽大的院子,“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东堂风景很好,“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北堂是女眷居住活动的区域;此外还有南亭,南亭外面是菜地,“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院子的西边没怎么盖房子,“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
韩愈把这所房子视为自己三十年辛苦奔波的最大成就,写了一首《示儿》,向孩子们表达内心的骄傲与喜悦:“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三十年奋斗,韩愈终于在首都买了房,后来他还在城南置办了一个小别墅,当然,韩愈是在长安城的这套宅子里寿终正寝的。
买房子、盖房子,追求高大上,这一点,古今之人概莫能外。把这种追求发挥到极致病态的,就是那些权势上的暴发户。比如唐代杨贵妃的兄弟姐妹們,仗着皇帝宠爱,“竞开第舍,极其壮丽”,比赛盖房子,看谁的高级,一间大厅的花费,动辄超过千万缗。更为变态的是,房子盖好,发现别人家盖的竟然有超过自己的,立刻推倒重建。敢于“平明骑马入宫门”“淡扫蛾眉朝至尊”的虢国夫人作风更是豪横。一日,她率领工匠闯入韦嗣立的宅子,“即撤去旧屋,自为新第”,扔给韦家十亩荒地了事。这韦嗣立也是当过宰相的人,他与中宗的韦皇后是同姓疏族,被强拉进韦后的外戚团队。想当年,韦嗣立家的骊山别业落成,中宗亲临祝贺,赏赐优厚,给韦家别业所在地赐名“清虚原幽栖谷”。韦皇后倒台之后,韦嗣立受到牵连,在政治上一蹶不振,“幽栖”不能。此时,韦嗣立已死,韦家全无势力可言,所以虢国夫人才敢强拆他家的宅子。权力的蛮横,权贵的野蛮丑陋,由此可见一斑。
宋真宗朝的“圣相”李沆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文明风范。李沆做宰相,在开封盖房子,大厅前面建得很窄,仅能容一匹马掉头。有人批评太寒碜了,李沆笑着说:“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太祝、奉礼”指太常寺太祝、奉礼郎,是官僚子弟恩荫入仕的常用官衔。李沆的意思是,倘若子孙无能,只能靠父祖荫庇做个小官儿,那也就无所谓了。宋朝的高官以俸禄优厚著称,钱不是问题。后来,夫人又劝他买新房,李沆说:“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李沆的回答,显示了佛教对他的深刻影响,也透露出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信息。
李沆的代际传承观念,并非绝无仅有。宋初的武将郭进的表达更加直率,他在开封城北的大宅子落成,举行宴会庆祝,“乃设诸工之席于东庑,群子之席于西庑”。让建筑工人坐上首,自己的儿子坐下首。有人问他:“诸子安可与工徒齿?”郭进指着工人们说:“此造宅者。”又指着儿子们说:“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
晚唐五代的战争和政治动荡将世家大族涤荡殆尽。从宋朝起,国家不再干预土地兼并。科举向几乎所有男性开放,朝廷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员,个人奋斗、科举成功成为家族盛衰的决定性因素。人的阶层流动性增强,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都是可以获取的,也是可以失去的。有人向上,就有人向下。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必须持续奋斗,也必须有一颗平常心,能为向上的欢呼,也要能接纳向下的。
(源自《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责编:王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