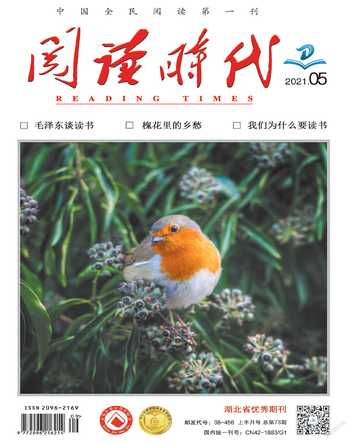我的阅读引路人之暗夜灯火
谢越清
夜幕沉沉,寒风呼啸。关上窗户,我坐在书桌前,翻开《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书厚过砖头,600多页,二十五章。昨夜一气看到第十二章“中国的昨日与现在”,今晚接着行云流水地往下读,争取在明夜啃掉这块沉甸甸的砖头。速读的习惯和能力由来已久,是我上初中时被父亲单位的“大笔杆子”逼出来的。也是他,把我引上的阅读之路。
我上的中学就在我的出生地。它是全县最偏僻的一个农耕小镇,也是公社“首府”所在地。那段时期,“教育闹革命”,数理化被取消,史地课听说过没上过。主课变成了学习并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学习“两报一刊”社论(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写学习心得和大批判文章、出宣传墙报、刻钢板油印宣传小报,此外就是到校办农场劳动。
渴望找书来看。可家里除了一箱我小学时看烂了的连环画,再也找不出任何称得上是书的读物。那三五个玩得来的同学家也是如此。我从上小学起就不喜热闹,不好扎堆,更不会花样地玩儿,找不到对胃口的书看,自然觉着百无聊赖。
我的阅读引路人,就是在这个时刻出现的。
他是我父亲所在单位的同事,一大家人租住在我家正对面的一栋老宅子里。由于隔街相望,加上又同单位,他妻子和我母亲以姐妹相称,两家的孩子们也往来密织。只有他,从未来我家串过门。我倒是不觉得奇怪,因为平日里就罕见他出来闲坐闲聊。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一点耳闻: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地主家庭,1949年前中学毕业,在单位专事写材料,回家后还通宵达旦地写,人称“大笔杆子”。
对他的印象也仅限于偶尔一瞥:戴一顶藏青色的旧软呢帽,穿一件洗得泛白的蓝色中山装,衣服的左上口袋里总插着两支钢笔;烟不离手,面色苍白,少言寡语,严肃多过笑容,喉结大而凸显,一口浓重的湖南普通話。我是一直默默地仰视着他的,因为他是街上惟一的笔杆子。
他和我的零距离接触是我读初二的一个三九天。晚饭过后我站在家门口的青石板上莫名地发呆,他突然出现在我跟前,又突然凑近我的耳边,突然问我最近看了什么书没有。我顿时慌了神,回应得吭吭哧哧:读了啊,背毛主席语录100条和“老三篇”。他听罢长“喔”了一声,然后不声不响地转身走了。
他的背影已消失在暗淡的屋子里,我却还一头雾水。
两天后的傍晚时分,他又来到我家门口,朝我招手。夹在他手里的烟,火星闪闪烁烁。我出门跟着他,进到他家。他点亮餐桌上的煤油灯,却把我带到离灯一丈来远的天井边。
星空透过天井投下一方暮光,朦朦胧胧。
天井边放了一张木条凳。他侧身坐下后,示意我坐在他身边。第一次这样近的挨着他坐,仿佛坐的不是一条木凳,而是一根电线,浑身上下极不自在。
见我一副紧张样,他露出和蔼笑颜,轻声说:“我妻子和大女儿经常说起你,说你很喜欢看书,作文也写得不错。”
我点了点头。
“你这个年龄是最该多看书的时候了。”
我又点了点头。
“读过《古文观止》吧?”
我晃了晃脑袋。心想,什么书?听都没听说过。
“唐诗宋词呢?”
我又晃了晃脑袋,感觉脸上有些发热。
一阵沉默。
他接连吸了几口烟,望着那边的煤油灯,喉结缩动了几下,紧抿的嘴把脸上的肌肉拉成了几条山脉。
“想不想看长篇小说?”他转向我问。
“想!”
他起身进到一间房里,过了会才拿来一件破旧的衣服,先朝大门口看了一眼,然后从衣服里摸出一本用牛皮纸包住的书,递给我,说:“这是我找别人借的,你赶紧先看,三天以后务必还给我。”
我即刻把书翻到扉页,朝向煤油灯那边,看清了书名。
“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听说很好看!”我惊喜地把书贴在胸口。
哪知他忽地从我手里把书拿了过去,面带微笑,却用严肃的口气说:“这部小说你只能在家看,不可带到学校去,也不可让任何人知道。做得到吗?”
他盯着我,目光如炬。
“做得到!”
“还有,”他顿了下,把头朝向大门,声音小得近乎无力,“如果万一被人揭发检举了,你不可说是我借给你的。你保证做得到不?”
“我保证说是我自己的书,是路上捡的!”他话音刚落,我便急切而干脆地回答,生怕他变卦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阅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保尔与冬妮娅的恋情、保尔在战火中成长的命运及陌生的苏联风情,使我大开眼界。我用两个半夜晚读完了它,感觉像是从一条小舟登上了一艘巨轮,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乘风破浪。
自此,长篇小说犹如磁铁,将我紧紧地吸附其上。按时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给他后,我又从他那里借了好些大部头:有《牛虻》《红岩》《苦斗》《子夜》《复活》《死魂灵》《三家巷》《红旗谱》《激流三部曲》)《静静的顿河》《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几十部。这些小说都被贴上“毒草”的标签,无论是阅读还是收藏它们,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所以,每借来一本书,我都只在夜晚躲进房里阅读,如同在干见不得人的事,始终没让任何人有丝毫察觉,包括我的父母和姐姐妹妹。
每到晚上7点多,小镇沉睡了,我就回到我一个人住的后屋房间,把煤油灯灯芯捻小,房门闩牢,再拿一根木条堵住房门底下的缝隙。觉得万无一失的安全了,才从床板底下取出裹着“造反有理”宣传画的大部头,坐到条桌边,一页页默读,冷得不行时,就一边搓手,一边往手上哈气。常常是煤油灯下读半夜,再钻进被窝打着手电看半夜,一目十行地扫荡,至多三个夜晚,一部长篇就看到了封底。小说是看完了,但进入我记忆里的,顶多就是大概的故事情节、几个主要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待到看《红楼梦》,一目十行就失效了,“阅读期限”把我阻挡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关隘外,我难受至极。
《红楼梦》是他借给我的最后一部长篇,也最难读。通篇的半文言文还勉强读得下去,难倒我的是生僻字、诗词对联。生僻字多如牛毛,我不得不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字典;大观园完全就是个制造诗词对联的大工厂,诗词对联动辄脱口即出,美得云雾缭绕,可其中的生字,尤其是典故,把我看得云里雾里。当第三个黑夜被晨曦驱逐后,书才看了不到一半。我不得不踩着点把书还给他。
早上去他家还书时,我一直低着头,生怕他看見我羞愧的脸。
他还是把我带到天井边,像往常那样收起书,先拿回到那间房,再空手出来坐下,接着便是往常同样的问号从他嘴里缓缓而出:“这部小说怎么样啊?”我以前的回答每次都很快,“好看”“过瘾”“很有意思”……这次我却不知如何回答,好半天才憋出三个低音字:“没看完。”头仍然低着,不敢看他,也不敢想象他的表情。“没事,以后有机会再看。”我听见的是他温和的声音。
一只手落在我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接着又是他的声音,缓慢、温和而有力:“《红楼梦》值得反复读,还有你看过的《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和外国名著,以后也可以再看。至于其他的长篇,一目十行,囫囵吞枣就行了,甚至不看也没什么遗憾。”
我这才抬起头。天井上空现出一方蔚蓝。朝阳穿过天井飘逸而下,在他的身体右侧镶出一道橙边,映红他疲惫的脸,照得那两支钢笔的笔帽熠熠生辉。
“为什么?”我盯着钢笔帽,怯怯地问。
他吸了一大口烟,那烟头,灿得耀眼。“经典作品是被漫长的时间筛淘出来的,不是谁指定的,所以叫传世之作。读传世之作,才能学到真正的东西。”他看着我说:“以后你要多读书,特别是要读经典。我总觉得,现在不让看的书,迟早有一天是可以自由地看的。”
他的这番话,我从未听老师和其他人说过,感觉新鲜又豁亮,似乎明白了以后该怎样看书,同时,心里也生出了对那个“可以自由看书”的日子的渴盼。
自那个凛冬保尔和冬妮娅给我启蒙后,我的世界里便只有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两年的高中期间,我从几个要好的文学迷同学手上又借阅了不少书,读过的有沈从文、老舍、林语堂和冰心,还看过《林海雪原》《青春万岁》《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借阅的方式是从看过的地下工作者电影里学来的,即“单线联系”(我只知借书给我的人,从不打听书的主人),回家夜读,绝不传阅。毕业多年后聊起同窗往事,我才从他们嘴里知道,那些“毒草”除了有各自家族的长辈藏下来的,竟然还有一些是在外地当红卫兵或造反派的亲戚送的。一个老同学说,他的沈从文和老舍的书是他表哥送的。表哥当时在县城一家工厂上班,加入了造反派组织,也是个文学迷。送书给他时说,这几本书是他们在县一中一个语文老师家抄来的,因为太喜欢,他就悄悄地藏下了。
当插队知青后,我更是四处找人借书看。我所在的生产队地处公社边缘,特别偏僻,十来户人家竟有一大半与我同姓,他们视我为族人,家里只要藏着书的,大多愿意借给我看。我一人住在田野中央的一间废弃的仓库,又有书看,自然是乐不思家。那一本本大部头,如朋友和伴侣,陪伴着我;像空气和粮食,滋养着我。我的单调而狭小的空间,被书接力开凿成一个无限辽阔且精彩的世界,其间风光迷离,蜃楼叠现,令我陶醉不已。
责编: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