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见星河想见你
幸有幸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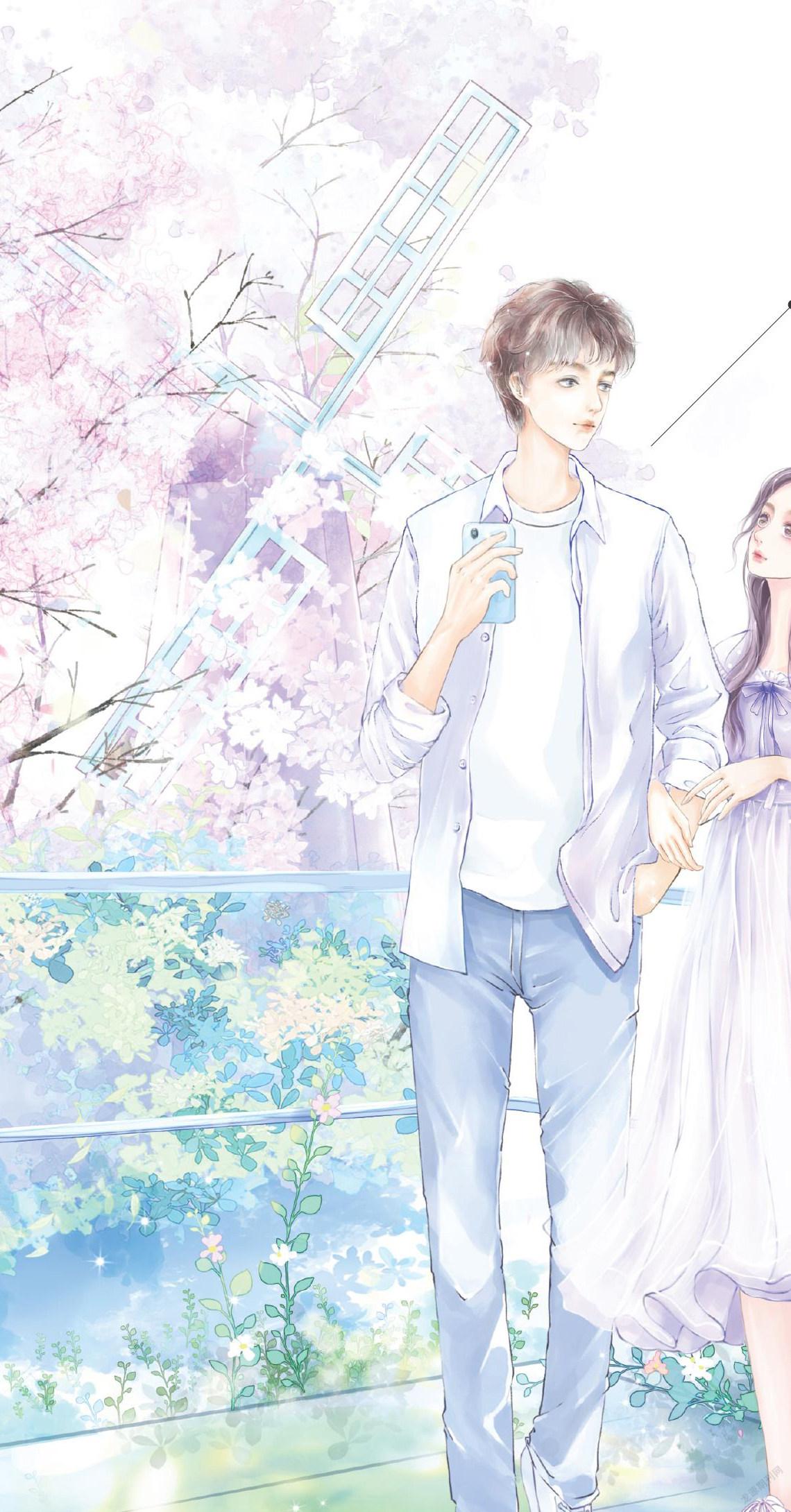
1
一场雨过后,栽在院子里的海棠花便悉数绽开了。
宋幼棠推门进来时钟谬正蹲在石阶上捣鼓中药,药材铺了满地,几乎让人下不了脚。
直到钟谬将最后一把芍药装进袋子后,他才闲散地转过头,发现了在门口无措地站了半天的宋幼棠。
他们相互打量了对方几眼,最后还是钟谬沉不住气,起身向宋幼棠走去。
没等钟谬问话,宋幼棠就磕磕巴巴地开口:“你好……我来找钟老医生配些药……”
钟谬上下瞥了一眼面前的人,最后将目光停留在她蜡黄的面庞上。
钟谬有意耍弄她,他微微俯视着怔在原地的少女,语气里带着些许遗憾:“真不巧,我爷爷昨天刚出远门去了。”
因为挨得极近的缘故,宋幼棠可以清晰地闻到钟谬身上沾染着的中药味。
宋幼棠从未被人这么直勾勾地盯着过,脊背顿时僵了。她后退了几步,掏出背包夹层里的药方,有些气馁地说道:“不对呀,我上次来的时候他还嘱咐我今天要记得过来拿药呢。”
钟谬夺过那张药方,擅作主张道:“让我看看上面都写了哪几味药,配药这事我也会。”
念了几种药名后,钟谬皱起眉头,小声嘟嚷:“钟老头怎么也不把配药分量写上去?真是爱偷懒。”
没等他抱怨完,院子里便传来了一阵呵斥声:“钟谬!门口的麦冬都要晾潮湿了,你还不快收进去!”
“你不是说钟老医生出远门了吗?”宋幼棠仰着头问他。
“这不是临时回来了嘛!”钟谬丝毫没有谎话被拆穿的尴尬,面不改色地回她。
趁着自家爷爷在拿药、看诊,钟谬生起了逗弄宋幼棠的心思:“哎,听说你是学跳芭蕾舞的,看你气色这么不好,那舞蹈学校怎么也肯收你?”
彼时的宋幼棠还没学会回呛他,只独自坐在木凳上生闷气。
瞧着她愤懑的模样,钟谬却笑得十分愉悦。
钟谬第一次见到宋幼棠,还是在几个月以前。
钟谬所在学校的对面就是一条商业街,十六七岁的学生正是贪玩的年纪,放学了谁也不愿早回家,多半会在附近溜达一会儿才回去。
考完期中考试的那天,钟谬被伙伴们拉去商业街看演出,他们去得早,舞台上只有隔壁艺术高中的芭蕾舞蹈队在排练。
大家兴致缺缺地看了几分钟便起身要走,只剩钟谬一人看着舞台中央发愣。台上的舞者个个身姿挺拔,眉眼间大都蕴着藏不住的灵气。钟谬却独独记住了第一排角落里那个面色微黃,脖颈纤长的少女。
那天之后,他放学回家总会多绕几条街,去艺术高中那条种满了海棠花的小道。听着围墙内传来的练舞节拍声,他总会想,那只丑小鸭此刻是不是也在排练室里反复练习着某支舞曲。
2
受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钟谬自小就对中药颇有研究。
别人还在玩泥巴、卡丁车、跳长绳的年纪,钟谬就已经能将上百种中药偏方倒背如流,说起各种中药的功效时更头头是道,同龄的邻居小伙伴们有时会打趣着喊他:“钟谬老古董,钟谬老古董!”
每每这时,钟谬总会拿起院子里浇花的喷壶追赶他们。只是这天,钟谬刚拿起喷壶往外跑时便和宋幼棠撞到了一块。
冷不丁的,喷壶里的水浇了宋幼棠满头,水流顺着她的发梢一路往下淌去,钟谬手忙脚乱地将喷壶搁置在地上,迅速地跑回屋内找了条干毛巾。他努力扯出一个笑,试图化解这尴尬气氛。
宋幼棠接过毛巾,并不提这茬,只笑眯眯地问他:“钟老医生今天在家吗?”
“不,不在。”不似头次相见时的调皮,钟谬这次口吻认真,像是怕面前的人不信,他又补充道,“是真的,骗你又没有糖可以吃。”
宋幼棠“嗯”了一声,从帆布袋子里翻找出一张药方和一袋空药包,递到钟谬面前:“上回你不是说你也会配药,那就请你帮我看看。”
钟谬连忙摆手,上回纯粹是想逗弄她,配药这事他可不敢掺和,一来怕犯事,二来怕挨骂。
“你再等等,钟老头大概还要一个小时才回来。”
宋幼棠看向屋内墙上挂着的大挂钟,着急地说:“我下午两点还要排练舞曲呢,从这里回练功房都要一个多小时呢……”
听了这话,钟谬眉头微皱,最后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给钟老头打电话,让他远程配药。
“蝉蜕和山豆根各十克,北杏十五克,桔梗二十克……”钟谬嘴里念叨着自家爷爷配的中药名称与分量,又将那些药材悉数装袋,等他抬头,恰好和宋幼棠的视线撞到一块去了。
递给她药时钟谬不自然地甩了甩袋子:“喏,药罐子。”
宋幼棠气得红了眼睛,而后又干巴巴地回了一句:“才、才不是。”
钟谬抬头望了一眼时间,声音顿时拔高了一个度:“还有二十分钟就两点了。”
“要是迟到的话,老师会在原先的训练里多加两小时的……”宋幼棠皱着眉,站在原地干着急,过了两三秒,她又抱着几分侥幸心理问他,“你家的钟表会不会坏了?”
对上她澄澈的眼睛,钟谬过了半晌才悠悠回话:“绝对不会。”
这下,宋幼棠彻底苦着脸了。
从学校出来时,她是估摸好时间后才掐着点出门的。谁知道恰逢周末,赶上到交通高峰期,耽误了不少时间。想到一会儿免不了被领舞老师批评,宋幼棠闷闷不乐地垂下头。
宋幼棠不知道钟谬用了什么理由便让久不批假的老师同意放了她一天假,她问了钟谬几遍,见他不答,她索性站到海棠树底下看钟谬熬药。
方才钟谬拿过她的药说要替她熬制,她先是犹疑着打算拒绝,谁知钟谬说完话后便到屋里端出了专门煮中药的锅炉。从起火到熬制药材,每个步骤钟谬都做得娴熟无比,从锅炉中冒出的雾气几乎遮住了他的脸,钟谬挥动着手里的蒲扇,模样专注认真。
宋幼棠站在树下,目光落在他微微汗湿的衬衫后背,一时间,她看得有些恍神了。
一阵风拂过,院子里的海棠树枝叶摇曳,花瓣缓缓坠落,有零星的几片花瓣掉在了宋幼棠的肩上。
等钟谬回头,正好看见了这一幕,他停下挥动蒲扇的动作,瞧着宋幼棠潋滟的双目,一时变得拘谨无措起来。
3
从春天到夏初的距离,钟谬数了一下日历表上被他圈起的日期,正好两个月。
这也是钟谬给宋幼棠送饭的天数。
有一天给宋幼棠配新药方时,钟老头对宋幼棠的母亲念叨了句,药补不如食补,营养均衡,气色才会有所好转。听了这交代,宋母皱起了眉。她工作忙,常常出差辗转于不同的地方,明显是没空打理宋幼棠的饮食。沉思了片刻后,她问:“钟医生有合适的营养师推荐吗?”
在一旁整理药材的钟谬瞥向宋幼棠,见她表情淡淡的,看来是对这样的事早已见怪不怪了。
见钟老头翻找电话簿,钟谬踌躇片刻后开口道:“咱们家不就有一个现成的营养师?”
钟谬指的是自己的奶奶,林笠。钟老头还未从医院退休前,许多就诊病人的一日三餐都是林笠按照营养食谱严格调配的。
钟谬这话点醒了钟老头,问了宋母的意见后,他当即拍板决定让林笠负责宋幼棠的日常饮食。
当天晚上,钟老头又想到了一个问题:谁来送餐给宋幼棠吃?
钟谬往碗里夹了块焖豆腐,假装不经意道:“我知道一条近道,正好可以顺路经过。”
怎么会顺路呢?从他们学校到舞蹈附中,就是搭乘公交车都要转上两次车。
从第一次送餐的那天起,钟谬总是提前一个半小时起床,搭乘首班公交车,而后转一次车,下车后一路狂奔到宋幼棠学校。他赶到时,额间和发梢总是布满了汗。起初宋幼棠并没在意,时间长了,她便察觉出了些端倪,直勾勾地盯着钟谬。
钟谬有些羞赧,他别过脸,摆出一副神情自若的样子,找了个蹩脚的借口:“我最近在练习长跑。”
宋幼棠并不拆穿他,只戳了戳他的肩胛,变换着音调喊他名字:“钟谬,钟谬。”
但钟谬也并非次次都能准时将饭盒送到宋幼棠手里。有一回放学,他被老师安排留下来给跟不上功课的同学讲题。钟谬耐着性子将解题步骤写在草稿纸上,同学仍不懂,他看了一眼挂钟上的时间后,气得将撕下来的草稿纸揉成一个纸团,丢到桌子抽屉里。
等钟谬赶到舞蹈附中时,只有一楼练功房的白炽灯还亮着。隔着半开的玻璃窗,钟谬看到宋幼棠站在大厅中央,随着音乐节奏踮起脚尖一下一下地跳动着。
那是钟谬第一次近距离地注视跳舞的宋幼棠,他听见心里“嘭”的一声,像是烟花绚烂地绽放于天际。
他们坐在高高的石阶上,头顶上是亮得晃眼的路灯,宋幼棠拉开饭盒外的保温袋,并不过问钟谬迟到的事。她夹了块胡萝卜吃,含糊不清地说:“下周末我们要跳《胡桃夹子》,这可是我首次领舞,排练了好久呢,你不许不来。”
钟谬的手臂撑在上一级台阶,过了好半晌,他才应允了一句:“好。”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宋幼棠这才认真吃起了饭。从他们坐着的位置仰头望去,可以看到天上的那轮弯月。
钟谬将两手的拇指与食指指尖对在一起,合成一个圆,孩子气地说:“你看,这样就把月亮圈住了。”
宋幼棠也学起了他,只是,她偏过头,将圆环对着钟谬的脸,学着他的口吻道:“你看,这样就把钟谬圈住了。”
路灯将他们的影子拉长,钟谬收回手,抬头望着月空,在心底许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心愿:希望今晚的月亮不要西沉。
4
钟谬趕到场时,演出正好开幕。观众席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他蹑手蹑脚地挑了个不显眼的位子坐下。
从他的角度望去,并不能完全看得清台上表演者的动作,只能隐隐看个大概。宋幼棠一谢完幕,连妆都没来得及卸便跑到钟谬跟前,歪着脑袋问他:“我刚刚跳得怎么样?”
她的话里带着不加掩饰的期盼,钟谬笑着回应她:“嗯,跳得很好。”
宋幼棠揪了一下钟谬的手臂,撇嘴道:“你糊弄谁呢?我刚刚都注意到了你在发呆。”
见被她戳破,钟谬不自在地摸了一下鼻子,找了个借口:“我还可以回去看电视回放,不是说晚上的表演和电视台同步直播。”
宋幼对钟谬的说辞显然不满意,她把手背到身后,闷声闷气地说道:“在电视里看和在现场看的视觉效果又不一样。”
钟谬被她说得没辙了,摊手无奈地说道:“那总不能让你再跳一次给我看吧?”
这话才刚说完,宋幼棠一把拉起他的胳膊,往练功房所在的方向跑去。
还是在一楼那间练功房,《胡桃夹子》的背景音乐一响起,宋幼棠便展开纤细的双臂,身体灵活地旋转跳跃起来。她抬头露出长长的天鹅颈,做出鹤立式舞姿,灯光照在她脸上,像是梦一样美,钟谬怔怔地盯着她看,那翩翩起落的舞步,仿佛踩在他的心尖上,一下一下地拨动着他的心弦。
这是,宋幼棠为钟谬一人跳的舞。
舞曲终了,宋幼棠脚尖落地,瞄了一眼钟谬,对上他澄澈的眼睛。宋幼棠笑得有些腼腆,巴掌大的小脸上飞着一抹绯红。她眨着乌黑的眼睛,弯起嘴角再次问了他那个问题:“我刚刚跳得怎么样?”
钟谬不答,只安静地盯着她看,好半晌后,他才后知后觉地鼓起掌,再次回答:“嗯,跳得很好。”
宋幼棠带钟谬参观他们学校,走了一段路后,钟谬姿态悠闲地靠在木栏杆上,听宋幼棠说小时候练舞的事。她并非本市人,当听到她说当初选择这所舞蹈学校只因喜欢学校里栽种的大片海棠花时,钟谬嗤笑道:“你也太幼稚了。”
宋幼棠侧过身子,睁大眼睛瞪他,反驳道:“才不是呢。”
过了几秒,宋幼棠再次开口,语气认真:“第一眼相中并选择的东西,哪怕有一天不喜欢了,但是想起做决定的那一刻,也是开心的。”
夜色宁静,透过树梢可以望见皎洁的月亮,钟谬觑她一眼,眉眼含着笑意,随口说:“我想到了一首诗。”
“不会是‘床上明月光’这样的学前诗吧?”宋幼棠打趣,说完便咯咯笑了起来。
钟谬当即反驳道:“才不是——”
钟谬收起吊儿郎当的模样,背起从前学过的诗:“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佳期旷何许,望望空伫立。”
背诗背出了伤感的气氛,宋幼棠踢了踢钟谬的球鞋,仰头看他:“钟谬,现在还是夏天呢,这诗说的明明是秋天,不许你背这首煞风景的诗。”
她这话把钟谬逗笑了,他捏了一下她脸颊上的软肉,故意说道:“好,好,不背了,留着秋天的时候我再背一次。”
宋幼棠拽起他的衣角,愤愤地试图拍他,钟谬躲开。过了一会儿,只听她气呼呼地改了一句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钟谬。”
钟谬不但没恼,还笑得格外飞扬。草丛里飞出几只萤火虫,他随手一指,对宋幼棠做了个“嘘”的手势,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看闪着点点莹白光亮的萤火虫在草丛里飞舞。
也不知过了多久,宋幼棠忍不住偷瞄了一眼钟谬,好奇地问道:“你会捉萤火虫吗?”
钟谬点头,声音慵懒:“但我不会去抓它们,再把它们放进玻璃瓶里。就让它们在大自然里自在飞翔多好。”
听了他的回答,宋幼棠一点点儿地弯起嘴角。
钟谬回去时,宋幼棠站在路灯下目送他,等他走了一段距离,宋幼棠忽然喊他:“钟谬,明天见。”
钟谬回頭望去,宋幼棠笑着朝自己挥手,晚风拂过她身后的那片海棠林,摇落了不少树叶。
钟谬也扬了扬手,在心里轻轻说道:明天见,以后的每一天都要见面。
5
这年的冬天来得急,秋天几乎是一闪而过。
宋幼棠收好钟老头开的中药后,对一旁正在给药材分类的少年说:“钟谬,我们去逛逛那栋新建的大楼好不好?听说最近好多人都去那儿打卡了呢。”
钟谬将大衣领子拢得更高,头也不抬,冷声拒绝:“不去。”
平日里总在他耳边叽叽喳喳说个没完的人忽地噤了声。钟谬掀起眼皮望她,只见宋幼棠垂着头,失落地抿着唇。
“等我把剩下的药材分拣好就去。”钟谬悠悠开口。
宋幼棠的眼睛登时闪亮起来,她跑到他跟前,脸上堆满了笑,叫唤着他的名字:“钟谬,你真好。”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栋建筑大楼原先是一个废弃的煤工厂,开发商邀请建筑师对场地肌理进行重塑,原来工业遗迹被改造成了游玩新场地,还做了生态修复。”场地介绍人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这也算是一种脉络转生的方式。”
他们从内逛到外,宋幼棠拉着钟谬的衣袖,将看到的新奇事物指给他看。将她的雀跃尽收眼底,钟谬问她:“是喜欢建筑还是喜欢这里?”
“喜欢建筑。”宋幼棠回话,眼睛亮亮的。
她眺望着映红了半边天的晚霞,自顾自地说道:“我爸爸他们家的人都是建筑师,以前我看得最多的就是和建筑有关的书籍了。年纪小的时候不大识字,就看图,一张张看过去,怎么也不看腻,那时的心愿也是学建筑。后来爸爸和我们分开了,妈妈把家里的那些书全丢了,我也学了跳舞。之后在路上看到喜欢的建筑物,只敢匆匆瞧上一眼,不敢多逗留,我怕妈妈生气,也怕自己失落。”
钟谬望着她被夕阳笼照着的侧颜,暗暗做了一个决定。
宋幼棠来找钟谬时,学校门口人头攒动,但宋幼棠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人堆里的钟谬。
“你骗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近道。”一挤到钟谬面前,宋幼棠便嘟嚷道。
这是她头一回从自己学校去钟谬学校,前后转了几次公交车后她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钟谬每次来找她,都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得知钟谬刚刚进行了模拟考,宋幼棠问他:“你明年夏天打算报什么学校?”
“同济。”钟谬很快回答。
“那正好在本市。”她又小声问,“同济的药学院有中医学吗?”
“我不打算学中医。”钟谬平静地说。
宋幼棠“啊”了一声,显然有些诧异:“你父母和钟老医生他们都打算让你学这个专业,你之前不是也有这个意愿吗?况且你还有中医学的基础……”
宋幼棠凑到他跟前,神秘兮兮地说:“哦,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你现在的成绩和往年的录取分数线差了一大截。”
“你就别乱猜了。”钟谬打断她的话,“怎么突然来找我了?”
宋幼棠这才想起正事,她从背包里掏出一张卡片:“快恭喜我吧,我被选中去茱莉亚学院当为期半年的伴舞了。”说着,她又自豪地扬了扬下巴,“同届的舞蹈生只有我被选中了呢。”
吃晚饭的时候,钟谬随口将这事告诉了家里人,宋幼棠瞪了一眼钟谬后害羞地低下头扒饭。
钟谬有一间独立的书房,这还是宋幼棠头一次踏足。宋幼棠好奇地东瞧瞧西看看,看了一圈后,她注意到书柜里有几本书被钟谬藏在了夹层里,有本书还露出了封面平面图的边缘。
见她要拿出来,钟谬赶忙拿身子挡住,脸上挂着心虚的笑:“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他不让看,宋幼棠就偏要看。她捏了一把钟谬的手臂,趁他吃痛松懈时,她抽出夹层里的书一看,都是建筑类书籍。
宋幼棠默不作声地望着他,钟谬漆黑的眸子里透着些许窘迫,支吾道:“原本打算送给你,给你个惊喜的……”
宋幼棠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见她的关注点转向别处,钟谬这才轻轻地舒了口气。幸好她没翻开书看里面的内容。毕竟,没有人会在要送人的书里胡乱涂写。
6
钟谬一接通宋幼棠打来的越洋电话,里面便传来她熟悉的声音:“钟谬!为什么你的电话总是打不通!”
被质问的人歪头夹着手机,腾出手把地上晾晒药材的塑料布铺平,他耐着性子解释,声音略显沙哑:“我在乡下的中药种植基地帮忙呢,这里信号不好。”
得知钟谬这个寒假因为和家里吵架被送到种植基地,就连生活费也被中断了后,宋幼棠差点儿跳脚:“你犯什么错了?”
“关于报志愿的事。”钟谬是不紧不慢地回答。
宋幼棠还想继续问,他却不肯多说,最后因为信号不好,电话自动挂断了。
寒假结束前,钟谬才被接回家。原本白净的少年晒黑了不少,衬得他的眉目愈发锐利了。坐在驾驶座上的父亲问他是不是仍旧执拗地想学建筑,钟谬望向车窗外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嘴角挂着温和的笑,再次肯定地回答了父亲的问题。
高考结束后的一个月,宋幼棠的伴舞表演也正好划上句号。她来找钟谬时,他正趴在院子里的桌上打瞌睡。
宋幼棠轻手轻脚地凑到钟谬面前,专注地打量他,心底满足又甜蜜。这样凝视了片刻,宋幼棠伸手扯了一下他浓密的睫毛,钟谬皱了一下眉,很快清醒。
睁开眼睛看到是她,钟谬抓起一支签字笔,拿笔帽端戳了戳她的额头,宋幼棠龇牙朝他扮了个鬼脸。
宋幼棠又好奇地问了几遍钟谬报了哪个学校,学的什么专业,钟谬不答话,只侧身垂着眼睫不理会她。
钟老头听到声响从屋内走出,替她解了谜。他的语气听着十分轻快,又带着几分遗憾:“从此以后我们家少了个中医,多了个建筑师。”
听到这话,宋幼棠怔了怔,大脑像是停止了转动一般。
“钟谬,”她喊他名字,叫得严肃又认真,“寒假时你和家人吵架就是因为这件事对不对?”
气氛变得古怪起来。宋幼棠想起自己曾对他说过的话,想起钟谬书柜里那些被他藏起来的书,想起来找他时看到的那些建筑图纸,想起她提起志愿时钟谬的一言不发……泪水在宋幼棠的眼眶里打着转,她的手蹭到桌面上的书,其中一本掉落了下来,扉页上赫然写着:实现你未能完成的愿望就是我的心愿。
宋幼棠用恶狠狠的语气掩饰语调里的颤音:“钟谬,你怎么这么傻啊!”
钟谬拍了拍她的头,半晌才蹦出一句:“宋幼棠,你哭得鼻涕泡都冒出来了。”
被他这么一说,宋幼棠这才停止抽噎,嗔怒地喊他:“钟谬!”
夏夜蝉鸣声聒噪,路旁的香樟树散发着清新的香气,钟谬送宋幼棠回去。他们缓步走过大街小巷,分别时,宋幼棠在后头喊他:“明天见,钟谬。”
7
谬然建筑事务所成立的那天,邀请了某舞蹈工作室来表演,本市可供选择的演出工作室就有很多,事务所的成员弄不懂钟谬为什么非要指定邻市的这家。
演出结束后,宋幼棠听到有人在喊“钟谬”,她惊得放下整理到一半的舞裙,倏地回頭望去,正好撞上了钟谬定定注视着自己的目光。
同宋幼棠惊诧的反应不同,钟谬走上前自然而然地帮她把舞裙整理好。半晌后,钟谬开了口:“以前你跟我说不考第一舞蹈大学,要去巴黎的芭蕾学校,是真的吗?”
宋幼棠的身子僵了僵,对上钟谬探究的眼神,佯装镇定道:“真的。”
钟谬“哦”了一声,不可置否,他垂下眼帘,又问她:“那你后来怎么没有联系我?”
宋幼棠装作若无其事,用略显轻松的口气说:“那不是学业繁忙,再加上……”
钟谬挡住宋幼棠看向别处的视线,他扯出一个笑,打断她的话:“宋幼棠,都过了四年,你用的借口还是一如既往地烂。”
钟谬想起往事,失神了好一会儿。
那段时间钟谬正在着手设计一个园林建筑的平面图,而宋幼棠也在忙着准备参加舞蹈大学面试的事,他们总是约在学生街的一家小吃店匆匆见上一面。有一天,钟谬一见到宋幼棠,就注意到她眼眶通红,俨然是刚哭过的模样。
钟谬刚想问她,放在桌上的手机蓦然亮起,传出收到新邮件的提醒音。
宋幼棠看到那封邮件是南加州建筑学院的交换生邀请信。先前她听钟谬提过,交换生的名额只有寥寥几个,很不容易申请到。
“眼睛怎么红红的?谁惹你不开心了?”钟谬关掉屏幕,扭头问她。
“没啊。”宋幼刻意用平淡的口吻反驳。
“钟谬,”宋幼棠试探着问道,“如果我没有考上第一舞蹈学校……”
“说什么傻话呢?你一定会考上的。”
宋幼棠低下头:“万一呢,你也知道,我文化课不太好。”
“你要是没考上的话,我就不去南加州了,陪你一起等明年。”
见钟谬语气坚定,宋幼棠收回原本想说的话,换了个说辞,告诉他:“其实我之前没有去第一舞蹈学校面试,因为我打算去巴黎学芭蕾了。”
钟谬没想到的是,他去了南加州后便和宋幼棠失去了联系。等他回国才得知,宋幼棠去第一舞蹈学校面试的那天发了高烧,那是她理想的学校,她瞒着自己,躲去了另一个城市,执拗地从头再来一年。
以前她总说“明天见”,那时他们谁也不知道,从某一天开始,明日隔天涯。
“你当初为什么不声不响独自跑开了?”钟谬尽量让嗓音听上去平稳些,“宋幼棠,你还欠我一个解释。”
宋幼棠闻言苦涩一笑:“我怕,耽误你。”
接下来,宋幼棠将所有的心事全盘脱出。她因为年少时的自卑,犹豫着,退缩着,不敢无畏地走向他,她希望能够自己也能变得和他一样优秀,能和他并肩同行,而不是让钟谬一次又一次站在原地等她。
“你知不知道,这几年,我每一天都好想你。”
哪怕宋幼棠找借口再荒谬,钟谬还是假装相信了。他知道,她一定是躲在暗处偷偷努力着。若不是他一直在找她,若不是他恰好去邻市出差,若不是他走进了那家舞蹈工作室,看到贴了半面墙的关于自己的信息,从获得的奖项到新闻采访……若不是他找了个理由,让她重新回到这座城市,他们或许会一直错过。不过,好在命运眷顾。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见到话,你是不是打算一直躲着不见我?”钟谬顿了顿,加重了语气,“丢下我一个人偷偷跑开那么久,你想怎么负责?”
宋幼棠摇摇头,眼圈顿时泛酸。
钟谬失笑,替她揩去脸上泪水。他想起那个在院子里拣药的午后,院子里的海棠花被风吹落,簌簌地掉了满地,她怯怯地走到自己面前,垂着头不说话,好半天才敢悄悄掀起眼皮注视他。
从前只望了那么一眼,却好像认识了许多年,现在只望了这么一眼,却好像这些年从未过去。
海棠花依旧盛开,她仍是他清晨与傍晚的全部意义。
(编辑:八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