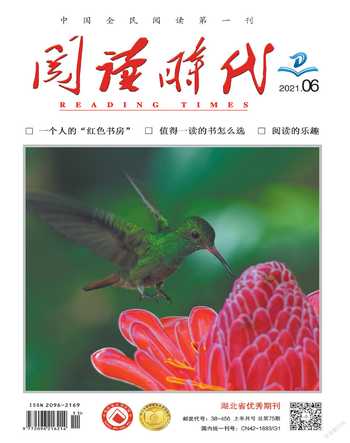我的阅读引路人之不忘初心
谢越清
1977年的一个秋日,得知“大笔杆子”要调到县里工作。我向生产队请了一天假,急匆匆地赶回家送他。他深感意外,“没想到你还专程从队里赶来送我。”他扔掉半截香烟,双手紧握着我,笑出了少见的灿烂。
他的热情唤醒了我的歉疚。插队务农一年多了,我很少离队,偶尔回家一次,也是蜻蜓点水,扑腾几下,旋即匆匆飞回乡下,没看见过他一次,也未曾想过主动去看看他。他依旧面色苍白,却精神了些,穿的还是那件中山装,插的还是两支钢笔。他用白色搪瓷缸给我倒了一大杯温热水,把我拉到家门口。见我回头瞅那天井,他笑了笑,说:“门口敞亮些。”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次我终身难忘的长谈!那年,我19岁。
我刚坐下,他就迫不及待地问我是否知道恢复高考的事。我告诉他,听广播了,想报考,但心里没把握,毕竟中学没学什么,基础太差。
他连连摆手,“你一定要报名!一定要报名!”接着站起来,以一种近乎家长的口吻说:“高考能改变你的命运,你不要错失良机!必须参加!要有信心!”
我使劲地点头说:“听您的,我一定报考!”
他咧开嘴笑了。我心里却涌起一股酸潮。生怕自己掉泪,我赶紧端起茶缸把半个脸罩住,咕噜咕噜地喝起来。
又听见他说话了,说的是几年前借书给我看的事。说那些长篇小说其实都是他自己的。我惊讶得直呛,怔怔地望着他。
他晃了晃夹烟的右手,“我出身不好,运动搞得人心惶惶,全家老少九口人要靠我养活,我不得不比其他人更加小心翼翼,所以才对你谎称那些书是找别人借的。”
他眼里泛出歉意,“越清,你能諒解我吧?”
听完最后一句,我放下茶缸,腾地站起来,转身望向天井,抓耳挠腮,不知所措。真没想到那些“大毒草”竟是他自己的收藏,更想不到他为所谓的“谎称”和“保证”歉疚了几年,还要我谅解他。我跟他非亲非故,他为何要冒险主动借书给我看?不就是因为喜欢我爱看书吗?我爱看书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回过身来,声音颤抖地对他说:“那些书,是不是您的不重要。您冒那么大的风险借给我看,把我引上了阅读,尤其是喜欢文学的路,让我不再空虚,从此充实起来。您是在帮我,我感激您还来不及,怎会怪罪您呢?”
他抬手要我坐下。我刚落座,他立即伸出双手,一把抓住我的右手。我顿时觉着手心手背夹在一股暖流中。他放开我后,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我连忙抓起火柴盒,划了两根火柴才给他点着。
与此同时,我的好奇心也被点燃。“红卫兵抄家那么厉害,您那些书是怎么藏下来的?”我忍不住地问。他淡淡地一笑,弹了下烟灰,说:“恍若隔世了。我们单位那时有造反派组织,他们每次和红卫兵搞行动,我都会提前知道。一回到家就赶紧藏书,水缸底下压个十几本,晚上再到屋后面的林子里埋几捆。每本书都裹了好几层牛皮纸,以防它们受潮腐烂。等抄家狂飙过后,取回来就是了。”
“您就不怕他们发现吗?”“当然怕。不过,最初没想那么多,可能是读书人的本能驱使吧,一心想的是,想方设法把书藏起来。你知道读书人最舍不得的是什么吗?是书。书要是被销毁了,不让看了,人生就觉得无意义了。埋书的时候,我胆战心惊得不行,怕受处分,怕丢工作,更怕坐牢,还怕连累家人……万幸的是,他们每次抄家都没有想到水缸和小树林,总盯着柜子、箱子、抽屉、床板和床底下。呵,也许是我运气好,也可能是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力在护卫这些书吧。”
那天,他还说书籍载的是人类对自然探索的认知,是对自身活动、情感、心理和思想的记述、探究与评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文明的载体和进步的阶梯。
又说古代最早的书刻在龟甲上,称之为甲骨文;而后写在木简、竹简和丝帛上,所谓尺牍、简册和尺素的说法就是这样来的;再后来就是唐朝发明了雕版印刷、北宋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才有了纸质印刷书。最后他还说了书在历史上的一些不平的遭遇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我听得津津有味,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我还在回味着,见他长吁了一口气,一大串烟雾从他鼻孔里冒出,袅袅升腾。他的眼睛跟着烟雾移动,烟雾散化后,他仍望着上空,嘴唇喃喃地翕动着,“‘四人帮’倒台后,让人们看的书好像慢慢多了些,可以自由读书的日子应该为时不远了吧!”他凝视着我,满脸殷切期盼的表情,家长似的叮嘱我说:“越清,不管今后怎么样,你都要坚持多读书,好好读经典。只有读书,才有前途。你有了前途,你父母就不会再苦了。他们太忠厚老实了!”紧接着他又郑重其事地补了一句,“还有。除了读中外文学名著,你以后一定要读历史和哲学,要炼成一个心明眼亮的人。”
我频频点头,眼里泛潮。
“对了,你打算以后做什么工作?”他忽然话锋一转,问我。
“如果考得上大学,想读中文,像您一样,也从事写作。”其实还有一句话我没说出来,就是希望他给我传授写作技巧。我插队后尝试写过几篇东西,但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没一篇让自己满意的。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写作没什么诀窍,用真诚的心写真实的事和真情实感,就行。但写材料除外!”
次年初冬时节,一纸大学新闻专业录取通知书,把我的写作愿望变成了现实。写作理想如愿实现的惊喜,有望做新闻记者的虚荣,顷刻间使我膨胀得近乎癫狂,那阵子,俨然自己扶摇直上九万里了。曾有过向他报喜的冲动,但不知为什么,那冲动转瞬即如露珠般地蒸发掉了。待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时,我已在新闻行当摸爬了近30年,霜发覆顶,满脸沧桑。
我的写作愿望确实是实现了。可在“主流媒体”忙乎了10来个春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为之痴醉的所谓写作也就那么回事,我还是回到了他当年为我预设的站点——一生阅读,述而不作,思而不写。与书相伴,不争不鸣,自得其乐。
我对他的感恩和敬意,自此与日俱增。“一定要去拜望他!”我反复地跟自己说。三年前的一个三九天,我回乡专程上县城看望他。他对我的再一次“从天而降”,欣喜得双眼眯成了一条缝。我坐在他的身边,二人华发相映。他握着我的双手,久久不松,反复地说,我一直惦着你,一直惦着你……我给他敬了支南国的“好日子”香烟,起身为他点着,然后自己也抽起一支坐下。两串烟雾交会在一起,升腾,消散。我跟他说了自己这些年的“新闻写作”之旅和心路历程,他听了直点头,说这番记者经历好,坚持阅读好,就这样蛮好……他脸色仍旧苍白,一身藏青色棉衣,干净整齐。聊毕,我才环视客厅。客厅的灯很亮,是我喜欢的暖光。没有吊顶,没见到电视机。三面墙壁立着无门的夹板书橱,每个书橱都是满满的书,其中一个里面码着几套线装书,毛玻璃茶几上搁着《庄子》《道德经》和钱穆的《国史大纲》,书里都夹有竹质的书签。另一面淡黄色的墙上,挂着一幅梵高的“星空”复制画,我家也有一幅。
我起身走过去,伫立在画前。那棵黑暗的大树,赫然兀立于画前,占据着画面的三分之一空间。它状如火焰,意欲吞噬星空;又似魔爪,幻想操控星空。星空未予理睬,星月悠然闪烁,流云兀自旋转,低矮的房屋簇拥着高耸的教堂在寂夜里沉睡……我轻抚着画框,朝他说这是一幅非常奇幻的作品。他立刻接过我的话头,但说的不是“星空”,而是我:记得你上初中时很喜欢绘画,高中时还在画,对不?不等我回答,他又把话题转到了梵高身上,说梵高是位奇才,他苦在生不逢时,也幸在生不逢时;苦在生计艰难,也幸在生计艰难;苦在不为世人理解,也成在不为世人理解……他对梵高的解析让我惊叹,都82岁了,思维还如此清晰深邃!
“越清,不要看了,快过来坐。”他拍了拍布艺沙发,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回到他身边刚坐下,他妻子就过来给我添茶。她一直默默地坐在他右边的单人沙发上,我与他交谈时,她一会看看他,一会望望我。他们的5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这间80平米房子里,只有她伴着他。
给我添完茶,她回身去给他添,忽地對我说:“越清,你不知道,他昨天听说你要来,高兴的不得了,都晚睡了一个多小时。我看你们俩真是有缘分,像前世的兄弟,两个白发,两个烟鬼,两个书生。”
听罢,他和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我告辞时,他站起来,身子颤巍巍的,要我等等。我欲上前扶一把,他晃了晃手,缓缓走到书橱边,抽出一本书,递给我,说送你作个纪念。
难道他出书了?不是说只读不写吗?
我接过来一看,是叶芝诗选。惊疑遂消。我随手翻到一个折页,一首划了红道道的诗跃入眼帘:
随时间而来的真理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
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落我的枝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我抬头对他说:“我喜欢这首诗。”他笑了,笑得很灿烂。
去年的平安夜那日清晨,手机铃声惊醒了我,故乡的发小兄弟说,他昨夜驾鹤西去了,享年84岁。又说,他的孩子们都不要他的藏书,他妻子只好把那些书全烧给了他。我的心一阵阵地紧缩,两眼发潮。
当天夜深人静时,我在小区的一角寻了块干净的草地,燃了三炷香插上,点着一支“好日子”香烟供上,然后取出叶芝的《随时间而来的真理》复印页点燃,朝着1100公里远的西北方鞠了三次躬。看着那复印页火熄屑散,我想跟他说点什么,却一句也说不出,只在心里默念着他的名字,“务一先生,务一先生,心无挂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