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农村包围城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在艰辛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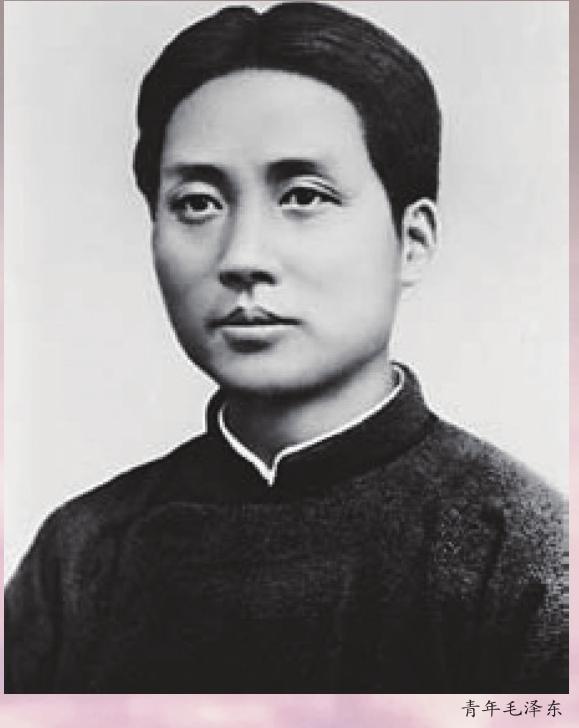
古田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收到了林彪写给他的一封新年贺信。在信中,林彪表示对现在红军的形势比较悲观,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对毛泽东“一年内争取江西”的计划表示怀疑,希望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区域游击,运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扩大红军的影响。他向毛泽东袒露了心中的疑问,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点。
林彪的信,反映出当时红军干部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想法。毛泽东打算在复信中,深入阐述古田会议没有涉及的一些问题:如何评估当时的革命形势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希望借此教育红四军干部认清形势和前途,统一思想。
在复信中,毛泽东写道:“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对林彪的这个观点,毛泽东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问题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因为井冈山生活困难,才有去湘南的“八月失败”。回来后依然经济上无出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被国民党军撵着跑将近两个月,在大余、圳下等几次战斗均告失利,直到大柏地战斗才缓过劲来。1929年2月,上海的中共中央来信又提出分散红军,隐匿大的目标,朱德、毛泽东离队的问题,使不少中层干部产生了分散游击的想法。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信中用很多篇幅,再次回顾了湘南“八月失败”时的军事冒险错误和“二月来信”中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要红军解散的论点,说明这两件事情前一个“左”,后一个“右”,都没有正确估计和把握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
毛泽东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的红军和革命,还是很小的“星星之火”,但是这个革命终究要发展,要掀起高潮的,那就是“星火燎原”: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毛泽东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但是革命高潮何时能到来,还有许多条件和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还要耐心等待,但是要坚信,革命高潮是迟早要来的。
对于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毛泽东浪漫地预言: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108页。)
毛泽东这封信写得热情洋溢,循循善诱,如同老师教诲学生。我们要问:古田会议时毛泽东和林彪住在一起,还写什么信呢?这实际上是他们两人在探讨有关中国革命的重点问题,然后借这个方式来教育干部,让大家更容易接受毛泽东的思想。所以,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信,已不是私人之间的来往。毛泽东让红四军政治部将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党支部,以便让更多的指战员了解他的思想。
对于林彪写信这件事,50余年后,黄克诚大将评论说:“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不是正确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这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当提倡这种精神,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该提倡这种作风。”(《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806页。)
1948年2月初,林彪致电中宣部,针对各解放区自行编辑出版毛泽东的选集,要求收录毛主席给他的信时,不要公布他的名字。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要求。后来,在此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将批评林彪的地方改掉了。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在这篇文章下做了一个题记: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
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明了什么?通过这封信,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领袖气质。
什么是领导人,什么是领袖?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当上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就是领导人,但未必是领袖。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完全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左”倾盲动的思想下领导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断送了许多共产党员的生命。这些领导人也像走马灯一样,被共产国际换来换去,他们没有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去考虑党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的特点在于:每当中国革命处在一个转折的初期,他都拿出了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是马后炮,而是当大家站在十字路口,对形势还没看清楚,不知道往哪里走的时候,他提出一套理论、方针和办法。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是正确的,他的办法是能打胜仗的。
在红军初创时期,土地革命战争的低潮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農村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武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在1938年的全面抗战初期,当日军正在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在节节败退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指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方向和策略。
1949年国共双方战略决战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描绘了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
事实证明,这些理论都是在一个时代转折的初期提出来的,对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成为指引方向的人,这就是领袖的历史作用。
古田会议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描绘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前景,但它依然是个火种。毛泽东的思想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同,留苏的博古轻蔑地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1932年中共中央在江西宁都,给毛泽东扣上“逃跑主义”的帽子,再次把他赶下台。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结果,是丢了中央苏区,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走到遵义,红军干部战士都认识到博古、李德的指挥不行,这才开始确立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曲折和失败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1959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书记的时候说:“1927年是个大胜,也是个大败。蒋介石争得了政权,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党内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革命高潮变成了革命低潮,共产党由合法变成了非法,大批党员被杀戮。那时我们党缺少经验,只懂得同资产阶级合作,不懂得斗争。敌人教会了我们两个方法:第一是做秘密工作,他不杀人我们学不会的。第二学会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几十年。我们创立了十几块根据地,有三十万军队(包括游击队),有三十万党员。这个时候我们又犯了错误,‘左的错误。以为这个时候我们也了不起了,轻视敌人。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时犯‘左的错误。一犯错误就很大,三十万军队就剩两万军队,垮下来,中间经过一个长征。秘密工作因为‘左的错误,也破坏的差不多了。这是一个失败,很大的失败。但是失败教会了我们,大概这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失败教不会党员。”(《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时代在发展前进,大浪淘沙。中国人求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是一个层层积累的过程。没有前人的探索和牺牲,就没有后人的胜利和成功。那些为此奋斗过的先驱,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和敬仰。尽管有些人中途转变了、堕落了、背叛了,走向历史的反面,但是我们依然应该肯定他们曾经作出的贡献,因为这都是历史大道上一粒不能缺少的石子。
(本文选自图书《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有删节。)
图书简介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一书溯源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迄20世纪初,下及1929年古田会议,通过剖析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众多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的党派中脱颖而出,找到适合中国生存、发展的道路,呈现了终成燎原之势的“火种”的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初心力量。该书入选2020年度“中国好书”。
作者简介
刘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党史、军史专家,著有《战上海》《决战:东北解放战争1945—1948》《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