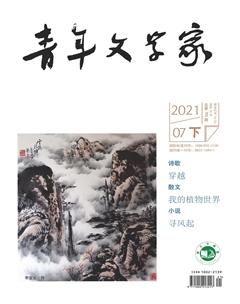“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张艳
穆旦,原名查良铮,借用杜运燮的话来说,穆旦“是第一流的诗才,也是第一流的诗人”。穆旦虽然只给我们留下了约154首诗歌,但有趣而令人惊叹的是,他有“双重”的诗歌创作,那就是诗人“穆旦”创作的诗和诗译家“查良铮”翻译的外国诗歌。本文想要重点探讨的是诗人穆旦晚年即1975—1976年创作的诸如《智慧之歌》《冥想》和《冬》等诗篇,并试图以挖掘穆旦诗歌中的死亡意识的方式来观照其晚年的内心境遇。
1976年1月19日,穆旦骑车摔伤了腿,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地震等原因而没有及时接受治疗,并在1977年2月26日突发心脏病逝世。腿伤是穆旦晚年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性事件,似乎也成了他写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触因。从穆旦现存诗歌末尾所标明的时间来看,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存诗不少于27首,是其年度诗歌写作之冠。也就是在这一年的3月,他写下了一首一直被视为其晚年诗歌开端之作的《智慧之歌》,在这里他揭示了内心的秘密,诗歌开篇即写道: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
看到“幻想”,不禁让人联想到他在1942年写下的“从幻想底航线卸下的乘客,永远走上了错误的一站”(《幻想底乘客》)。如今,“欢喜”已“枯黄”,年轻时的激愤情绪消退,“我已走到了幻想底盡头”。“我”回顾令“我”欢喜的“青春的爱情”“喧腾的友谊”和“迷人的理想”,发现爱情与友谊,或是已“永远消逝”,或是早已扭曲变形。“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这真是对穆旦人生的最大讽刺。他在青年时期就心系祖国,壮年时期又满怀期待、排除万难回到祖国,他的一生都在为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而努力践行着。但如此豪情壮志终究还是成了“笑谈”。
正如段从学先生在《跋涉在荒野中的灵魂—穆旦与鲁迅之比较兼及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穆旦诗歌中的现代性冲突体现为“物质现实对个人的无情挤压,个人时间的有限性与社会历史时间的无限性之间的冲突,其基本形态是个人与外在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坚实的冲撞,穆旦因之而突入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对于这一冲突,我们从他早期的《赞美》等诗篇中就可以看到。在这些诗歌中,他向我们揭示人生的隐秘,人生至多不过百年,我们都被社会历史进程所挟持而导致个体被无声淹没,“多少人的痛苦都随身而没,从未开花、结实、变为诗歌”(《诗》,1976)。痛苦是生活的常态,我们“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在这“幻想底尽头”,我体会到了他人生的全部酸楚,一种人生沧桑静穆之感浮现。
不仅是《智慧之歌》,作于这一年5月的《冥想》,也写下了“突然面对着坟墓”的窘迫: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在这里,诗人用一种完成时态来表明他对自我人生角色的最终体认—“普通”。但如若我们对穆旦的生平稍微有点了解就知道,即使在那个名家辈出的时代,穆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无法被取代的。而且,他还绝不仅是一位战乱中的“文弱书生”,他曾远赴缅甸战场有过惨绝的“野人山经历”。但穆旦还是将这一切归结为“普通”。诗人在诗中前面章节说,“我”在“生命的突泉”里“注入我的奔波、劳作、冒险”,“仿佛前人从未经临的园地就要展现在我的眼前”。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在“仿佛”这一虚拟语气中蕴含的失落与痛苦。当然,这短短几句诗中蕴含的情绪也是复杂的,从“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个体时间的有限性和社会历史时间的无限性之间的冲突。
而“坟墓”,是死亡的住所,诗人怀着一种对生命行将消亡的强烈预感,再也抑制不住检视生平需求,并将之诉于笔端。于是有了他在这一年的诗中对友谊、离别、爱情、人生、理想、爱好、艺术、“冥想”“梦呓”、时间(季节)感等多方面的叙述。例如:
呵,永远关闭了,叹息也不能打开它,
我的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
留下贫穷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
独自回顾那已丧失的财富和自己。
—《友谊》(1976/6)
爱憎、情谊、蛛网的劳作,
都曾使我坚强地生活于其中,
而这一切只搭造了死亡之宫;
—《沉没》(1976)
我细看它,不但耗尽了油,
而且残留的泪挂在两旁:
那是一滴又一滴的晶体,
重重叠叠,好似花簇一样。
这时我才想起,原来一夜间
有许多阵风都要它抵挡。
于是我感激地把它拿开,
默念这可敬的小小坟场。
—《停电之后》(1976/10)
这些充满对死亡感知的诗句,让我们感觉到其风格明显异于诗人前期的“外冷内热”,而是异常冰冷。“我的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回顾的都是“已丧失”的。不论“爱憎、情谊”还是创作都是为“我”搭建“死亡之宫”。这些诗句弥漫着冷彻的寒意,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而《停电之后》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的《秋夜》,相比较而言,我们会发现鲁迅笔下的“秋夜”是躁动的,而穆旦的这首诗却安静得仿佛世界不复存在,生命体征几近于无。再加上“坟”这个富有精神内涵的“心象”,还有“花簇”点缀着,这也许就是诗人对死亡的想象吧!
穆旦晚年的一首首诗歌,都是哀伤而凄厉的生命挽歌,而将这挽歌奏向高潮的是那首被称认为是穆旦的绝笔之作,作于1976年12月的《冬》。如下是主诗第一章: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