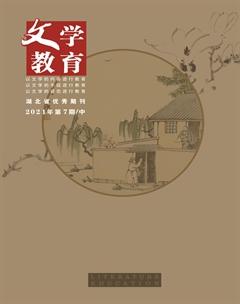仰望俗世之光
子青
我准备研读蓝风新出的诗集《俗世的光芒》,岸雪提示我,说他是口语诗。我不知诗是什么,网上的注解很多,无非是说诗是抒情言志的,在文体上,诗有形象、有节奏、有韵律,是分行的。最给力的是:只有一种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就是诗歌。
女儿也写诗,我曾买了《海子诗全集》,想得暇读读,以期能理解女儿。可女儿说,海子已过时了。那是12年前的旧事。记得有一次,我把女儿写的诗歌,分享给一个早年也写过诗的朋友,他严肃地批评我女儿应该继承传统,我们还有了何为“继承传统”之争。因为朋友看不懂我女儿的“新诗”,直到他在一个学问深厚的诗歌群里试着晒出了我女儿的一组诗,有人指出那是由“时间逻辑”转换成了“空间逻辑”,朋友似乎才找到读解我女儿诗的密码。
对诗,我的确是门外汉。“口语诗”一说,我之前闻所未闻。我借助网络,才知道它已是诗的潮流,口语入诗,似乎有“颠覆”之意。稍微有点“史”的概念便知,这“颠覆”便是“创新”,是值得颂扬点赞的。
我赶紧补课,郁葱的一段话让我对“口语诗”这不新的新事物有了定盘星:真正好的口语诗,不需要那么多的诠释,它可感受,可触摸,但关键是,它是“诗”而不是“话”,它有审美价值和意义。
我依稀记得,学生时代读书,老师讲过:“诗言志”“愤怒出诗人”之类的话。我依葫芦画瓢,来读蓝风的诗集,便有一个有底气的标准:只要分行在言说。其实,是不是传统意义或更新意义上的诗不重要,重要的是:蓝风在写什么、说什么?他是否言志、有无真情的流露?特别是是否表现出了诗歌应有的批判性思考?
善解人意的蓝风在把《俗世的光芒》文档发给我时,又分享了一个名家刘一君为其诗集作的序言:读《俗世的光芒》。蓝风非常谦逊地说,仅供参考,称其“蓝风”就行。我用心打印出这筹划中的新诗集,以便真正用心学习琢磨。
蓝风是真诚的,他一再说,能不能找到感觉写点啥并不重要,写不写,兄弟感情还在。我接收到《俗世的光芒》书稿电子文稿的那晚,我正在外与几个文友喝酒聊天。待小酌微醺回到家时,我计划好的是次日打印了再认真地拜读。我跟蓝风说,我一定会仔细研学,无论如何也要写出一篇真切的读后感来。
那晚,我躺卧在床,久久无法入眠。蓝风即将出版的诗集,拟用《俗世的光芒》为名,两个关键词:俗世和光芒,应该是整个诗集的视野和亮点所在。我在想,蓝风为什么要强调“俗世”,俗世与他的诗歌有何割舍不了的联系?他已置身仕林,在一个县城,已然高高在上,他关注“俗世”,又获取了什么样的光芒?我隐约有一种直觉,在蓝风留恋的“俗世”,一定有某种他内心珍视向往的东西。我想到一个计划中的诗歌评论题目:《仰望俗世:一种置身仕林的疏离感》,或是《回不去的俗世:一种置身仕林的疏离感》。
我在手机备忘录里记录了我灵感的闪现:光芒照射是有距离的,诗人与俗世有间离,又渴望俗世之美。他想回到那俗世,不管是天上的俗世,还是地上的俗世,因身份使然,他似乎只能仰望或遥望,一种身不由己的疏离感搁置在心,他一直在表达一种失去的向往。用这个视角来审视他的诗歌。他有意无意已经把这种身份感浸入诗歌,他不是记录俗世的日常,而是写偶尔进入俗世的瞬间感受。他一直努力在用俗世的光芒照亮他那方寸间阴郁着的心。
我们随着诗人的心走,慢慢会发现,我们只是在俗世外看一出俗世的生活剧,尽管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但那只是我们企图能回去的俗世,无奈遗憾的是再也回不到那个原乡。或许他在仕林找不到应有的认同感,只有在俗世他才能找到情感的皈依。他对社会的无奈,他作为社会人那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疏离感,时时处处都在困扰折磨他。也许,只有诗歌才是他“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的自我宣泄。他一直在俗世和仕林间摇摆,有一种“人在曹营心在汉”的离心力在牵引着他,他记录了这种心迹。俗世的光芒,应该是最原始的蛮荒之地所发出来的光,是“人之初、性本善”发出来的光,当俗人也被酱缸浸染以后,还有光吗?当俗世已是市井,而且乡村的天、地、水,也被污染后,环保成了抹不去的梦魇。
也许我具有某种天分,我仅从尚未付梓的诗集的书名便可预知蓝风的心语。待我真正一页页一首首仔细研读蓝风编入《俗世的光芒》诗集中的所有诗篇时,跟我两年前展读他第一本诗集《彼岸》的感受完全不同。那是蓝风心灵的歌声,是他站在苍茫的雪域高原,敏感而多思、脆弱而刚强地感受着与时俱进的生活潮流,那是蓝风的另一种性情映照,也是他守正笃实、持之以恒的价值影像。他以一种家国情怀,把读者带入一种西藏生活的美好愿景中。自然,这种主旋律的颂歌为他赢得了喝彩。而今,蓝风呈现给我的新诗集《俗世的光芒》,在创作年份上与《彼岸》有太多的交织,可我感知到的却是另一个蓝风,或许像他拥有几个笔名“高辛、蓝风、山之南”一样,他在需要的时候会自动变换。
正如诗人刘一君所说,蓝风这本新的诗集,是以其俗世的人生为根基的,而且这个俗世的人生装有他全部的生命。不管是感悟日常生活,还是从常见的物相中引发出哲思,蓝风都试图采集一点点光,先照亮自己,再照亮他人。的确,外在与内心,官话与诗语,会让他有一种疏离感。但是,蓝风通过诗歌,还原了他自己,又超越了他自己。蓝风以一种平实、直白、削减的崭新特色,在学院气息浓厚的意象、象征、隐喻的泛滥中,彰显了一股悦目赏心的清流,坚定了我的粗浅认知:口语诗当是一种心语的自然流淌。诚如刘君所言:跟随蓝風的视野,无处不是诗,无处不能诗。他在这本新诗集里,天然去雕饰地成就了一个大写家的风范。
我与蓝风虽相熟经年,但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尘世,我们未曾有过灵魂层面的深交,熟而不识。及至这本《俗世的光芒》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爱不释手地读下去,仿佛才认识一个本真的他,一个真正称得上“蓝风”的诗人。
开篇第一首《面馆》,蓝风即为我们带来了浓厚的烟火气,在此,我们也找到了他个性化独特的视角,开始随他,丢掉身份感,回到了俗世。紧接着,我们在他的《读史》里,明白了他的信念:德为王。他没有像吴思那样,从历史里读出《血酬定律》和《潜规则》。也无意为我们展露出令人恐惧的管仲陷阱。他不想跟我们打《哑谜》,尽管他也有警觉,他还是不忘初心,会从《纪念日》获取力量之源。
我后来问过蓝风的简历,知道了他于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于湖北襄阳,先后做过建筑工人、工程师、乡镇公务员、机关文秘、援藏干部。他闲暇时以诗怡性,诗作散见于《诗刊》《诗歌月刊》《天津文学》《白诗歌》《九月诗刊》《中国当代诗库》《汉水》等。难得的是,等他位居小县城的庙堂,仍能孜孜不倦地笔耕不辍,当然,除了情怀,更多的是在借诗歌释怀。
一个人的感情基点,应该还是原生家庭和早年的经历在心里留下的烙印。从《顾客》里,我们感受到蓝风对底层劳动者的那种怜悯之心,而这一点,多少也会影响他后来的为人处世之道。置身仕林,闯荡宦海,他耳闻目染的一切和奋力的拼搏,自然会使他身疲心累。“我两手空空/却置身其中/不能向东,亦不能向西/不能言白,亦不能言黑”(《梦》)。他内心是有一个自己的,但被“奔腾着的千军万马”裹挟着,他无法动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在《愚人节》里感叹,那无尽的靡靡之音,他又能奈何呢?也许读读《时代三部曲》,在王二式的快乐和自我排解中,他能暂时地纾解自己紧张的神经。
好在有个家,那是他短暂歇息的港湾。“我的对或错/都可能惹你生气/只是你不知道/我在你熟睡后/抚摸你的头/一回/二回”(《给儿子》)。他的努力,他的艰辛,除了自己的梦,不就是为了这个他深深眷念着的家吗?
但他的乌托邦有时也会被人鄙视,尽管这是支撑他努力的坚定信仰。《乌托邦的愤怒》只能深藏于心,他还得笑呵呵地回答,假称自己也是“喝喝小酒/打打麻将/再到洗浴中心/放松放松”。一个社会必须有信仰,他坚信这一点。“有人说他瘦/有人说他老/有人说他苦/有人说他穷/但没人会认为/自己比他强大/比他富有”(《在杜甫铜像前》)
理想主义者常常是落寞的。在《夜色》里,我们能感受到蓝风内心那种深深的落寞。“晚风是凉凉的/江水是凉凉的/城市如一个/巨大的容器/填满夜的泡沫/车辆来来往往/仿佛没有终点”“月光落在沙滩上/落在草地上/她的脸颊是凉凉的/鼻尖是凉凉的”。
蓝风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在《葡萄》里,同样“又大又圆/又紫又亮”的成熟葡萄,命运是不同的,尽管都“急切地等待/看中它们的路人/把他们挑选,购买”但是最终,总有“没卖完的葡萄”被扔进巷子里的垃圾房。有一句励志的话:是金子总会发光。但你是葡萄呀,你有保鲜期,你的寿命就那么长。
这种焦虑感,已然嵌入蓝风36岁的那颗年轻的心,他有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尽管他也知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香蕉、桔子、苹果和核桃的机会或命运是不一样的,你无法乔装,你甚至可以安慰自己说,核桃最终总要被打开,它内部的干瘪和霉烂,并不能最终改变结局(《核桃坏了》)。即或有一天你成了《天花板》,“它高高在上/目空一切/而楼上的人/总是把它踩在脚下”这天花板犹如过去的弄臣,虽处万人之上,终究还是在一人之下。货以帝王者,谁能逃脱这样的命运呢?
蓝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目标,虽然当时他还没到不惑之年,他已经是青年老成了。在《主角》中,他成了一个世事洞明道行很深的人,“斟满酒/除了他之外/每个人都在/寻找空隙/一有空隙/就使劲儿/往里钻/钻进去的/带着表演者的笑容/没钻进去的/带着旁观者的笑容”。其实,就是侥幸成了“角儿”,不过也是各领风骚两三年,都有过气时。
蓝风在《大雾》里袒露了他的心迹:“大雾笼罩了/一座座城市/一条条街道/人们只有/在大雾中/才能感觉到/大雾的存在”这犹如当年伦敦的大雾,窒息了数千人,一夜之间使一个城市停摆,人们才醒悟过来。这个世界没人愿意做先知,所有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知为何而生,也不知生而为何。蓝风能在众人皆醉时独醒,也是慧根使然。
一种虚无主义的情绪开始笼罩了他,一个在宦海漂泊沉浮的诗人,开始反省是否应该回到原点。他用九节记录了《陪母亲看海》,他是带着歉意,以一种补偿之心,陪母亲看海。从走到人生边上的母亲身上,他懂了何谓“人生苦短”;而在纷杂的现实中,失忆的母亲仍在本能地呵护着他。“天凉了/回家”,这岂只是嘱托,这是警世恒言,更是神谕。在这首诗里,蓝风似乎找到了人生的新坐标,他从一种无意义的打拼中回到了真正的现实,回到了亲情的温馨里,至少心理上他已经完成了回归。
从新的视角看,很多过去被他珍视或认可的东西,他开始质疑。在《脏东西》里他清醒地认识了何谓“脏东西”,那些丛林法则,那些进化论的论调,他开始厌恶,但又无奈。因为“离开那些脏东西/我们四处碰壁寸步难行/迷恋那些脏东西/我们难以启齿却侃侃而谈/拥有那些脏东西/我们羞于见人却踌躇满志”。一种人格分裂症的病魔似乎缠上了蓝风。
在《谎话》里,他坦陈了自己的病症。他也在《无题》里分析了自己以及罹患同样疾病者的病因:“其实都不信/但他们说/信//其实都信/但他们说/不信”。寥寥数语,振聋发聩。
在人生的三岔路口,未来的路该咋走?蓝风在《黎明》里有所思,也有所惑。“黑暗里/我想了一些事/想了一些人/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天亮了/我想的那些事/想的那些人/突然觉得/不再那么重要”。正如我多年前写下的一段话:得意之时崇尚法家,失意之时崇尚道家,平和之时崇尚儒家。我常常自问,我能活得洒脱一点吗?人都是心随境移矛盾的,蓝风也无法摆脱现实的困扰。
蓝风是一个矛盾体,他的诗如其人生,逐步由看破,到看透,只是还差那么一点点,他一直无法真正地放下,他羞于从宗教里寻找一条解脱之路,始终陷于俗世的泥沼之中。正如《老婆》和《甲虫》,他没有勇气抛弃喧闹的俗世,也走不进《素描》里那些男男女女平凡简单的幸福感之中,他只能不断地发出《天问》,却连一只《甲虫》和《蚊子》也不敢杀。我冒昧地推测,若有一片树叶飘落在他的额头,也足于砸破他的头。
我是一口气整整用了三天读完蓝风的新诗集,欲罢不能,心潮激荡。这里我只是粗略地罗列我对他一些诗歌的表意粗浅感受,也试图用简单的读解梳理一下他的人生感受。蓝风充满哲思的诗篇,印证了那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它也告诉我们,蓝风在岁月的碾压中是逐步在臻于成熟,激情让位于拷问,尽管他台上会有另一套话语,但在口语诗里,他还是想吐露真情。只是,他在灵魂的拷问中成了一个矛盾体。正如他忌讳宗教话题,而内心又缠绕着它,他在《反思录》中写到“我害怕原罪和轮回/造孽和报应”;他恐惧孤独,但又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知音,那首不知能跟谁聊的诗《催眠术》道出了他深深的孤独,他只能假以写诗,在诗歌的王国里化作彩蝶;他想退出江湖,又心有不甘,想再试试做一块巨石,期待一个美好的结局(《水落石出》)。
其实,蓝风心里不时也会跟明镜似的,他已经意识到他所有的努力最终都会《打水漂》,“石子从水面掠过/激起一串水花”“收集它们/耗尽了他半生的時光”但是,“水花溅起/又瞬间消失”“那些扔出去的石子/沉入水底后/就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的确,他再用心,那世俗的名利,终究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都是过眼烟云,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如果把蓝风的前后两本诗集《彼岸》和《俗世的光芒》对比并置着看,一阳一阴,一正一邪,一高一低,这两面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一面示于人,一面藏于心。他一时清醒,又一时迷茫。他之前那种以《彼岸》为象征的高调的亮相,在《俗世的光芒》里无疑暗淡了下来。不过,我更乐意看见蓝风的这种毫无粉饰的本真状态。
感谢岁月的磨砺,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生活也能教会我们如何去完成人生之旅。我们只需不抗拒天上那个“俗世的光芒”照耀,哪怕需要假以时日,慢慢融入诗意的俗世,我们也可跟随蓝风在俗世光芒的沐浴中成长。正如《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城市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