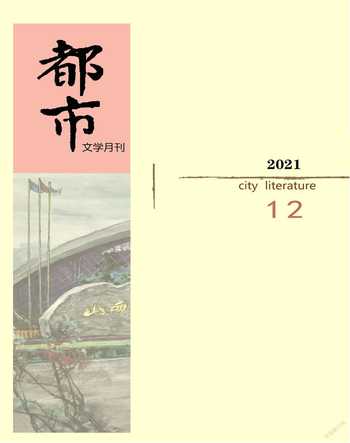山言林语
刘云霞
星空
太阳啊呀一声落下去,似乎又被崖边物挂了个暂停;余晖掠过蔼蔼丛林抛出去,对过山顶立即披了一条梦幻般的黄披风。一朵两朵的云在山头探头探脑,或雪娃娃般坐在那里摆姿势做造型。一切都是恬静淡然的样子。
当夕阳在对面山顶放幻灯片时,林间万物已渐渐沉在水样的暮色中了。月亮不知何时从西天嘟噜一声浮上了树梢。初出的月牙如拔得精细的女人眉,一副寡白无色貌;渐渐地,银月越来越浓地泛出了金光,身姿也丰腴起来。那先银后金由淡而亮的月貌变化上走着夜的脚步,天幕随之越来越深了起来。但这月只是个报幕员,轻轻一晃便没了踪影;大片紫云从树梢山顶飘溢出来,像日月合体的精血。
昼沉夜浮,星斗满天。
当浩瀚星空一览无余于视野时,我终于感到独我的存在了。渺小而真实的存在感,是只有在这纯净的静夜里才会有的。尽管同时袭来的,还有被无边夜海吞噬的一丝恐惧。
平日里,被车流人流机器流搅拌着,人几乎成了钢筋水泥的混合体,进进出出间难有片刻自如和放松。虫声鸟鸣是难听到的,广场公园路边草木丛,随便一个旮旯都有人扯着化学味十足的嗓子证明自己的存在;塔吊像游走的机器人队伍,一步步碾过树木庄稼从城市向乡村迈进——夜的静与黑连乡村田野都难觅全貌了。
但是此时,独步于霍山谷地洪洞东北隅一个叫后柳沟的地方,天与地都以婴孩般的澄澈淳朴围过来,让人应接不暇间有些受宠若惊。
后柳沟周边还有前柳沟、十八盘、疙洞峪、平疙台等,这些沟盘峪台左旋右绕上颠下簸把闹市远甩于外,手机这个人体赘生物终于也没了功能。与大自然会晤,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进山途中曾见“水曲柳的拯救与保育”字样。这个要保护的作物之柳与前柳后柳的地名是否关联不得而知,但这些珍稀动植物只在荒无人烟处才会有确是毋庸置疑的。如此看来,人之于山林终归是不速之客,我不由得放轻了脚步。
在纯粹的夜幕下,星星们或群或独或繁或疏都自如地在自己的位置闪烁。想一想,上一次与星空对话似乎还是在母亲蒲扇下的故乡小院;此后经年,匆匆忙忙爬坡赶路,竟好像再无看见头顶的星空,不知是少了星空还是缺了一双仰望星空的眼。
我们的孩子更是与星空无缘。无夜时代,他们一面世就迷乱于电光霓虹里。虚幻的梦想裹着稚嫩的双腿,从这个班到那个班,从书本到书本,从一条胡同到另一条胡同,泥土里灵动五彩的质感,星空中浩渺无垠的辽阔与他们始终隔着一个屏。视域限制着想象和放飞的动能,精神世界总难免有一片荒漠。一如与星空断片多年且终日被忙碌包裹的我们。
而现在,那个曾经看星识字的“厂”字,母亲说古里相隔于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等,都依然亮在那里。这昔日场景的再现,像咔嚓一声的时空倒片,不由人生出天悠岁短的唏嘘。
飞机在云层内嗡嗡,偶尔钻出来星星般闪烁一下,证明人在浩瀚宇宙中的存在。有流星划过,按照天人感应之说,天上一星地上一人,这是有生命的陨落。人将自己渺小而短暂的生命寄托于遥远的星星上,一颗迷茫无助的心常因星的恒久闪亮得到抚慰和照耀。地球给人一个驻足的支点去眺望浩渺的宇无垠的宙,视域是何等局促狭小;科技宗教神话因此都扑棱了翅膀,以有限对无涯努力地触摸和探索。空间站卫星飞船,真主基督佛祖天罡地煞,都在人仰望的视野里闪烁。
如今,原始仰望里曾为人类指点迷津的星,越来越多地走进人的生活或人类交互对语。
比如此刻,我正面北寻找天宇间一个北斗七星勺。人受这天启,放飞了无处不达、分毫不差的北斗导航;但对我来说,数十年人间岁月,天上北斗的神形只在耳边或神话里,目里却没个真切貌,不知这光阴如何虚度了去!
目光从天而地。万物没在夜色里。山如卧兽,树丛剪出神话中的影子幢幢。除非有一台热成像摄像机,否则你不会窥见森林居民们丝毫的夜生活,更无从知晓植物在黑夜里的丁点秘密。
夜的黑,催生了人类天上地下神间鬼界无所不至的想象力,以及由此而生的丰富多彩的精神滋养品。但是,这一切日下正在悄然退化。此时,我把自己浸在夜里,努力动员和唤醒已然麻木的感官,去感受黑夜的存在。呼应我的,除了萤火般飘忽的虫啾,只有风哗哗水潺潺。但这已足够了。终日被车喧、人喊、灯嘶、机鸣拥堵得几乎失聪的耳,被这风声水流涤得清亮;甚至能感到风生水起处草木的身姿和溪流石上的跃动,心也因之漾在一汪静里。难怪人们会把虫啾鸟鸣雨流溪潺的天籁之声放在枕边,失眠的孤岛上,婴儿般投身自然怀抱不啻最好的救赎。
三两头牛卧在夜深处专注反刍。星空之夜,原也是一个巨大的心灵澄净器呵!
日出
山顶如海岸。
风呼呼如纛舞旗摆。海中千岛明灭,万顷云雾翻波卷浪,气吞山河。山顶的夜辽阔而冰凉,画面却是蓝紫红橙热闹纷呈。这一望无际的辽阔中,正流变着别样的时空相对论:天空抖落亮闪闪的袈裟,又川剧变脸似的一重重由墨而淡;随后云霞出海曙,一抹橘红下,夜与昼悄然完成盛大交割。这一切,貌似时间在走,其实都是天在旋地在转,静谧中空间推动着时间。岸边翘首东方的人,崖壁随风摇曳的树,都在这无声的动里慢慢浮出梦一般的剪影。
有人工或天然垒叠的石垛将黑影剪落在橘色天幕上,像人类亘古不变望天的姿势。高台上有电视塔耸立,恰似千里海航的导航。
太阳如红豆蹦出来,天地万物立即浸在一片红光中。人仰视太阳,却少能看清其真容。但此时,在海拔2300多米的高山之巅,太阳以其千种娇媚万般温柔的真切注视着大地苍生,让人感到冉冉而起的希望和感动。
随后,这童话般美丽的太阳在其款款上升途中,又不断地易状变彩:一盏橘灯,一面铜镜,一缸金水,就这样朦朦胧胧闪闪烁烁泼泼洒洒于云海之间天地万物;沐在其中的也随之在光影里不断变换着自身的色彩。
“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这接天连地,大气磅礴之所在,让人顿悟,天地原为一气,山海本是同体的。海里隐着山,山里蕴着海,沧海桑田中,太阳推动着山与海的云雨和一泻万里的生命大河。这样看,山与海倒像是地球万物的父母或雌雄双体,而这里,太岳南端霍山最高峰老爷顶,正在演绎一场蔚为壮观的山海經!
突然想起《山海經》为何会单把山与海汇在一起。除了同是蕴涵博大,奥妙无穷外,是否因为二者相以沉浮转换中有着诸多相同基因呢?
而那穿林越壑上天人海无所不往,奇禽异兽千川万流无所不见的《山海经》,是否是冥冥中的上天旨意神人所为,为的是托体于地球的诸多迷途羔羊能按图索骥找到生存之道,或阿里巴巴开启智慧之门?《山海经》记霍山,“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养之可以已忧”。这种可以除忧去愁的尤物,此时,是否像常升常新的太阳一样,正隐在云雾深处某个角落以其脉脉温情,默默照耀着我们潮湿的心境?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当山阳一株株作物渐次被云霞染金阳光点亮时,山阴大片土地还在黑阴里睡着,远处却是彩云白雾夹杂着的一片迷蒙。隐约可见火柴盒似的楼群,烟卷似的烟囱,显现着人在浩瀚苍穹下草芥般的卑微存在。如果能有一管洞穿云雾的窥镜,当能发现,那里五色五味的市井烟火正在晨光下渐渐鼎沸。
云雾上下两相里看,恍若天上人间。
山林
没人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
一个褶皱四起沟坎遍布扭扭歪歪挂于山体的森林。一切都像天崩地裂后的仓皇散乱无序,一切又如天荒地老里的悠然率性随意;或许中间还有一场滔天洪水的冲刷,让草木万物挣扎抓持的瞬间凝成了一个定格。小溪或在乱石树木间跳上跃下,或在草丛落叶下轻泅漫衍,总之都是漫无目标地流动,也可视其为无道之道的“大道”哲学;奇形怪状的石块,小如鹅卵,大似小山,也都四散零乱地滚落着,那乱中透出的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又让这死寂之石有了几分生动和生机。
最奇是那些树木。直立的歪斜的横卧的,或单或丛,都是无规则状。那直立向天的,长着高着,不时还随风打个哈欠,这时,就有那弱不禁风的枝条折下来,发出轻叹般的咔吧声。也有那原已老朽的树,一个懒腰伸过度突断了身子,留下半截枯木在那里;说是死,那如青筋暴露的根之手仍四面紧抓着大地,支撑着其枯而不倒,并任鸟儿风儿一如既往地在肌体上摩挲亲热,像生命在超度。那歪斜或横卧的,歪着卧着就匍匐在地了,有的实体早已皈依大地,轻捻即碎的外形却长久留在地面,并慢慢托起一芽两株的新绿,开始新生命的轮回。
在承载万物的地面上,叶子果子枝子花朵,枯荣层叠的草,飞禽走兽的粪,风携来、鸟衔来的胞子、种子、花粉,不知已落下了多少重旧;曾经鲜艳芬芳抑或朴实无华的,曾经健硕刚硬抑或婀娜多姿的,都以回归的姿势混合进来,充实着大地母亲无穷的蕴涵和孕育力,这地上于是又长出了不知多少代的新。
山林如同人,诞生、发育、成长、死亡,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林中生命却在不断往复重生。那把顽石妆成卧豹的斑斑黑藻,时光绿雨下满目可见的轻苔,石罅树隙楚楚摇曳的菌菇们;还有相交互绕,经时间之力软与硬相握和解的石与树们……一切都在生生死死中见证着沉默的时光,一切又似自然怀抱中无生无死的涅槃。其中,蕴着一个深不可测的时光轴。万物在一个空间里,彼此间又有隔世隔代的鸿沟。山林为此无处不热闹,又每每很孤独;如同夜空里看似紧偎依实则隔天涯的星星们,又如同人生人世。
总之,在一个深山老林的清晨,当太阳的探照灯把七彩光投射进来,并哗啦啦把山林从树梢到地面斑斑驳驳撒满了金子时,林间万物都从不同时间岛屿上抬起头来,开始了新的出发。鸟们早早就开始载歌载舞,松鼠们松果般喊喊喳喳挤满了树,褐马鸡在山坡上悠然迈开了猫步,花儿们在不易察觉的角落顾盼生姿,蜂蝶蚊蝇们忙不迭地翩跹吟咏;当然还有花开花落声,果子呼呼落地声,树叶哗哗私语声,小溪淙淙欢歌声……
一头牛从山坡上穿林越石奔跑而下,边跑边悠长地峰叫;其状似在呼儿寻夫,又像在为新一天开幕。牛进入山林,并和林间绿坪相以衬托成景成画,颇有点牛郎进入织女领地仙凡相姻的感觉。牛在山林中奔跑的姿势很潇洒,但一把盐就能诱得它随时回归人类的缰绳和圈笼。这一点颇像此刻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渴望没入荒林山野做一回完全自然人,又不得不依着一个山庄栖身。那些特立独行的帐篷客,或山顶看星观日,或山谷听风弄溪,多半也是依着山庄人气驻扎的。避世而趋群,向山而行者,心里常有两股力量在拔河;那些惯于绿拥红簇或人熙物攘者,更是不屑于与这寂寂山林为伍的。说到底还是人不懂山林,更不懂那些和人一样也夫妻儿女知冷知热过着日子的森林居民们。人因而与山林,与那大道之源的自然终究隔膜着,而自然,也以其穿透亘古的幽幽之目,睥睨着螃蚁般的人间走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