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羊皮袄
秧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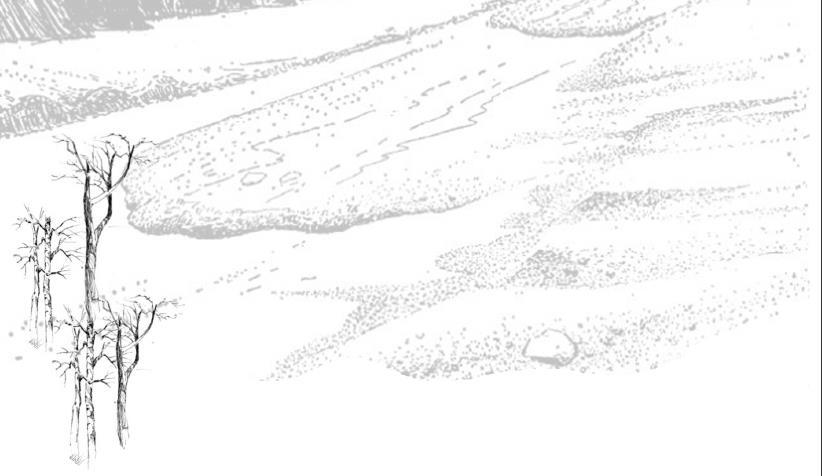
一
不是还有三公吗?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从大有的脑海里闪过。这闪电带来的不是疾风暴雨,是隐隐约约的希望,就一会儿,十几分钟的事,两千元就到手了,学娃的学费,还有油盐钱都解决了……
老婆香还在哭,哭得真惨,那眼泪,像开闸的洪水,从窄窄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不做丝毫的停顿,哭声像台风呼啸过屋顶,凄惶得很。大有一骨碌起来跑到她身边,压低嗓门吼道:“别哭了!现在你终于不用再伺候爷爷了!”香却哭得更凶了,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心,绝不是伪装出来的。大有望着窗外,不远处重重叠叠的青山,在薄薄的月色中,像一只只蹲着的巨兽,仿佛要把一切吞没掉。
山里人恨这山,就是这一座座像利剑一样插入云霄的山,让那些鲜鲜的枣、软糯的柿子、脆脆的苹果运不出去,烂在自家的籮筐里。它们刚收下来,大伙舍不得吃掉,指望果贩子过来,然后换成钱。那些远道而来的果贩子,是城里人的孙子,在这山沟沟里,却摇身变成了大爷,比大爷还拽味。他们开着一辆小型东风车,车斗不会很大,一次能收下的果子也就三四千斤。可这山里的土地种啥发啥,一颗苹果核,无意中丢弃在门前的土里,来年也会长出一棵小苗来,你还没来得及认清它的模样,它便不拿自己当外人了,才三几年工夫,在你门前挂果子,一结就是几百斤。山里人在惊喜的同时,也非常无奈,果子多意味着供过于求,最后只好贱卖。
有一年,大雪封山,一位身材矮小、长相猥琐的中年人,战战惊惊地开着东风车上山,一听到车声,全村人都争着抢着将箩筐往外挑,生怕迟到,人家就不要了。一个个在萧索的寒风中,拢着袖子,脸上堆砌起来的笑意,将脸都撑变形了。那果贩子从这头走到那头,仿佛面对的不是一只只果筐,而是列队欢迎他的士兵,那装模作样的姿态,也像一位凯旋的将军。邻居二嫚主动出击,一把拉住那果贩子,娇滴滴地说:“大哥,这天寒地冻的,先去俺家喝杯热酒暖暖身子!”二嫚虽不好看,但一娇一嗔的,颇有几分妩媚的样子,像《西游记》里想尽办法吃唐僧肉的女妖精,那果贩子可能从来没受过这等待遇,去二嫚家待了一夜,次日就收走了二嫚家所有的果子……
想到二嫚,大有激灵灵地打了个寒战,这女子势利眼嘴巴大见好就上有便宜就占,这事儿要是让她知道了,可不得走漏风声,还不知道她会整出啥幺蛾子。大有再次压低嗓门冲香吼道:“哭丧啊!”香一边哭一边还嘴道:“就是哭丧!我不哭,别人咋来随礼!爷爷你早不走晚不走,咋偏偏这时候走呀……”香愣是哭成了咏叹调,颇有一唱三叹的气势。大有实在忍不住了,一个箭步蹿到香的面前,伸出铁扇似的巴掌,用力甩在她的脸上,香被打得晕头转向,她以为大有嫌她没伺候好爷爷,又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拉开了扯着嗓子的架势,大有一把捂住她的嘴,在她耳边嘀咕了一阵……女人的眼神活泛起来,像一条上岸缺氧又被扔进水里的鱼。
硬板床上躺着大有的爷爷,爷爷这辈兄弟三人,都是长命的。爷爷今年一百零五岁,从他一百岁起,县上的干部就开始关注起这个老寿星,连续几年爷爷的生日,不是县长就是书记过来慰问,最起码也会来个秘书代劳,由镇长陪着,探望这位百岁老人。人老了果然是个宝,大有从来没想到,爷爷在有生之年,居然能为这个家做出这样巨大的贡献:一束鲜花,一个红包,一个几层的大蛋糕。那蛋糕比鸡蛋好吃多了,大有切开蛋糕,小心翼翼地切下一小块,给二嫚家的小子送去,这女子厉害着呢,来年卖山果,说不定因这蛋糕的情分,她会伸手帮衬一把。
九月初八老爷子的生日,二嫚记得比自个老娘的生日都清楚。进进出出中,二嫚问几次了:“今年那些领导还来吧?”大有带着几分矜持拿捏着含糊答道:“谁知道呢?人家领导忙,可不比咱们!”大有心里是有底的,去年明县长亲临,走之前握着大有的手使劲抖了几抖:“好好照顾老人家,这样的寿星全国也没几个。”隔了半个月,村长从镇上领悟精神回来,举着一张报纸,兴冲冲地找大有,说:“上报了,你家爷爷上报了!”报纸上刊登的是重阳节专版,一群大大小小的领导围着百岁的爷爷,众星拱月一般,这十里八乡,谁有这样的荣耀?最实在的,还是临走前那个厚实的红包,连村长都有几分眼红了。
大有摸进里间,昏暗的灯光下,爷爷像睡着了一样,爷爷是与老父亲相会去了。老父亲走了几十年,爷爷却硬生生将自己活成了一棵老古树,一百零五岁,离生日还有三天,这棵老树终于活得不耐烦了。“爷爷,你就不能再等三天呀?”大有摸着爷爷逐渐变凉的手,那手青筋虬起的模样,活像一段老树皮,他摸了摸爷爷凹陷的双颊,尽力合拢他微张着的嘴。香也窸窸窣窣地凑到面前,大有想着爷爷一个星期前起病,就因为受了寒,老人开始咳嗽,引发了身体的老伤。大有伸出脚来,狠狠地踹了一下香,他提醒过她给老人加条厚被子,她却忙着去采山药材,结果忘记了。大有看了看香憔悴的脸,叹了一口气。
大有两口子一直忙乎到半夜,他们先给爷爷梳洗,然后换上衣服,这些都是提前准备好了的。他们不敢放鞭炮,老人殁了,村里的风俗是要大哭,烧香烧纸放鞭的,好让老人走得稳,还要请族人帮忙抬上山……
大有在下定决心的那一刻,就不敢声张了。他和香抱着爷爷,挪进了后院的一间偏房,点了一盏豆亮的油灯,那灯将夫妻俩的影子倒照在墙上,让人感到说不出的诡异。“通知学娃吗?”香问了一声。学娃是大有和香的儿子,正在镇上读书呢。“三天后通知!”大有特别有主意。
天边几点星星蒙昧地眨着眼睛,大有和香一前一后向三公家走去,初秋的夜有几分凉,香不禁打了个寒战,但白天里还是有几分热的。她喃喃道:“会不会发臭呀?”大有回转身:“闭上你的臭嘴!”香不敢吭声了。
三公的屋与大有家隔着十来分钟的路程,清清冷冷的月色下,山的样子、树的样子倒映在月地上,像张牙舞爪的怪物。香紧跟着丈夫大有,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晚上,她老是觉得害怕和心慌,三公家的阿黄狂吠了起来,狗总是这样,喜欢虚张声势,以显示自己的尽职尽责。“瞎了你的狗眼!”大有恨恨地骂道。
屋内漆黑一团,九十多岁的三公早睡了,人老了,白天黑夜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没有界限,人老了,连模样都成了一个版本:枯树皮一样的脸,昏浊的眼,半闭半合着,脸颊削瘦得吓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仿佛永远在赶一段长长的山路。三公是爷爷的亲兄弟,还有二公,二公前两年走了。三公跟孙子三有住一块,大有、二有、三有,各家男丁单薄,三个堂兄弟,如同一个藤蔓上的三个瓜,一串串地结下来,透着热乎乎的亲热,如同一锅刚出笼的馒头。终究是没出五服,血管里流淌着的血液至少有一半是相同的,所以,对于接下来需要三公帮忙的这件事,大有充满了自信。不过,想想躺在床上的自家爷爷,他的心里还是充满了凄然,他就这样被孤零零地放在偏房里,没有鞭炮,没有香纸,让他走得寂寞而冷静,人走该是有灵魂的,爷爷回头看看自己的样子,心里会不会感到悲怆?可想到学娃,大有的心硬了硬,他伸出手,拍了拍三公家那扇厚实的木门。
“嘭嘭嘭……”拍门声在这深夜里格外刮人耳膜。“谁呀?”三有警觉地喊了一声。“大有,你大有哥!”一盏昏暗的电灯“啪”地拉亮了,然后是趿拉鞋子的声音,门“吱”地打开了,三有探头探脑地向外看,大有便迫不及待地挤了进来。大有来不及坐定,便迫切地说:“你大爺爷殁了!”三有连忙转身进房,拿一盏手电,披上外套,“我去看看!”说着,他立马红了眼眶,自己的父亲走得早,小时候也没少给大爷爷添麻烦。“咳!咳!咳!”一声接着一声的咳嗽声从三公的房间里传出来,大有朝那房间望了望,这咳嗽声与爷爷多像呀,毕竟是亲兄弟。大有一把拉住三有:“大爷爷殁的殁了,你哥现在碰到坎了……”三有奇怪地望着大有,看看自己家徒四壁的家,难道大有哥要借钱?想到这,他真有几分为难,自己前几天是卖了一只猪,收入八百元,给儿子喜娃送去了三百元,还了一百多元的猪本,剩下的都是账呢。三有搓了搓手,心里想,除了借钱,别的都好说。大有看着三有忐忑不安的样子,急急地压低嗓子开了口,三有听了大有的话,立马拍着胸脯保证道:“我后天就将爷爷送到你家去!这个忙我帮定了!”大有和香千叮嘱万吩咐:“兄弟呀,千万别走漏了风声,千万!”
大有和香走后,三有连忙关上大门,回到暖暖的被窝里。老婆兰掐了他一把,斜眼睨着他:“大晚上的,大有哥找你干吗呀?”瞒谁三有也不会瞒着自家媳妇:“大爷爷殁了,哥找咱们借爷爷。”“不借,送给他养!”兰说。“大爷爷殁了,我们明天得过去帮忙,早点睡吧!”三有将手放在老婆的奶子上,兰连忙拨回男人那只不老实的爪子。
三有睡不着了,索性揽着兰,将大有哥的打算和盘端了出来,兰“呼”地就坐了起来,她指着三有的鼻子骂道:“你答应啦?你脑子进水了?人家拿钱拿物,你得到什么好处了?你还得赔上自己的谪亲祖宗,这一移来一移去的,把人摔坏了,哪个负责?”爷爷的地位一下子高起来,高过了对面的王屋山峰。要是平时,兰可没这么金贵过爷爷,她总叫他老不死的。兰脾气火爆,三有拿她没办法。兰恨恨地哼道:“他们可真会打算呀!这忙……咱们可不能白帮,叫大有哥把那件皮袄子送给爷爷,也不枉咱爷爷辛苦一场!”兰的话如同一块烙铁,将三有狠狠烫了一下,可他做不了婆娘的主,他只好低声下气道:“我已经答应大有哥了!”“我问你,这个家谁说了算?”兰用力掐了三有一把。
大有和老婆香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回自己家里,后院里偏房那盏绿豆大的灯,权当爷爷的引魂灯。大有走进偏房,老人的身体已经完全僵硬了,他忍不住低声哭诉着:“爷爷,孙子不孝,连老也不让你安生地上路。”他握着爷爷冰冷的手,自己的老爹结婚晚去得早,山里人讨一房媳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爹近四十多岁才生了大有,可惜爹娘都不长寿,大有的记忆里更多是爷爷。爷爷背着生病的他去镇上看医生,差点摔死,可他硬生生将大有护得好好的,爷爷严重骨折,大有却啥事也没有……想到这里,眼泪像滚落的珠子,“爷爷,等县上的人来看咱了,我一定将你风风光光地送上山!”
二
大有倚在爷爷的床前守了一夜,恍然中,他梦见爷爷对他说:“孩子,我不计较风不风光,只是这种骗人的事……咱做不得呀!”大有哭着说:“今年种的果子全烂光了,学娃的生活费还没着落,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爷爷叹息着,摇摇头转身便走了,大有拼命追在他后面,爷爷越走越急,不像一个一百零五岁的老人,倒比孙子都走得快……大有慌慌的,结果就醒了,一抹脸皮,全是眼泪。
“大有哥,大有哥!”隔壁二嫚在门外探头探脑地说,“借你家的柴刀用一下。”大有一激灵,快步走到堂屋,抄起门后的柴刀,递给二嫚。换作以前,他会吩咐她小心着用刀,秋天来了,家家都要囤放过冬的柴火,都得用刀呢,现在,他只盼着二嫚快走,可这死婆姨偏偏朝着爷爷的房间瞟了两眼:“今天咋没听到你爷爷咳嗽呀?”“昨晚香给他蒸了紫苏鸡蛋。”大有连忙回应说,“你早点把刀还给我,下午我还要砍一截老树根给爷爷冬天取暖用呢。”听他这样说,二嫚一步三扭地离开了,大有摸摸自己的额头,都是汗……
大有没胃口,吃不下去饭,为了做出一切如常的样子,他让香蒸了红薯。他夸张地蹲在门口的槛石上,“呼呼”地吃起来。他努力回忆以前吃饭的样子,将自己如洪水般翻涌的心事,竭力压制下来,用习惯筑成情感的围坝,不让心事决堤。正吃着,三有从坡上过来了,大有连忙站起来,迎着三有,脸上挤出些许笑意,那副窘迫的样子,如同清早刷牙时拼命挤出的那点豆大的牙膏。这事操作起来的关键是三有,大有突然就不自然了,他的脸上布满了巴结逢迎,他清了清嗓子,问三有:“兄弟你吃没?”他原以为三有是过来看爷爷的,看爷爷应该带点糖或啥的,即使爷爷喝不上,也是山里的风俗,但三有空着两手,也许他是怕走漏了风声,大有突然释然了……
“大有哥……”三有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进屋后,他并没有提出去看爷爷,他吞吞吐吐之间,冒出来的话,让大有都脸红了。
三有盯着自己的鞋尖,仿佛鞋子上突然长出了一朵花。“你三公年纪大了,怕搬来搬去受凉!”三有含含糊糊地说。人老了,真是活成了一棵树,后辈不用驮或背了,用搬。大有望着门外,仿佛有一股透骨的凉风穿过自己的身体,他迷茫地望着三有一张一合的嘴。这个小自己五岁的堂兄弟,说着说着就脸红了。特别是提到羊皮袄子的事,羊皮袄子变成了一只夹手的螃蟹,让他的神情有一丝被刺激到的痛楚。羊皮祆是前年县领导来慰问,特地送给爷爷的,它不是全新的,五六成的成色,用手摸去,带着贴心贴肺的柔软,里面是厚厚的足有两寸长的羊毛。虽然是送给爷爷的,但香舍不得给老人穿,老是推托说,等老人走亲戚的时候再穿,除了收到礼物的当天,爷爷用手抚过一次羊皮袄,他不曾穿过一天。随后,香将袄子收了起来,大有懂香的那点小心事,无非是想留给自己穿。大有居然也眼馋上这件皮袄子,全村的人都眼馋,那天,三有媳妇兰还用手捻了捻羊毛,很有经验地推断道:“这绝对是一头小羊羔的毛,那么软!”
三有走后,大有捋了捋他的话,像要捋顺那羊皮袄上长长的毛。大有实在意想不到三有会来这一招,昨晚还答应得那么痛快……他阴着脸皮,推开香陪嫁的那个樟木箱子,这箱盖犹有千斤重,羊皮袄整整齐齐地放在木箱最上层。除了有一回,去香的娘家,香非得显摆,让大有穿着走亲戚,捂得一身汗,大有就再也舍不得穿了。
去年六月六那天,香还将羊皮祆拿到太阳下晒了一阵,不敢晒得太久,怕晒坏了。村里的女人经过门口,忍不住用手摸摸,香便摆出一副大方的样子,回来冲大有唠叨,谁谁谁那手粗糙得像砂纸,居然也不自觉,还去摸这金贵的袄子,她的神情里饱含着骄傲,因为这突然而至的优越感,香那晚还特意用艾叶给爷爷泡了一个热水脚。
这会儿,大有极不舍地将脸贴在羊皮袄上,那上面好像还有淡淡的太阳的味道,是微暖的香味,可这种香暖转瞬即逝,就像他和三有隔着辈分的亲情。
这时,香闯了进来,女人到底是沉不住气了,刚才,三有的话一字不落地敲打在她的耳膜上,像突然下的一场不讨喜的雨,她还打算晚上去找三有说道说道呢。可这羊皮袄的损失看样子是等不到她的挽救了,她的眼泪再一次汹涌而出:“你拿出去,还收得回吗?”她固执地捏着衣服一角,想篡改这件皮袄子的命运,大有黑着脸,冲她喊道:“松手!”香表现出空前的勇敢,可在大有用力的撕拉中,她心疼地松了手,宛如亲娘对待与人贩子拼劲撕扯的孩子。
大有将皮袄装进布袋里,一步一挪地向三有家走去。此时已是中午了,堂弟媳兰看到大有过来,脸上有喜出望外的神情,这种喜又被一种情绪刻意地埋藏了起来。这个不讲情面的女人,大有心里恨恨道!这事,他是怪不上三有的,要怪只怪他耳根软,降服不了这个刁钻刻薄的婆娘,平时一声“大有哥”,比自家妹子都亲,关键时刻,照样下刀子。
午后的时候,天突然阴了下来。二嫚来还柴刀,可能是自己心虚,大有总觉得二嫚话里有话,这女人的脸上堆满了浮夸的笑:“老爷子过两天生日,可又要热闹了!”大有连连点头,接过柴刀,慌慌地说要赶在下雨前去砍一担柴回来。大有是无心砍柴的,他像一株失了水分的植物,恹恹的。可他说要去砍柴,就必须装装样子。
大有将香喊到里房,吩咐她将爷爷的房门关好,若有人来,就说爷爷睡觉了。他让香守在堂屋,假模假样地拿着鞋底做女红。随后,大有阴沉着脸,拿着柴刀枪担上山了,远远望见一个人,他便努力挤出几分笑来。他此刻最不想见的人是村长,他还没想好怎么去应对他,偏偏不是冤家不聚头,村长夹着一支烟,从远处晃悠悠地走来了,他拍了拍大有的肩:“这两天让你婆姨将家里好好打扫一下,给爷爷洗个澡……别呛坏了领导!你狗日的摊上个好爷!”大有将头点得像鸡啄米,他心里还是有几分虚:“领导会来吗?”“人家吐口唾沫都像钉在板上的钉子!”村长摆出一副常与领导打交道的样子,大有连忙点头称是。
香坐在堂屋前,心不在焉地扎着鞋底,好几次针扎到了手,她的心里乱极了,她后悔自己对爷爷的那些怠慢,可老人说,阎王要你三更走,你便不敢五更亡,这是命呀,她又想。如果大有的阴谋暴露,会不会去坐牢呢?她的心里乱成了麻……
天色渐渐晚了,大有肩膀上的枪担两头,挑着两小捆柴,缓缓向家走来。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让香心痛,她真想说,咱不要那兩千元了,可这两千元的诱惑实在太大,一只老母鸡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下蛋,得下好几年呢。
三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天很快亮了,夜里少了爷爷的咳嗽,完全陷入了沉寂的状态。偶尔刮起一股风,让人不自觉地感到沉重,昨天的阴天,并没有一滴雨从空中飘下来,这个白天居然出了太阳,太阳一出,温度就上来了,香一连进了后院几次,她的心里揣着忐忑,这种情绪感染了丈夫,大有总觉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味道,他定定地瞧着爷爷,心里祈祷着一场雨……
早上,大有和香连早饭都没吃,他们吃不下去。大有一边絮絮叨叨,一边进进出出,仿佛爷爷还活着。他心中越来越没底了,越来越焦灼,好在过了明天,最迟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慢慢挨吧。可这一天的时日,硬生生地过成了一年,时光之无涯难挨,一眨眼都成了爬树的蜗牛,从春天萄萄树刚绽出芽尖,到结满萄萄,仿佛就漫长成了这样子。大有在堂屋搓一根麻绳,香还是装模作样地纳着鞋底,一天多下去,鞋底还是原样子!
“大有!大有!”门外响进村长的叫声,咋咋呼呼的,像一群被惊起的雀子,从大有的心头飞过,香立刻站起来,脸色也变了……大有看着自家婆姨的■,立马用眼神示意她躲到后院去,香像一只受惊的兔子,转身就走。
村长背着两只手,踱进屋里,他这样子有巡查视察的意味了。“昨天交代的事都办利索了吧?”“妥了,妥了。”大有掏出口袋里的香烟,十八元一包的蓝色黄鹤楼,还是过年的时候,香的侄儿顺手给了自己一包,大有听到村长的声音,立刻从堂屋的立柜里翻了出来,香烟经过漫长的七八个月,已带有几许陈年的气息。“你小子,混得好呀。”村长斜睨着烟,大有连忙递上火,递火的同时,心里一动,手一哆嗦,将整包烟都递给了村长,村长毫不客气地就接去了。他推开爷爷的卧室门,探过头来瞧了瞧:“咦,爷爷呢?”“阿香正给他洗澡呢!”后院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大有机灵得像个猴子。“你小子会来事!”虽然村长只年长大有五六岁,他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对待大有,充满了优越感!“上面的领导十有八九明天会来,你们就等着上报吧!”村长吐着烟圈,准备进到后院去。“别,别去!”大有连忙拦着村长,“老人三根骨头四根筋的……”村长脑补了老人丑陋的躯体,立马止住了步。“村长,哪阵风把你吹来了?”二嫚突然冒了出来,倚在门框边,一边嗑瓜子,一边朝村长抛着媚眼,村长立刻走出门去,去二嫚家嗑瓜子去了……
上午有惊无险,天气太闷了,燥热燥热的,大有的心越来越沉重。午后那阵子,突然起了一阵风,紧接着居然下起雨来,那雨噼里啪啦地砸在屋顶上,砸在门外的坪子上,气温立刻降了下来。没有冰块,也没有冰棺,老人当尽快入土为安,这陡降的气温,让事态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老天爷,真是活菩萨!”香激动地对着雨说。
香将爷爷床前的引魂灯,点得如豆般大。爷爷一张蜡黄的脸,布满了丘壑深的皱纹,充满了苍凉感。香在想,爷爷的魂魄也许就在这房间里,用他昏浊的眼盯着自己,直到看透她的心。现在,她心里又后悔了,后悔自己漫不经心,后悔那压箱底的羊皮袄,应该给老人多穿几回……她的心里一直祈求爷爷,帮助她和大有渡过这难关,山里生活的艰辛,如一把架在脖子上的刀,让人迫不得已往这条路上赶。“爷爷,最迟后天,定让你入土为安!”香在许下承诺的同时,心中也是不安的,因为这决定权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来访的领导手上。香又祈求道:“爷爷,让他们明天就来吧!”一个死了的人,力量是无穷大的,在香的意念里,爷爷可以左右这世上他成心所左右的,香突然又有几分笃定。
中饭时,香烙了几张葱花饼,葱花饼也是爷爷和大有最爱吃的。香在灶上忙碌着,大有在灶下沉默地烧着火,待烙好了饼,大有先用盘子郑重地盛一张,摆在爷爷灵前。如果死人真的有灵魂,爷爷一定会发现短短的两天两夜,他的孙子大有已变得像一个老汉,眼眶深陷,眼圈发黑,脸上的皱纹仿佛横生的乱线,头发乱蓬蓬的,黑发中平添了好多白发,这些陡生的衰老,像一群打入群众内部的异己分子,向全世界宣告,大有遭受了空前绝后的打击……
香极心疼自家男人,虽然她也好不到哪去。这种悲哀的日子里,烙饼是极不道德的,有着庆祝的意思,山里缺衣少粮,烙饼是只有过节才有的吃食,一年也烙不上几回的。大有这两天里,几乎没怎么进食,他在折磨自己,用身体的虚空来应对这种局面。可人毕竟是人,他嘴唇翘起的干皮,他无神的眼,仿佛比躺在偏房的老人都不如。香固执地做了烙饼,她盛面粉时,恶狠狠地舀了一大瓢,这可不是她的作风,她是一个精细的、会过日子的温婉女人,可这会儿,仿佛过了今天,不想明天……大有捏着香烙的饼,卷起来的饼中间除了葱蒜,居然还潜伏了一个煎得焦黄的鸡蛋,这婆姨啥时候煎的蛋,大有没发觉,他像被烫了一般,香注意到他的神情,眼里立刻饱含了一汪泪水。大有的心柔软了,他低下头,默默地大口大口地咬着饼……
午饭后,雨越下越大了,整个世界都笼罩在这铺天盖地的雨里。三有和兰共撑着一把大黑伞来了,这两人总是有点不同常人的作派,论长相,兰是不及自己的婆姨香的,可三有被兰拿捏得死死的,对于羊皮袄,大有心里清楚,这是兰的主意,不是三有的意思,但人家冒这么大的雨来,也算是自家人吧。
厨房的灶台上还躺着一个又大又圆的葱花饼,蘭吸了吸鼻子:“这烙的饼可真香呀!”香的脸腾地红了,红成了一片火烧云,像做贼被捉了一样。她慌张地端出饼子给兰,这一个饼,她自己都舍不得吃,想留着给大有当晚饭,可这厚脸皮的女子,竟然毫不客气地将饼接了过去。她揪下一小半给三有,自己留一大半,香看着兰吃得津津有味,心里已将她咒骂了一百遍:馋婆娘!馋婆娘!馋婆娘……她甚至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谁让你舍不得吃?活该!
也许是羊皮袄和烙饼垫了底,在大有家,兰做事倒卖力,除尘扫地捆柴火……大有和三有将爷爷的棺木倒腾出来,放在院子另一间偏房里。按照计划,等唬弄过了那一关,这些都是要派上用场的。香和兰还端出了几十斤面,炒面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出殡那天,是要请亲戚及村里的人吃饭的,吃食是大杂烩,做杂烩需要炒面,还有薯粉皮,这些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爷爷是再也等不得了……
灶上灶下的妯娌,各怀心事。兰一边炒面,一边咂嘴道:“两千块哩!”很心痛的样子,像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香连忙接话说:“谁知道呢……”密集的雨声掩没了厨房里的聊天声。因着那一件羊皮袄,大有三有香与兰结成了一个同盟,大有三有商量着,啥时将三公接过来,白天肯定不行,只好晚上了。兰说:“可别把爷爷给我摔坏了,我还指望他活到一百岁呢!”三有怕兰再迸出别的难听话来,连声说:“知道,知道!”
四
三有和兰吃过晚饭就回去了,雨大得像有人在天上拿一个洗脸盆往下泼水。大有今晚是不能睡的,他要守着爷爷,也许这是爷爷在家里的最后一晚了。他还要去接三公,三公是这场戏的主角,好在他的戏分不多,主要就是躺在床上,不过一旦有人拍照,就有点难办了,那些领导是分辨不出来真伪的,主要怕村长。想到村长,大有的眼皮跳了一下,心里又咯噔了一下……
从晚上六点多到十点多,雨还是下得铺天盖地,直到凌晨一点多,雨势才渐渐小了。山里的气候一下雨就冷,半夜更冷。
大有和香提着马灯,马灯在漆黑的夜里,像一团飘移着的鬼火。香撑着一把雨伞,山路湿而滑,一路跌跌撞撞的,香甚至摔了一跤,摔得好痛,裤子也摔破了,她强忍着一声不吭,更加小心地向三有家走去。
三有屋里亮着灯,门是虚掩着的,大有推开门,三有心照不宣地朝爷爷的房走去。三公睡着了,老人睡眠浅,像一条浮在水面的鱼。大有推开房门时,他便支起脑袋问:“天亮了?”三公说话口齿不清。人老着老着便老成了小孩,连语言功能也退化到了蒙昧状态。三公也糊涂了,他认不出大有是谁,多年的老花眼,所有的面孔,在他眼里全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香带了一床薄毯子,大有伏下身来,三有和香尽力将三公从床上抬起来,将老人放在大有背上。三公含含糊糊地问:“这是要干么事?”他极力想从大有的背上挣脱下来,三有有点不耐烦了:“房间漏水,换一间房!”老人终是听明白了,才放弃了无谓的挣扎。他更怕摔着自己,一双鸡爪般的瘦手,紧紧抓着大有的衣服,原来再怎么老也是怕死的。兰这个时候是没有露面的,这个婆娘早睡得像猪一样……
外面的温度比屋里低好多,香真怕将三公弄感冒了,她用毯子将三公包成一团。三有在一边帮衬着大有,香依然提着马灯,深一脚浅一脚,有两家的狗狂吠起来,大有恨不得将狗套上一个辔头,到底是有几分心虚,冷风一吹,将三公吹清醒了。他突然慌张地喊道:“别丢我!别丢我!”可能是兰伺候得不耐烦了,说要将老人丢掉,老人倒记得清楚,香连忙拍着老人的背,细心地安抚道:“不是丢你,不是丢你!”等到将三公安顿在爷爷的房间里,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香怕冻坏了三公,给老人泡了姜水脚,还喝了滚烫的姜水茶,老人心满意足地在床上睡着了。香盯着三公,终究发现了一些不同,爷爷的嘴角有颗痣,三公却是没有的,爷爷有几根眉毛长得像女子的头发了,三公也没有,眉毛倒好说,可这痣怎么办呢?那是没法装假的。香清楚地记得,村长曾特意说过那颗痣,可人老着老着,总不能连痣都长没了吧?香又慌神了,她嘀嘀咕咕地告诉守灵的大有,大有用力捻灭脚底的烟头:“事都这一步了,明早去找村长!”
老天爷仿佛生气一般,雨又开始不停歇了,大有和香商量了半晚上,最后觉得还是瞒不过村长的。天刚蒙蒙亮,大有给了香一大块去年腌的肉,让香去给村长送礼。香想起有一次去地里锄草,村长蹲在地沟边,没脸没皮地说了好多疯话,香生气发火了,村长才夹着尾巴溜走了。香不肯去,可大有说女人家好说些,如果他去,也许村长会生气,一发火会同他杠起来,到时候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香只好硬着头皮过去了。
大有家离村长家一里多路程,山里人家,房子像散落的蘑菇,东一间,西一间。香走得磨磨蹭蹭,恨不得将这一里多路,走成八里十里的距离,她实在有点惧怕村长,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开口。她一路心里打着小鼓,好几次真想回头算了,可她硬咬着牙,坚持向前走。
村长家还是不同些,清一色的红砖,香才走到门口,刚巧碰到村长从厕所出来,他一边系着裤带,一边清着喉咙,好像随时要发表啥重要讲话。香的脸腾地红了,她终究是脸皮薄,换成二嫚,老早将腰扭成麻花了。“村……村长!”香叫得嗑嗑巴巴,她的话像一个人走在一段泥泞的路上,随时有跌倒的危险,村长看着红了脸的香,又看了看她手里拎的一大块肉,知道是找他办事的,但这大清早,会有什么事呢?他急急地将香往屋里让,这婆姨五官真周正,这念头像个正躲猫猫的孩童,突然又冒了出来,让村长吓了一大跳,吓一跳的同时,他那双手居然不老实地握住了香的手,嘴里客气着:“还带东西来干吗?吱一声就行了!”香急急放下东西,村长却不干了,他推脱着,和香扭成一团,“村长,別!别!”村长突然觉得自己晕头了,他伸开猿猴般的双臂,将香用力圈在自己怀里,香用力挣脱,却是怎么也挣不掉,她的眼泪突然来了,急疾得像门外的雨:“村长,我还戴孝呢!”“戴孝?谁死了?”村长一下子蒙了,“我爷!”村长终于松开了香,香哭哭啼啼地说了整个事情,留下一脑袋浆糊的村长……
香撂下的话像一块大板砖砸在村长头上,怎么就死了呢?还死三天了?他昨天还接到镇上干部的电话,询问老人的情况,他还拍着胸脯保证,老人好着呢!一百零五岁,一棵老树长出这么多年轮,你连数都数不清……村长悻悻然地环顾着空荡荡的堂屋,他将自己的手对着空气圈起来,仿佛怀里还有那一团柔软。他陡然生出许多恨意来,居然敢给他设套,可这个套自己是鉆进去了,他无法打电话去镇上,说老寿星已经走了,说不定领导还会怪他说得不是时候呢,县上领导好不容易来这偏远的小镇一趟,否则这镇这山这村,像被一个顽童遗失在草丛里的弹珠,让人怎么也惦记不起。
“胆真肥呀!”村长一路走一路咬牙切齿,一块隔年的腌肉就想将他打发了,他要将腌肉还回去,他突然悟过来去还肉的目的了……他的脑海里晃动着香的眉目:这个木讷得如石头的女子,那瞬间的忸怩脸红,突然成了草丛里冒出的一朵花,这朵花现在就开在村长的心尖上,撩拨着他,让他的心痒痒的,像有一只毛毛虫爬过。他得将这只毛毛虫捉起来,大有他们不是有事求他吗?自己不是也平白无故地卷进了这圈套里吗?村长在心里反复自问,问着问着就变成咬牙切齿的愤怒了,这种愤怒又烧成了一团火,他得找香出这股火,他后悔自己早上的心软……“村长!村长!”路过二嫚家门口,嗑瓜子的二嫚来不及吐掉粘在唇边的瓜子壳,便用甜得浸了蜜的声音招呼着村长,村长懒得理她,一头扎进了大有家。
这个家静得像无风的湖面,可谁想到湖底下暗流涌动。村长推开大有爷爷的那间房,床上一个老人在昏睡,村长仔细端详了几分钟,大有的三公和他爷爷真有几分像呀,不是熟悉的人,还真瞧不出。这大有可真行!村长四处走动着,像一条在自己领域里巡游的鱼。
香犹如呆头鹅一样,木木地坐在灶台前,锅里的水已经烧开了,腾起了一股白色的雾气,突然而入的村长,让香吓了一大跳,村长还没问,香便慌张地说:“大有去三有家借东西去了。”村长举了举手中的肉,将它放在灶台上,意味深长地说:“不找他,找你!”女人分明脸又刷地红了……这个女人过于敏感的神经,总能激起村长探究的欲望,这一次,村长比在自己屋里大胆多了,他的心里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情绪,他上前就扑倒了香,灶前的柴火垛变成了男人和女人的战场,村长用力地将香往自己怀里拽,香拼劲向后倒,最后村长便服服帖帖地压在了香的身上。“别!别!大有回了!”香含糊的挣扎犹如春药一样,“大有会坐牢的!”村长紧咬的腮帮吐出的话,像一把无比锋利的小刀,香突然松开了自己的手,她像中了蛊般,居然主动脱掉了裤子,她低着头,眼睛里汪着泪水,她变成了一个合谋者……这时,突然有人狠狠地抓住了村长的衣领,他像一只受惊的虾子,扭头一看,原来是大有。大有恶狠狠地举起拳头,村长却挑衅地吼道:“打呀,往脑壳打!”大有却像突然被抽去了筋,软绵绵地放下了拳头……香惊恐地掩紧自己的衣服,泪水像断了线的珠串,大有重新举起巴掌,重重地扇在香的脸上,一个明显的巴掌印烙在脸上,像一个无比耻辱的标记刻在香和大有之间。香像发了疯般,冲向大有,大有恨恨地骂道:“贱货!”“我贱!我最贱!”香又像一枚发射出去的火箭,一头冲出了家门。
大有极凄惶地跌坐在地上,他感到头痛欲裂,他突然茫然无措了。他想到村长贴在香身上的手,恶心得想吐了。香在他的心中,人品比二嫚高出一个珠穆朗玛峰,可刚才的一幕,却让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婆姨居然不反抗?她居然任由村长压在她身上,她甚至有一丝丝享受的样子……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疯狂地刺激着大有的心脏,将他的心揪成一团。
“大有哥,大有哥,香姐要跳河呢!”二嫚像一匹受惊的母马,急匆匆地跑进来,“嗡”的一声,一群马蜂在大有的脑壳里炸开了窝,他强拖着自己疲惫的身体,跑向村后唯一的那条河。这几日里,他所遭受的人情冷落,像一场突然而至的冰雹,将他的心砸得千疮百孔,他突然觉得累了,累得喘不过气来,他也不想活了,和香一起去扑河,可学娃怎么办?他想起三有,三有拿走的羊皮袄,想起兰吃自家烙饼的心安理得,还有二嫚做贼似的探头探脑……这一切堆砌成一堆沉甸甸的稻草,早压在他的身上了,他随时会被压趴下,可香和村长偏偏又往这稻草上淋了几大瓢水……
香在后村的河边哭得撕心裂肺,人生的种种不值,让这个单纯的山里妇女彻底坍塌了,送出去的羊皮袄,送出去又还回的腌肉,最后连自己也差点被送了出去……以前堂堂正正的大有,这几天里变成了一个畏畏缩缩的矮个子!她心头上搁了一把锋利的刀,这刀随时会掉下来,将她的心切割出一个口子来。
一群人拉扯着香,香一副天塌下来的样子,她无法诉说这个沉重的秘密,这秘密让她对自己不齿,对大有不齿,对整个世界愤怒。村长也赶来了,他黑着脸皮,一直没吱声,这事毕竟跟他是有关系的。堂弟媳兰拉扯着香的胳膊,脸上的表情却分明有几分幸灾乐祸,一件羊皮袄与两千元比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可从大有送出羊皮袄的那一刻,兄弟间的情分犹如突然打了折扣的商品,兰是感觉得到的……大有看着狼狈的香,看着各色人的表情,他觉得从头到尾是一场闹剧,而他是一个荒唐的小丑,也像一只蹿上蹿下的猴,他累,他想要回自己的羊皮袄,他更想指着村长的鼻子臭骂一顿,继续演下去,他的把柄就在村长手里了,香迟早是要搭进去的……
大有挺直了腰,一步步走向香,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滚落了下来,这些泪水像一群迷路的孩童,它们一直堆积在他的心头,现在终于找到了出口。他可怜的爷爷,已经寂寞地躺了三天。大有冲上去,拉着香的手,对围观的人说:“我爷爷殁了……”话音刚落,三有的老婆兰说话了,“大有哥!”兰的嗓门像平地吹起的哨子,尖利得很,她突然心里漏了个洞,那件温暖的羊皮袄,她还盼着给三有穿着走亲戚呢,还有爷爷,她巴不得让他在大有家里待上十天半月呢,这一切都是应该的!村长也急急地凑近来,如果县领导这会儿动身出发了,大有顶多损失了二千块钱,而他这个村长,倒成了风口浪尖上的那一个!大有沉着脸,表情陡然变得坚定起来。他不再理会兰和村长,他一字一顿地哽咽道:
“我爷爷殁了!”
围观的村民连忙赞道:“香真是孝顺的好媳妇呀!”
没过一会儿,爷爷很快躺在了堂屋的硬板門上,引魂灯跳动着豆大的火苗,香插在了香炉上,纸钱也烧起来了,一阵鞭炮声突地响起,村民们冒雨向大有家奔去。这满世界的嘈杂声,惊醒了睡在大有家的三公,他带着一脸老人特有的茫然,从梦中惊起……
选自《黄石文学》2021年第1期

《一号码头》张立平布面油画60×100cm 2019年
责任编辑 张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