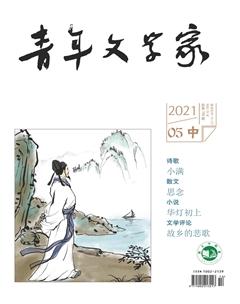试论日本近代小说《不如归》中的悲与美
郭晓梦 程雅倩
明治维新被看作是日本从封建社会步入近代化的标志,在日本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不如归》的作者德富芦花出生于明治元年(1868年)的一个世家家族,可以说日本近代社会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他成长,渗透在他的人生历程之中。该小说正是创作于这样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大背景下。
虽作为一部家庭小说登场,但《不如归》所描写的川岛武男与片冈浪子的凄美爱情故事直击无数被时代所累、受封建家庭压迫的青年男女的心,反映了明治时代的诸多黑暗社会现实,代表了大众心声,作者芦花亦因此一举成名。《不如归》与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齐名,被称为明治文学的两大畅销书,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悲剧文学的力量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作为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开篇首句,它是托翁借由安娜的悲剧一直扩展到所有家庭的幸与不幸中。无独有偶,《不如归》的故事发生在相似的背景下,由名叫浪子的女主人公承受着世间的一切苦楚,无论她身处何处、是何身份。悲剧文学总能够带读者走进凄凉、悲苦的作品世界,或使人悲愤或令人伤感……但这样的观感并不影响大众对悲剧文学的喜爱,正因它惹人无限遐思且饱含余韵,激起读者心中的那一丝丝涟漪实则蕴含强烈的冲击力,反而在世界文学作品的瀚海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同样是悲剧文学,日本作品作为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有其独特的色彩。即便是明治时期西方思潮涌入,也未能动摇日本几千年来深受东方文化影响的根本。委婉、细腻的表达以及东方女性的内敛、温婉中无不透露着美好易逝的哀怜美,这正是日本传统审美理念中倡導的“源于自然、融于心灵”的“物哀”。
德富芦花生长于日本传统世家家族中,从小受到底蕴深厚的家庭文化熏陶和东方文学的滋养,《不如归》中他时而凄美、时而铿锵、时而柔软与冷硬兼收并蓄的文字以及人物刻画无不令人动容,将这世间最真情亦悲切的“悲与美”发挥到了极致。
二、《不如归》中的悲
(一)源自原生家庭的悲
明治年间作为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动荡、阶层不稳,最为苦难的莫过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反观女主人公浪子,她生于上流社会之家,父亲是有名的陆军中将,母亲出身于官宦人家,理应是无忧无虑的大小姐,但却也难逃命运的捉弄。八岁母亲因病离世,这本就在她幼小的心灵上铺了一层阴霾,然而继母的到来更将她推向了家庭的边缘。
继母留英归来,追求西洋风习,个性自我,但心胸狭窄,见不得家中有前妻痕迹,甚至对家主片冈中将也事事评长道短,更别说她会善待前妻之子。
乖巧伶俐的浪子渴望母亲的关爱和照拂,但换来的却是继母的排斥、猜忌,使得八九岁的孩子就无着无落。“不被爱是不幸的,不能爱更加不幸。”继母不仅对浪子怀有成见,还不允许周围人与她亲近,妹妹、父亲,甚至家中女仆若略微亲近浪子也会被认为是对她领域的侵犯。如此迫于继母威慑的十年间,浪子压抑自己的情感,不得不自怜自闭隐忍地活着,仿佛一朵生在阴暗处的花。
(二)爱情困境
继母的压迫使浪子对新婚和未来生活充满了期待,满心欢喜地步入了川岛家。何其有幸,浪子能够得一知心人,与丈夫互相爱慕,感情深厚,伊香保度假的悠然、春日草间采蕨的欢快、平日里的嬉笑打趣、武男出征的往来书信……无一不印证着二人真挚的爱。然而福祸总是相依相伴,浪子在夫家虽有武男的疼爱,但同时也有一位“不懂道理、气度狭小、乖僻而极其任性”的婆婆。
武男父亲性格暴躁,动辄铁拳相向,其父在世时其母忍辱负重地在苦海中煎熬了三十年。待到其父病故,“川岛家的寡妇忍耐了三十年苦痛的水闸……立刻开放,水一下子都流了出来”“开始向周围人肆意地催索……” 仿佛要把之前的苦痛从周围人身上讨要回来,儿媳浪子正巧成为婆婆的被索取人。加之武男是川岛家的独子,与浪子越是亲昵,越易招致婆婆的嫉妒与不满。武男是海军,征战在外时日多,浪子与婆婆的相处也越发不易,她甚至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婚前的阴暗世界,但无论如何都极力委屈自己侍奉公婆。
不过一年光景,浪子意外染上了肺结核传染性极强且治愈不了的绝症,当时被认为足以毁灭家族的可怕疾病。小夫妻情深,婆婆见劝说儿子无果,遂趁武男出海之际不顾情理地强行将浪子遣回娘家。蝉能够脱壳,人却不能摆脱自己,浪子被离婚非二人所愿,薄情的婆母与无情的结核就像两座翻不过去的大山横亘在两人之间,强大的外力将他们推入了爱情困境的深渊。
(三)对现世的无奈
“世间没有像梦那样自由,武男本确信两人的关系是死也不能切断的……却不能不感到这区区的世间风俗惯例在企望和现实间筑着一堵不可超越的障壁。” 他出海归来面对浪子被母亲以他的名义逼迫离婚的结局是何其悲痛,见她、接回她竟成了“世间所谓的义理体统之下不能做而又办不到的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千百年来的封建传统岂是明治维新伊始的一朝一夕可改变,任凭武男如何与母亲争辩,终抵不过所谓的川岛家存亡与母亲独断专行的家族权威。“我要活,要千年万年地活下去。”这呐喊声源自浪子强烈的求生欲望,但肺结核宛如命运陷阱,不仅让她毫无招架之力,更是那个时代所忌讳的死症。生的欲望越是强烈,结核不治的绝望就越发凸显,“要活下去”终不过成了一句空嗟叹!
若说结核无情,封建家族制度的压迫更是冷酷残忍的典范,武男与浪子意欲抗争,奈何难以冲破这意想不到的桎梏,徒留对世间无奈的悲切。
三、《不如归》中的美
(一)落花般的瞬时美
缘何日本人对樱花怀有特殊的情感?樱花总是于满开的最盛时期因小风、春雨而四散飘零,最能体现日式传统审美情趣中的“瞬时美”,越是美好的事物越易消逝。作者通过浪子呈现给我们一个唯美、羸弱而哀怜的女主形象,文中多处通过细腻的自然描写暗示浪子的一生如昙花一现、如樱花飘零,终骤然消逝归入尘土,然留予读者无限的美感。
武男与浪子春日采蕨归来时,“夕阳辉煌地照射过来……屹立在各处的孤松把长长的影子投射在草原上……举目四望,见远山静静地浴着夕阳。”通篇中类似的黄昏意境多次出现。黄昏是一天入夜前的最后一缕光亮,在文学作品中多以衰落、颓败、哀愁的意象形式出现,不论人物、事运……大多象征着命格或时运的末路。但夕阳余晖短暂的美和照耀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悲凉之感,使哀婉的意境反增一丝温情的余韵。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母亲离世前的幼年时光、父亲悄悄给予的爱抚、婚后与武男不到一年的相处,好比浪子悲哀的一生中瞬间的美好,也正是这短暂而零星的美好支撑了她的一生,终消逝在如花似玉的桃李年华。
(二)凄凉的孤寂美
浪子从新婚直至逝去不过匆匆三载,其间二人厮守的日子尚不足一年。“既做了军人的妻子,多离别是意中事。然而新婚不久的别离,分外使人肠断,好像失去了掌中的宝玉,空落落地几乎手足无措。” 温婉而低调的浪子在夫家谨言慎行,丈夫长年出航在外,纵有万般不舍也默默等待他归来。中篇里别墅疗养期间,武男出海前最后一次探病离开时“但见一钩残月凄凉地挂在松树上”,残月挂松枝。“松”与“待”在日语中发音均为まつ,借松树一语双关,徒留浪子空寂地等待;残月在东方文化中寓意不完整的美,此处正暗合了二人不得团聚的遗憾,孤寂之感借残月得到升华。
离开前浪子三声“早点回来”的呼喊成了武男出航在外萦绕心头的慰藉,然而此次离别后的重逢竟成了奢望。恐上苍也可怜这对苦命的人,赐予武男奔驰的火车上最后再见一次浪子即将消逝的昙花泡影之身。
離别仿佛总与孤独、伤感之间有一条看不见却斩不断的丝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在东方传统中,渡口、关隘等常作为离别场所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近代以来,火车的大众化让车站逐渐取代了以往的离别场所。人多而繁杂的车站、车厢使私人的离别融入了大众空间,车站拥挤喧嚣的人流进一步烘托了别离二人的孤寂心境。武男与浪子生前最后一面就发生在不经意间交错而去的两列奔驰的火车上,发狂般扑出窗外的上身、挥动的绛紫色手帕、淹没在火车轰鸣声中的叫喊……无一不印证互相思念的心,无奈二人带着伤感和苦恨随着南来北往的滚滚车轮擦肩而过、渐行渐远。
(三)时代的呼声美
通篇小说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武男与浪子真挚的爱,以及在封建家族制度压迫下陷入爱情困境终至抑郁身亡的惨剧。在那个黑暗阴冷、残酷的旧世界,人微不足道,尤其女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这是时代的悲哀,但作者提倡人道主义精神,主张民众自由。
浪子意图跳海自尽未果,被海边妇人清子所救,清子向她讲述了自己艰难困苦的人生历程,并向她推荐了《圣经》,期望给她生的希望和力量。“读着读着,仿佛山中迷路的人听到某处的鸡鸣声,又仿佛漆黑的晚上从某处射来一道微光”,清子作为基督教徒的人设暗含了作者意图借助西方思想的力量拯救现世,以及对女性大众苦难遭遇的严正抗议。作者通过作品站在文明开化的立场上鞭笞了腐朽封建制度的不公,作为近代畅销小说,希望借此能激起大众心底对现世的不满,激发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新时代女性对个性解放的追求,这必将是时代的呼声,是社会前进的力量。
四、结语
时代的呼声虽美,但文明开化的进程非一朝一夕可以推进,封建制度对人思想的禁锢也非三年五载可以解放,整个社会从外到内、从物质到思想的开化必是循序渐进展开的。浪子的故事虽然凄美,但唯愿她如浮萍一般短暂而飘零的一生和无处安放的灵魂到此为止,绚烂之后的生离死别不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