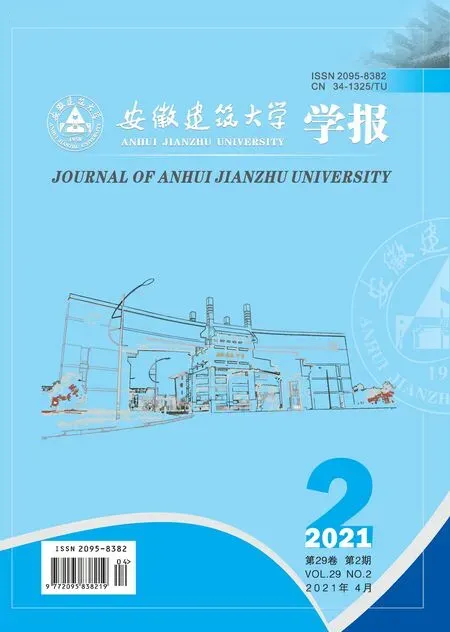安徽省农村居民点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汪勇政,余浩然,唐婷,蒋娜
(1.安徽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601)
农村居民点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农村居民点是农村人口生产、生活等功能的载体,是农村人地关系的核心体现。而农村地域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及土地利用转型都与农村居民点的用地变化息息相关。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城镇,农村居民点的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加速转型,出现了如农村空心化、环境破坏、土地粗放低效利用等问题,乡村物质与社会空间面临严峻挑战,成为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的阻碍。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实现乡村现代化。在此背景下,乡村聚落发展成为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当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内容上着眼于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时空演变与驱动机制、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整治分区与时空配置评价等方面开展研究并取得新进展。从研究尺度上,近20年来关于农村居民点变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微观样本村庄的研究;且已有的农村居民点变化研究受制于数据获取难,对于农村居民点长时间变化监测的研究较少。目前以地理格网为研究单元在土地利用上的应用是从综合角度进行统计分析,能客观准确地描述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变化特征,所以国内外学者常以公里格网为基本研究单元进行数据分析。而在研究农村居民点的空间类型变化上选择县域为研究单元,因为县级层面是土地管理及相关政策执行落实的基本单元,研究县级层面的农村居民点变化特征有利于探讨当前农村土地利用困境的内在原因及调控策略。在研究方法上,相关学者利用核密度分析与综合指标法探究农村居民点增减变化的真实情况,使用地理探测器通过因子分析模块深入分析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影响因素。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基于安徽省县域单元,利用多时期安徽省农村居民点栅格数据,运用综合指标法、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揭示安徽省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数量特征、用地变化类型和空间格局变化影响因素,以期为今后安徽省因地制宜制定农村居民点调控管理政策、综合整治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安徽省(114°54′-119°37′E,29°41′-34°38′N)位于中国华东地区,临江近海,有八百里的沿江城市群和皖江经济带,省域面积为14.01万km。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具有多种经济发展类型,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要冲和国内几大经济斑块的对接地带。其中农村内部地形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全省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呈现不协调的总体趋势,在县域、公里格网等尺度中表征出更加多样的变化类型。1995~2015年间,全省农村常住人口从4792万人减少到3041.1万人,而农村居民点面积由100万hm增加到115.14万hm,截至2020年4月,安徽省下辖16个省辖市,8个县级市,53个县,44个市辖区。在全省农村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下,乡镇地域农村居民点面积增加与人口减少的现象并存,农村居民点分布状况分异明显。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村庄发展历程,1995年农村处于无管控、自发生长的阶段,2005年后新农村建设使得村庄环境发生巨大改变,2015年美丽乡村阶段,农村进一步发展。所以选取1995、2005和2015年安徽省统计数据和空间数据进行研究。主要数据包括:①1995年、2005年、2015年3期高精度(30 m×30 m)安徽省土地利用栅格数据来源于中科院资源与环境数据中心,利用ArcGIS平台处理提取后,得到3期农村居民点斑块数据。②安徽省高程数据、行政区划数据。③农村人口、经济数据来源于安徽省各县市统计年鉴。
2.2 研究方法
2.2.1 核密度分析与景观格局分析
通过核密度分析法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邻域中的密度,来反映要素在空间区域上的疏密情况。其可以直观地描述某一地理区域的点是否处于集聚状态。使用景观格局分析通过简单的定量指标来反应安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景观格局信息。选取CA、MPS、MSI、MNN、PD、NP、PSCV等指标,采用Fragstats 4.2软件计算景观格局指数。
2.2.2 综合指标法
国内学者常利用综合指标法分析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增减趋势,研究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及类型判别(表1),常采用净变化率(land net rate,LNR)表征研究时段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的变化,式(1);采用结构变化率(land structure rate,LSR)表征研究单元用地的增减变化的急缓程度进行划分,式(2)。

表1 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划分标准

LNR
、LSR
分别代表第i
个单元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的净变化率和结构变化率;D
、D
分别代表研究初期和末期第i
个研究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T
、T
分别代表研究初期和末期第i
个研究单元的城乡建设用地数量(含城市、建制镇和农村居民点用地)。2.2.3 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
探究所研究因素的空间分异性,解释其背后驱动力的计量方法,是探测地理要素空间格局成因和机理且稳定可靠的重要方法。地理探测器包括4个探测器,其中分异及因子探测器是用来探测Y
的空间分异性;以及探测某因子X
多大程度解释了属性Y
的空间分异。用Q
度量,Q
的取值范围[0,1],数值越大,表明该因素对安徽省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异的影响越大。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尝试解释县域尺度下,1995~2015年安徽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的主要因素。其模型如式(3)、式(4):
3 结果与分析
3.1 安徽省农村居民点空间变化特征
3.1.1 农村居民点空间密度分布变化
基于1 km格网研究单元的安徽省农村居民点核密度分布的地域差异性明显,以安徽省中部为界限,形成“皖西南稀少型”与“皖北密集型”两个空间极化区域(图1)。

图1 安徽省农村居民点1995~2015年核密度分析
安徽省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点整体密度20年来较为平稳。由于合肥市是安徽省省会,有着对周围农村的强吸引作用,村庄发展方向会向其偏移,1995~2005年合肥市区周围的农村居民点逐渐增大,形成大范围、高密度的连续区。2005~2015年居民点密度再次发生改变,合肥市周围农村居民点密度和范围下降,这是由于农村居民点发展到一定程度,因其形成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为逐渐城镇化。另一方面,合肥市因自身发展会向外延伸发展,带动周围的农村居民点发展。
3.1.2 农村居民点景观指数分析
1995~2015年间安徽省农村居民点总面积(CA)逐渐上升(表2),净变化率为14.8%。NP、MNN在20年间先增大后减小,PD、PLAND数值逐渐增大,表明研究区在2005年前发生独立于原居民点的扩张,而2005年之后居民点逐渐集聚,新老居民点结合在一起,拓宽了原居民点斑块边界,PSCV近20年来一直扩大,表明农村居民点的斑块面积差异扩大。MPS数在1995~2015年逐渐增大,表明安徽省农村居民点破碎化程度下降,整体异质性降低,更加均质化。总体来看,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规模逐渐增大,个体斑块间的集聚性增强,斑块更加大型化,结构更加紧凑。

表2 安徽省1995-2015年农村居民点景观指数分析

图2 安徽省1995-2015年县域单元农村居民点变化类型
3.2 安徽省农村居民点变化类型划分
将安徽省农村居民点变化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类型划分,第一阶段1995~2005年,第二阶段2005~2015年(图3)。1995~2005年,全省农村居民点数量呈现总体增加趋势,总增加量为5 9615 hm,全省农村居民点净变化率为5.9%。农村居民点用地在城乡建设用地中的占比由91.1%下降到89%,农村用地增速低于城镇用地。
第二阶段中,安徽省农村居民点面积减少的区域占总研究单元的8.6%,分别是阜阳颍州区;蚌埠市淮上区、蚌山区;淮南市八公山、谢家集区、田家庵区;滁州市琅琊区;合肥市包河区与庐江县。其农村居民点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位于市区增长边界内,因市区人口增多,需要向外发展,使得农村居民点受到政策和经济的驱动影响搬离、拆迁或就地城镇化。
在县域研究单元的类型划分中,第一阶段划分出4个类型,增长型活跃区占研究单元总数的21%,大多分布在皖中、皖南地区;增长型迟缓区占研究单元总数的20%,平稳型活跃区占研究单元总数的21%,在省域内多分布在皖南地区;平稳型迟缓区占研究单元总数的38%,多分布在皖北及皖西南地区。第二阶段划分出5个类型,增长型活跃区域占总研究单元28.6%;增长型迟缓区占研究单元的25.7%;平稳型活跃区占总研究单元的9.5%;平稳型迟缓区占总研究单元的31.5%;减少活跃型区域占总研究单元的4.7%。
3.3 地域用地数量空间自相关分析
从宏观角度观察两个阶段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的特征,可以对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格局与分异规律有着准确的认知,有助于在更小尺度上评判不同区域的要素特征及内在机理。基于对市域尺度的认知,对安徽省县域尺度进行全局自相关分析,计算得到1995~2005年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全局Morn’s I指数为0.425,P
值为0.05,Z
值为6.6。2005~2015年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全局Morn’s I指数为0.497,P
值为0.05,Z
值为7.86。表明县域尺度下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的空间分布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全局自相关只能判断出研究单元的数量变化存在同类聚集现象,但其空间集聚格局如何尚不明确,需要使用Local Morn’s I指数分析,得到两个阶段LISA空间聚落图(图3)。
图3 安徽省1995-2015年LISA空间聚落图
(1)安徽省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高值集聚区在1995~2005年集中在安徽省中部、东部以及东南区域。此区域内地形平坦、耕地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区内二三产业相较于安徽省其他地区较为发达,能够为农民提高丰富的非农就业机会,农民城乡兼业化现象较多,易受到周围大城市的经济辐射,收入水平领先安徽省其他区域,改善自身居住环境的能力较强,故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变化较快。2005~2015年高值集聚区,分布出现“带状”连续性空间且分布在安徽省东南部地区。旅游业兴起对皖南地区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皖南凭借自然景观吸引众多游客,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很多农民依靠旅游业完成了房屋的更新。旅游业的发展伴随着旅游村庄出现商业化的现象,村庄因此而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旅游业也会带动村民自发在新的地点形成民宿餐馆等具有商业性质的居住房屋,从而扩大的农村居民点面积。
(2)1995~2005年,低—低聚集区域主要分布在亳州市大部分地区、六安霍邱地区、安庆市山区,区内由于水土资源匹配较差等自然条件的限制,村落规模小且散落分布,加之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低下,村庄更新慢,用地变化落后于安徽省其他区域。2005~2015年,低—低聚集区域出现在皖北大部分地区以及安徽省中部。皖北地势平坦,耕地面积广,人口众多。部分农民因文化水平较低、技能较差,只能依靠农业提高收入,而大量青年外出务工,前往城镇或者跨省前往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靠着原始的资金积累使得出现城乡跨越式发展。他们直接在城镇购买房屋,不选择在农村建新屋。整体农村居民点面积增加速率较低。
(3)高—低和低—高区域在安徽省内空间分布较为离散,产生“孤岛现象”,集聚特征不显著。
3.4 安徽省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变化的驱动因素
一般来说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是在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形成的,而快速城镇化下的社会经济、人口、土地管理等因素是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主要原因。为了更加深入揭示安徽省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的驱动因素,综合考虑指标代表性、数据可获取性、指标可量化性等因素,参考相关研究基于县域行政单元尺度,以安徽省1995~2015年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为因变量,选取X
1农村人口、X
2农村人均收入、X
3人均耕地面积、X
4人均粮食产量、X
5人均GDP、X
6农用机械总动力、X
7农林牧渔总产值、X
8第一产业占GDP比值、X
9农村户数、X
10城市化率、X
11农村就业人口比重、X
12高程共12个数值指标和空间形态属性指标。利用ArcGIS平台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对指标进行离散化处理并分为6个等级,处理后利用地理探测器进行数据处理。利用因子探测器来确定各影响因子对安徽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的影响程度,计算Q
值结果如图4所示。排名最高的前五位驱动因素分别农村人口、人均粮食产量、农业机械总动力、高程、农村人均收入。
图4 地理探测器各因素q值
农村人口增加是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点面积变化的主导因素。人均粮食产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人均收入直接影响的是农民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提高后农民需要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会一定程度增加住房面积。高程作为影响农村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制约条件,对于居民点用地增加也起到关键作用,安徽省南部多山而北部为平原,山区农民会在收入提高后出现将新房建于地势平坦、可达性较高的地方且受地形影响易出现“建新不拆旧”的现象,这也反映了皖南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比皖北用地数量变化较为剧烈的原因。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本文基于安徽省县域研究单元揭示了安徽省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基本特征。皖北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净变化率及结构变化率弱于皖南地区,存在市区周围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的情况。
(2)空间特征上,安徽省20年来农村居民点密度最大地方分布在安徽西北部地区,形成“皖北密集区”和“皖南稀疏区”。县域尺度上,皖北的用地变化类型平稳型迟缓区占主导地位,皖南地区用地变化类型则多为增长型活跃区和增长型迟缓区。
基于县域尺度的空间自相关分析,高值集聚区在1995~2005年集中在安徽省中部、东部以及东南区域,区域内地形平坦、耕地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2005~2015年高值集聚区,分布出现“带状”连续性空间且分布在安徽省东南部地区。1995~2005年,低—低聚集区域主要分布在亳州市大部分地区、六安霍邱地区、安庆市山区;2005~2015年,低—低聚集区域出现在皖北大部分地区以及安徽省中部。
(3)安徽省县域农村居民点的用地格局是在多重因素下综合影响形成的,农村人口、人均粮食产量、农业机械总动力、高程、农村人均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的主要因素。人均GDP、农林牧渔总产值、城市化率对于安徽省近20年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影响较小。
4.2 建议与对策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居民点面临着空间重构、功能优化等发展模式的转变,农村土地结构的优化调整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合上述分析与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土地的集约利用与合理配置是农村居民点优化的重要手段。由于农村宅基地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农村建设用地出现只增不减的现象,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空心村以及农村建设用地无序蔓延的不良现象。而我国城乡规划往往忽视了农村地区,导致村庄规划缺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本着“问题导向”的原则国家应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引导作用,强化土地用途的管制,本着耕地红线不动摇的原则,控制建设用地、创新生产经营模式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安徽省城乡发展目前处在不平衡的阶段,应因地制宜推进政策供给。
(2)在城乡融合背景下持续推进公共服务服务设施均等化,中心村镇的人口集聚是大势所趋,自然村的数量减少也是必然结果。因此,中心村镇的生产生活功能急需提升。坚持城乡统筹发展,转变农村与城镇发展的旧思维,发挥城镇总体规划对农村的促进作用,促进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优先向中心村镇倾斜,强化农村与城市的双向联系,积极推进农村人口市民化。通过资金投入、政策倾斜、人才市场要素流入等措施吸引农村人口向中心村镇集聚,引导偏远山区自然村庄的合并。
(3)加快构建农村居民点统计与监测体系,采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构建,实现对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总量控制、结构合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