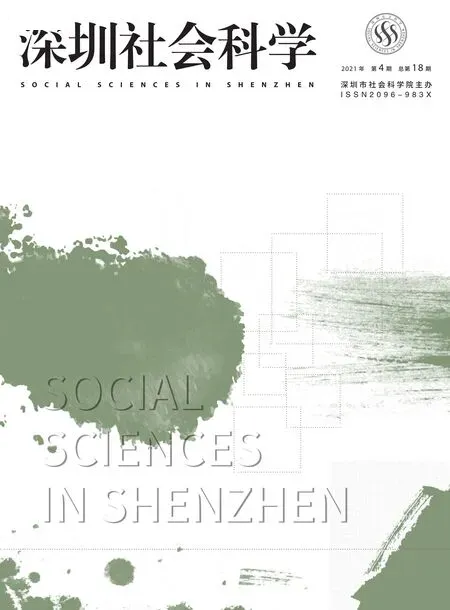中国社交用户头像选择的文化解释*
林升栋 吴晶晶 易 苑 刘红琪
(1.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2.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一、一个观察
近年来,社交网络媒体迅速崛起,为传统的人际互动增添了新的交往渠道和方式。以国外的Facebook、Twitter,国内的微博、微信等平台为代表,社交平台已成为当下各国人民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媒介技术重塑着人们的现实生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在社交媒体上也呈现出一些相异的媒介使用行为。以社交媒体头像为例,我们观察到:在美国社交平台,用户们常常将自我照片用作头像,其中大多是个人正脸的特写自拍,他们的头像就是其本人的真实头像。Facebook译名“脸书”,来自传统的纸质花名册,通常美国的大学和预科学校印有学校社区所有成员的“花名册”发放给新来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帮助大家认识学校的其他成员,因此,清晰的脸照是不可或缺的,脸书明显继承了这一传统。Twitter英文意思为“(人因兴奋)嘁嘁喳喳地讲;(鸟)叽叽喳喳地叫;格格地笑;(激动得)抖颤”,强调了面对面交流的口语性。尽管新浪微博是模仿Twitter,人人网模仿 Facebook,然而在中国的这两个社交网站中,却很少能见到将自我容貌特写展示的用户头像,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其它客体事物,例如卡通动漫、风景花朵、萌宠动物、明星偶像等。从研究者的观察来看,目前中国最热门的社交平台微信也是如此,很少有用户采用真人头像。
这种差异具有普遍性吗?如果是的话,在中国,人们为何不爱用真人头像作为社交媒体的头像?为何会选择“非身体我”的其它客体事物来呈现?这些“非身体我”的客体与自我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中美社交用户对于头像的选择为何存在着这种各自的偏爱?
二、对观察现象的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美用户在头像选择上确实存在不同偏向,本文选择中美两个属性功能最为接近的开放平台——微博和Twitter进行头像抓取。研究者借鉴前人做法,在采集头像时兼顾样本的多样性,先按一定标准抽取用户,再提取用户所公开的头像。[1]
用户抽样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美各抽取100名用户,为了保证样本所涉及的用户具有较大的异质性,来源地区不局限于中美两国的局部区域。借助微博和Twitter的高级搜索功能,利用平台提供的定位信息,[2]研究者首先将中国大陆的省级行政区按照首字母进行排序,根据随机数生成器生成10个数,以此选出10个省级行政区(安徽、北京、黑龙江、湖北、江西、江苏、内蒙古、宁夏、山西、云南),随后将微博的定位改为相对应的10个省级区名称,分别选取每个省同城微博展示的前10个用户的头像。研究者以同样的方法在美国的50个州中抽取了10个州(维蒙特、纽约、宾夕法尼亚、南卡罗莱纳、田纳西、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俄亥俄、堪萨斯、科罗拉多),每个州选取了10张用户头像。
小规模的抽样结果显示,在微博的100张头像中,只有25个用户使用真人头像,非真人头像用户高达75%。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中国的真人头像中多呈现出背影、侧面角度以及中远景构图,脸部特写头像仅有9张,在为数不多的真人头像用户中占比仅为36%。而Twitter的100张头像中,真人头像高达82%,其中,脸部特写图片60张,在为数众多的真人头像中占比73%。当然,微博和Twitter的用户数以亿计,本研究的小样本可能还存在较大的误差,将来可以做更大规模样本以提升精确度。由于本文的重心不在此,我们采用同样的方式二度抽样,得到相似的发现,两种偏好已经显示出来。
从小样本分析中,中国人更愿意选择非真人头像,在真人头像中,也会更偏向低头像容貌展示度;而美国人更喜欢选择面部清晰的真人头像,展示个人真实的容貌。另外,采用真人头像的中国用户明显有美颜以及摆拍痕迹,较为精致;相反,美国用户的真人头像更为真实自然,面部瑕疵和细节清晰可见。
三、文献回顾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媒体包围的环境中,通过图像、声音和眼睛来帮助创造日常生活的结构、支配闲暇时间、塑造政治观点和社会行为、并提供人们伪造身份的材料。[3](P1)其中,社交媒体头像成为个体在虚拟世界中自我披露或形象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越来越受到个体的重视。[4]对此,学者也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
从西方的研究来看,可能是基于西方用户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中展现真人头像的事实,研究多从图像视觉分析的角度,集中于脸部的美学和面部特征上,通过对图像中的面部表情识别、情感识别和情感分析,从而揭示人格特质。[5]已有研究表明,用户可以从他人头像中获得较为准确的个性印象。[6]众多学者也借助大五人格的调查分析来验证头像反映的个性猜测,[7]以及从用户喜欢的头像中提取美学和视觉特征来了解用户偏好,[8]推断用户个性。[9]
与国外研究不同的是,国内对头像的研究更注重心理分析,集中于个体对头像的使用动机方面。李翘楚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提出,个体在理解一个非自我中心化的世界中,交往行为离不开互相理解,而头像的存在就是为了传递个体的内在精神。[10]杨嫚等人研究了微信用户头像的使用动机,结果发现娱乐动机、扩新动机、从众动机是影响头像选择的主要因素:持娱乐动机的用户倾向于非真实、修饰、面部遮挡的头像;持扩新动机的用户更倾向于真实、原创、面部清晰的头像,展示真实且清晰完整的自我;持从众动机的用户更愿意选择侧面或背面照片,相对较为保守。[11]但这些研究还未能由表及里地揭示出头像之于个体的深层文化意义。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学界开始意识到头像并不是简单的个性反映和动机传递,在线身份通过积极的图片,描述了一个人的社会期望和展现。[12]这些身份被仔细地构造以反映社会和文化规范,看似独立的在线身份的产生不是天生的行为,而是对个人所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反应。数字世界中人类用户的虚拟自我能够反映用户认识自己的方式以及对自己的期望,[13]是自我在想象空间的身份建构。
自1892年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自我引入西方主流心理学研究以来,对“自我”的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对此,中西文化对“自我观”的界定也是不同的。受西方一以贯之的“独立”“自由”文化影响,西方人倾向于将“自我”看作独立的个体,强调“我”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是一种“存在的体验”。与之不同的是,在群体取向的中国社会体系下,自我嵌套在社会关系之中,“自我观”涉及个体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人际关系以及自我修养等方面。[14]王星河认为“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的哲学观造就了中西方之间的差异,[15]由此产生的相依型与独立型自我理论也已成为自我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文化概念。[16]
中西方两种自我观各具特色,这种特色应当会在自我参与社会互动中有所体现。以头像为例,用户对头像的选择并非是随意的,头像中的形象、色彩、行为举止都折射出既有的文化传统和自我建构的特点,人们可以借助头像更好地进行自我表达与自我呈现。西方对头像的研究,由于其主流是使用用户本人的真实头像,也因此少有关注不使用真人头像的现象。中国对头像的研究,主要关注使用动机,也没有在使用的头像图像与其自我之间深究。本文认为,中美社交媒体用户在使用本人真人头像与非真人头像方面的整体性偏向,正是中西方自我观差异在虚拟网络中的具体呈现,因此很值得对“我国社交用户为何少用自己的真人头像作头像”这一问题进行文化学与民族学角度的研讨。
四、研究方法
由于微博的活跃度已经下降,目前最为活跃的社交平台是微信,本文从用户使用的实际情况,以及上述观察的跨平台适用性出发,选择微信用户进行研究。与微博用户头像呈现情况相似,我们通过自己的微信群也观察到,微信的中国用户同样较少使用自己的真人照片作为头像,尤其是脸部特写的照片。为了探讨中国用户规避使用真人头像的原因,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对28位微信用户进行访谈。受访者相关信息如表1所示。半结构访谈提纲包括以下六个问题:

表1 受访者资料
1、您为什么使用这个头像?
2、换上这个头像后,您还会经常点开,观看这个头像吗?
3、您如何理解您和这个头像的关系?这个头像能否代表您本人呢?
4、您希望通过这个头像向他人传达什么信息吗?
5、您是否担心别人不能理解您的头像?
6、您用过自己的真人照片做头像么?(若没有,为什么?)
五、我们为什么少用自己的真人头像?
(一)差序关系与隐私保护
访谈中,超过半数未使用真人头像的被访者都提及是出于隐私的顾虑而未使用,顾虑的对象大多指向社交距离较远,尤其是在线下未曾有过较深接触的人群,例如“不认识的淘宝店家”“别人推的微商代购”“不怎么熟悉的以前同学”“没怎么见过面的亲戚”等。“如果是不认识、不太熟的人,没什么必要给别人看吧。”(S24)在受访者看来,自我形象是一种个人化的东西,会因为社交距离的远近而考虑是否需要开放。但不同于朋友圈的内容,头像的展示无法进行细致的分类管理,尤其是在线上加好友时,这种“隐私”将会直接暴露在“陌生人”面前。“我还没了解到对方长什么样,就让对方看到自己长什么样,感觉怪怪的”。(S13)从受访者角度而言,自我形象的分享与披露需要建立在双向连接中,伴随着社交关系的深入而选择开放。如果一上来便进行自我形象的袒露,会让这些受访者感觉自己与他人交往尺度有些失控,“好像裸奔一样”。(S13)而当问及是否会怀疑这些“陌生人”利用照片做一些触犯自我隐私安全的行为时,不少受访者却持否定或者怀疑的态度。虽然也有小部分用户提及担心微信授权各种应用软件,容易带来自我信息的泄露,但总体而言,受访者对此表现出的风险意识并不太高,“我觉得不会真的那么严重吧,毕竟一张照片也干不了什么。”(S7)可以说,在真人头像的隐私问题上,比起实际性的侵犯行为,就多数用户而言,对于隐私的敏感更多来自心理安全的需求,“还是心里觉得不舒服,就是不太想给那些人看”。(S7)
与许多中国用户对真人头像抱有较深的隐私顾虑不同,国外文献表明,美国用户对使用真人头像普遍持有开放的态度。这样一种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异,十分类似于双方在线下的日常礼仪:美国人习惯招呼与搭讪,在路上遇见陌生人,常常会双目注视微笑,打招呼友好示意。然而中国人面对陌生人时,则更多带着戒备心,表现为目不斜视匆匆而过,大多认为贸然搭讪有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冒犯与轻浮。[17]这种线下社交中的文化心理因素,可能也延伸至虚拟社交里。美国用户将真人照片作为头像向所有人展示,仿佛对每一个人都在无差别地打招呼;而中国用户面对陌生人,隐藏自己的真实面貌,划分出关系距离,避免和不熟悉的人有过多的接触和了解。恰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如同一圈圈的水纹,由中心到边缘逐渐变淡,以自己为中心,会对不同亲疏层级的他人,采取不同的交往模式。
面对虚拟空间中复杂差序化的人际关系,当中国用户无法去设置不同分组,只能使用统一头像去应对所有关系时,会更倾向于对自我形象进行遮盖和掩藏,表现出较低的自我真人头像披露意愿和更高的隐私保护意识,从而转向一种安全、委婉的自我呈现方式,可以以不变应万变,进行不同差序关系的调节和控制。使用图1的被访者(S13)表示:“微信上有很多不熟的人,但又想在社交媒体中表达自己可爱亲和的形象,因此选择了这只可爱的小鸟当头像。”无独有偶,另一被访者也表示:“选用这张照片(图2)做头像是因为图片很好看,具有普遍性的观赏美感。其次,旋转木马、迪士尼星黛露饮料杯都体现着少女心、可爱,希望通过这个头像展现自己少女心和可爱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别人也可能通过这个头像建立我的形象——可爱少女。”(S20)即使是使用自己的真实照片也会采取折中式的表达以划分出隐私与自我表达之间的安全领域,使用图3的被访者表示:“出国留学之后习惯使用自己照片做头像,但因为朋友列表有陌生人,不想露脸,所以选择了一张真人的背影照片作为头像。”

图1

图2

图3
(二)理想自我与他者凝视
在访谈过程中,很大一部分被访者称是外貌因素影响了真人头像的选择。“我觉得基本上用自己照片做头像的人都是长得比较好看的,我这种长得一般的,还是算了”。(S16)“我年纪这么大了,脸上都是皱纹,当头像不好看”。(S26)出于对自我容貌的负面审视,受访者选择规避将真人照片用作持续露出的社交平台的“门面”,而头像中的容貌展现也被默认成为在这个“颜值即正义”社会背景下,一种“看脸”才能拥有的“特权”。
在实际观察真人头像用户时,笔者也的确发现这些头像主人在呈现的照片中大多形象姣好,同时图像的性质也偏向美图照、艺术照、精修照等具有明显表演、展示性质的照片。例如图4,头像主人选择将自己置于美颜滤镜下,同时伴有一些卡通贴纸的遮挡,这让人物形象“看起来更可爱”的同时,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个体真实的肤色、五官、脸型等容貌特点。“比起一张更像我的照片,我可能会用一张更好看的”。(S7)相较于美国用户真实感强烈的大头照,这些中国用户表示更愿意在线上社交空间中表现出自己良好的一面,利用修饰后的美照构建出更加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展现给其他用户,而这也成为用户间默认的一种规则。“我觉得这很正常,基本上大家发的自我照片都会P吧,也没有人会特意指出来。而且微信里面有很多人其实很难见面,你用一张美颜过的,那些人或许也认为你现实里和照片差不多。”(S13)尽管这些线上的美图可能会带有修饰、虚假的成分,但依旧为某些用户在虚拟空间创造了自我的存在感和心理满足,并认为这种形象展示将有可能会提升自我在他人心中的形象。

图4
社交媒体头像虽然是用户按照自我意愿进行的自我形象构建,但同时也是一种在他人凝视下进行的形象管理。在精挑细选一张美照后,受访者依然“会不自觉地想象别人对这张照片的评价,别人会不会觉得其实并不好看,然后自己就觉得这张照片的缺点越来越多”。(S15)个体对自我形象的美化方向,表面呈现出理想自我的设计,但深层次也是在完成一种对假想“观众”眼光的迎合和调整。这种对于观众的假想不仅停留在容貌层面,还会延伸至对个人个性、品格评价方面的担忧。受访者会担心使用真人头像的自己“看上去有点自恋”“显得太张扬”“比较肤浅”等。从访谈结果来看,使用真人头像的用户会比使用非真人头像的用户不自觉地、更多地点开自己的头像,进行重复乃至放大地观看。这种强迫性的观看行为,正是一种用户不断自我审查,尝试趋向他人和社会环境眼光的妥协过程。
因此为了避免在真人头像下时刻需要面对的“凝视”,许多受访者表示不太会考虑将真人照作为头像的选择。即使是使用,一些用户也会更倾向于背影、侧面、低头等角度以及中远景构图的照片,以降低自我头像容貌展示的直接性。如图5所示,大海和建筑构成了头像的主要画面背景,人物在右侧边缘位置仅留下了一个令人遐想的侧身背影。

图5
总之,无论是“露美脸”“不露脸”或是“少露脸”皆可反映出中国用户对于社交媒体头像中“脸”的在意和谨慎。一方面,中国用户非常在意自己在社交平台中构建的自我形象,认为只有良好的形象才值得展示,甚至有可能会采取一些修饰来进行自我美化;另一方面,生性含蓄的中国用户对自我表达的尺度又十分克制和敏感,即使是个人照片,在他人和群体压力下,受访者非常在乎他人有可能的意见或批判的观点,害怕公开化的个人形象会招致别人的非议和揣测。这种社会取向下的自我也让这些中国用户更习惯于退而反求诸己,寻求一种内向化的表达,避免对外主动、直接的自我身体显露。
(三)精神内省与托物言志
部分用户在访谈中认为真人头像不足以完整、深度地呈现自我:“照片基本只能透露自己的长相,而且很多时候也只代表我在某个时间点的某一面。”(S12)从这些被访者角度而言,真人头像对于自我呈现的意义十分有限,所展示的只是在某个特定情境下,一个孤立、截断式的自我容貌。相反,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头像展示出自我的性格特征:“这是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的男主角(图6),性格比较犹豫懦弱,和我还挺像的。”(S4)或是某一时期的整体内涵和状态:“这张照片(图7)是我的猫干了坏事我抓住它的一瞬间,觉得挺有趣,同时也影射我那段时间被命运扼住咽喉的感觉。”一言以蔽之,这些受访者对自我的理解更趋于一种精神内涵式的整体动态感知。

图6

图7
截断式的自我容貌不仅不能体现自我感知的整体性,也无法透露出具有共通感知和意识的信息。单看真人照片无法推断这个人个性犹豫,但一个备受关注的动漫形象却可以;单看真人照片也无法猜测某人内心积郁,但一只被扼住喉咙的小猫却可以。
因此,当容貌无法体现出整体性的自我知觉和精神内涵时,中国用户巧妙地采用“借物抒情”,利用客体事物来进行个性与情感“托物言志”般的隐喻性表达。如图8所示,被访者选择了一幅色彩靓丽、热烈的花卉插图作为头像,“这些花的颜色让我想到夏日的石榴花,很有生命力,感觉自己都好像融在花里了”。(S14)被访者将自我对生命的感受和情感移置、灌注在客体对象中,使得客体对象“融”进了自我。可见在对头像中客体事物的审视过程中,被访者除了提及客体的形式、结构、色彩等可见因素外,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客体对象与主体我之间的感知联系,呈现出一种意向性的认知结果。

图8
所以,中国用户的头像即使只是一朵简单的花或是一只普通的小猫,但只要它们符合使用者主体的内涵表达,主体便会将自我的心境与人格寄于这些客体之上,在虚拟媒介中用头像作为“相似我”的呈现。而伴随着主体对自我感知的变化,用户也有可能调整头像图片以吻合心境,展现出一种具有弹性、可变的动态自我。如图9所示,被访者称自己在当时正处于迷茫无措的时期,色调灰暗的风景埋藏着自己的迷茫与焦虑;之后状态好转,她又将头像替换成图10,以鲜艳的花朵和明媚的蓝天暗示自己内心的平和与喜悦。

图9

图10
中国用户对于自我的意向性认知不仅仅是反映当下的自我,往往还会包含自我理想和灵性成长。他们对自我的认知也强调个人的道德修为,并视之为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如图11,被访者使用了一个中国人共通的文化符号——“青莲”,来传达自己的人生观:“自己比较喜欢青莲的意象,青莲素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意,如同李白称号为青莲居士……包含着自己不同流合污,造福社会的理想。此外,青莲也有青涩、不成熟、还在成长中的含义。”(S18)于她而言,青莲承载着自我预期的道德品质,是自我理想追求的化身。而将其用作日常可见的头像,正是完成一种内心深处的自我激励和自我表达。头像中的隐含意思,能够诠释出本人希望和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想法。被访者希望回避过多的交往,保持自我而非改变自己,从而实现自我和谐。此时,头像就是自己的理想化身和形象符号,代表本人对外传达。“图画中的枯藤和死水就像是生活,黑暗而狰狞,但也可以映射出莲花圣洁的倒影。就像是善恶交织,能和谐地融为一体,又好像没有什么情感,传达我平淡生活的感觉”。尽管有时这种含义和暗示并不能完全被外人所知,被访者却并不非常在意,“最重要是我明白,如果有人懂那当然更好”。对于这部分中国用户而言,头像暗含了一种积极而又内省的自我认知态度,相较于他人的理解,自我的内向传达更为重要。

图11
中国人的自我观念更加偏向于对自己精神内涵的整体感知,这种意向联系的认知方式可能与中国人更重视直觉思维有关,感性的直觉思维会更为强调物象与审美主体间心意的契合与否,而忽略其形式特征。[18]而西方的认知思维会更加唯实,偏向对事物存在的本质认知,认为“我”即是“我”,头像的呈现更偏向实体存在的“相等我”。如果说西方头像多用真人照片,如同强调写实性的油画,“以形写形”,表现的是真我在网络虚拟空间的再现。那中国用户的头像就像是一幅幅“重在传神”的中国水墨画,是自我精神内涵在网络空间的意向性表达,虽然头像中无我的实体,却隐而不露地倾诉着主体我的思想、情感与经验。另外,在有限的访谈样本中,尽管不爱使用真人头像的中国人,选择了丰富多元的客体事物作为头像,但使用的类型和对象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和趋同性。例如,年轻用户会更多使用卡通、萌宠、明星类头像,而中老年用户会更偏向风景、植物类头像。普遍而言,中国用户中头像元素的选择往往都落在大众喜好的舒适区,大众对其很难有强烈的厌恶感和不适意。头像的选择原本是个体主动进行的个性化自我建构,最终展现出的却是一些趋同的“面具”,一些编码规则和审美追求在人际间互相传染,变得更为流行,成为更多人的参照。[19]以研究者随机点开的60人微信群为例,用人与大海照片做头像的就有7人,且构图和角度具有非常高的相似度,如图12和图13,但这两位使用者并不相熟。

图12

图13
六、讨论与小结
社交媒体头像是用户在虚拟空间进行自我呈现和建构的重要手段,也是其他用户判断其身份、个性的直接线索。本文基于对中国人为什么少用真人头像这一现象,发现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与线下交往中的自我呈现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人们在虚拟空间的交往虽然摆脱了身体在场的情境,然而文化却以一种更为隐匿的方式深刻地形塑着人们的媒介使用行为。在我们的受访者中,虽然也存在个体差异,然而在共性的文化环境塑造下,被访者头像选择的心理因素和呈现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
社交平台头像的不同呈现策略承载了用户对自我的不同理解和期待。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西方人将自己看作与“他人”不同的存在,无论这个他人是朋友、陌生人,还是敌人,自我是独特的,他人是相似的。然而,东方人将自我看作互依的个体,在他们眼中,每个他人都是独特的,视自我与这个具体他人的关系而定,自我更像亲近的他人,而不像陌生的他人。因此,西方用户在头像选择上多使用独一无二的个体化形象,直截了当地将真实主体进行公开化展示,凸显出强烈的个人存在感;相反,中国用户的头像呈现却更倾向于一种主体隐匿的状态,借用客体事物完成自我形象的建构。借由头像这一自我呈现的重要窗口,中西方用户在虚拟空间中显露出对自我理解和表达的相异。在西方个体主义的价值系统中,自我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实体,以“真我”为核心,以追求一致性和统合性为最高原则。[20](P4)因此西方人更愿意用不加修饰的真人照片,真实、独立地展现自我,以个体的个性化容貌彰显自我与众不同的存在,反对因不同情景、不同人际关系而造成自我表达的不一致。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人的自我依赖于社交关系网络中,强调通过人己关系来进行自我定位以及行为模式的调整,自我的呈现会因不同关系与情境而发生弹性地改变;同时中国人也更倾向从外部角度出发观察并界定自我,在乎他人的意见和评判,这也容易让个体容貌的展示会因为自我与他者的“凝视”而受到影响,转向为一种内向化的安全表达;另外,精神自我也是中国人自我观中十分注重的一部分,不喜外露的中国人通过积极的自我内省,进行自我扩张,触发与他物的连接和感悟,让自我获得超脱实体本身的认知和思索,在相似性图片的表达下暗含着个体精神世界的独特性存在。
本文作为一个探索性的研究,打开了一些理论上的可能,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比如,一向讲求隐私保护的美国人却愿意在社交媒体头像上“大方”展示自己的“大头照”,而一向对隐私不怎么敏感的中国人却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大谈隐私保护。这种有趣的反转可能指向二者在“公”与“私”的理解上存在更深层次的差异。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为公,向外看是为私。一个中国人为了亲近的他人而损害公共利益,从亲者来看就是无私,但从陌生人来看却是自私。这种为了小圈的自私就被合理化了。从本文的研究发现来看,中国人的“隐私”受到了差序格局的影响。它跟欧美社会的公德与隐私两词中的“公”与“私”有着很本质的不同,西方人的公与私是一个实体性的定义,不随情境或交往对象不同而变化。当然,中美用户的这种使用整体性偏好,也可以从其它的视角加以解读,比如制度要素、使用功能等。当腾讯将之命名为“微信”时,信即信息、短信之意,就将传统书信往来的手写功能突出出来了。没有一个视角是完全独立的,制度、使用的选择也有文化的因素在其中。本文从文化视角切入,待将来的研究做更细致的思考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