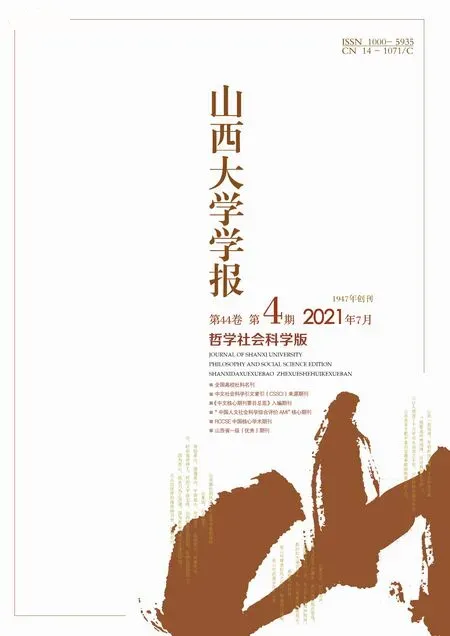战国中山遗址出土文献与子夏“诗教”
韩高年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史记·儒林列传》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1]3786子夏居西河教学,魏文侯尊礼之。借助于魏国军事上的扩张,尤其是在公元前406年攻灭中山并建立魏氏中山国的27年间,形成了儒学在华夏北方边缘地区的兴盛局面。子夏之学的核心是《诗》学,与孔门早期《诗》学的重视阐发《诗》之道德伦理与文化素养价值不同,为适应新的社会政治需求,子夏《诗》学更重视阐发《诗》的政治思想,颇具“诗教”的实践品格。其诗学格局渐趋阔大,且与礼法相配合,呈现出经世致用的面貌。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葬及灵寿中山都城遗址群中,发掘出带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及其他文字图像材料多件,其中尤以“平山三器”最为重要。这些出土文献为研究子夏对孔门“诗教”的实践,以及战国时代儒学“西进”“北上”提供了新材料。虽然这个问题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讨论,但对子夏学派对儒学的传授方式、子夏与魏文侯及中山国的关系,以及处于华夏边缘的中山国对华夏文化的认同等诸多细节,仍有未尽处,故笔者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好。
一、魏文侯经略中山与子夏之学的“西进”“北上”
鲜虞中山首见于文献记载的时间是公元前506年(《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296年为赵所灭,中间经历了为魏国统治的魏氏中山27年。学者认为中山国是白狄建立的国家,在战国时期具有相当的实力,号称大国,曾上演过“五国相王”的政治好剧。刘向编《战国策》专设有《中山策》,足见对中山国的重视。晚清王先谦撰《鲜虞中山国事表》一卷,并附《疆域图说》一卷,以彰其史。晚近又有吕苏生利用新出土的中山王墓器铭等新资料,补充王书,成《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补释》。据此,中山国之面目渐次清晰。
《列子·黄帝》篇载:“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杨伯峻《集释》曰:“中山,春秋时为鲜虞,战国时为中山国,在今河北保定地区一带。”[2]中山国为魏所灭事,载于典籍者如下。《吕氏春秋·自知》曰:“宋、中山不自知而灭。”高诱注曰:“中山乱男女之别,为魏所灭也。”[3]647《战国策·中山策》载:“魏文侯欲残中山,常庄谈谓赵桓子曰:‘魏并中山,必无赵矣。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复立也。’”[4]《水经注·滱水》:“(滱水)又东过唐县南。唐亦中山城也,为武公之国,周同姓。周之衰也,国有赤狄之难,齐桓霸诸侯,疆理邑土,遣管仲攘夷狄,筑城以固之。其后,桓公不恤国政,周王问太史余曰:‘今之诸侯,孰先亡乎?’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所以异禽兽也。今中山淫昏康乐,逞欲无度,其先亡矣。’后二年果灭。魏文侯以封太子击也。”[5]286-288杨宽《战国史》谓“中山在公元前406年被魏攻灭。”[6]322今人吕苏生亦认为“中山为魏文侯所灭,事在周威烈王二十年,即公元前406年。”[7]其说大体可信。
魏国灭中山后,虽然中间隔着赵国,但仍派遣太子击居中山国而治之。其治中山,主要是变易其风俗,改革其制度。《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翟璜进言曰:“得中山,忧欲治之,臣荐李克而中山治。”[8]《吕氏春秋·先识》载:“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3]397中山被灭的表面原因是其恶俗引起魏国的不满,但实际则是魏文侯时代魏国强大以后向外扩张的必然结果。文侯听从翟璜之言,以儒术变其“乱男女之别”的中山之俗,却是事实。太子击与李克皆为深受子夏之学影响之人,由治中山始,子夏之学遂传至中山。
子夏,名卜商,春秋时晋国温邑人(温邑在子夏出生时属晋,三家分晋后属魏),一说卫人。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夏生于公元前507年,少孔子44岁,卒年不详。可见他是孔子后期的弟子。《荀子·大略》载“子夏贫,衣若悬鹑”[9],可知他家境贫寒,出自社会底层。《后汉书·徐防传》注引《史记》:“孔子没,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1)(宋)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501.今本《史记》无“教弟子三百人”句。子夏为魏文侯师,《礼记》《史记》之《礼书》《乐书》《魏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多有记载。宋人洪迈《容斋续笔》疑之曰:“按《史记》,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矣。魏始为侯,去孔子卒则七十五年。文侯为大夫二十二年而为侯,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岁计之,则子夏已百三岁矣,方为诸侯师,岂其然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驳之,以为魏文侯为魏桓子之子,而洪氏误以魏文侯为魏桓子之孙。《史记》对此记载亦有误。魏文侯初即位,实在周定王二十三年,距孔子逝世30年。是时子夏63岁。魏文侯二十二年始为列侯,子夏84岁。西河其地战国时原属秦,在魏文侯时始为魏国所有。杨宽《战国史》指出:“魏国自从魏文侯进行了改革,国势就强盛起来。从公元前413年起,不断向秦进攻。这年魏军大败秦军,一直打到郑(今陕西华县)。次年,魏又派太子击包围秦的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并占有其地。到公元前409年,魏将吴起经过两年时间陆续攻取了秦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阴(今大荔西南)、郃阳(今陕西合阳东南)等城,并一直攻到了秦的郑(《水经注·河水注》),从此秦的河西地区全部为魏占有。秦于是退守洛水(在今陕西西北部),沿洛水修建防御工事,并筑重泉城(今陕西蒲城东南)加以防守。从此魏在河西设郡,以吴起为郡守。”[6]314由此看,《史记》所述子夏长期“居西河教授”,当始于“孔子没”(公元前479年)后,其影响在魏有秦河西之地后达到高峰。今人高培华考证指出:“孔子逝世之年子夏29岁。他在孔子生前,主要是求学和出仕历练,当时其志在当官为政;向同学解疑释惑不过是偶尔为孔子助教,并没有招收自己的弟子。当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期满,子夏已经32岁;经过如前所述比较短的过渡时期(充其量也不过一年左右的光景),则子夏返乡设教授徒,估计是在33—34岁之间,即是说肯定在35岁之前。从此时开始,直到87岁或者是百余岁逝世,子夏西河教授的时间,至少有半个多世纪,甚至长达六七十年。”[10]这一时期,在子夏之学影响下出现一批政治家、学者和社会改革家。见于文献记载的有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李克、吴起、禽滑厘等。他们虽非皆如《史记》等所载师从子夏,但应均为受其思想影响较深者。
正因为有“河西”之地为战略基点,魏国才能占领了中山国。而魏文侯之子击与李克执中山国之政的时间虽不长,但其成效却比较突出。其治国的主导思想为轻赋敛、恤黎庶、举贤才、厚风俗。即是受到子贡思想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魏国衰落、中山国复国之后。
二、中山王《方壶铭》《鼎铭》所见中山国的“诗教”

关于李克重法治的细节和在当时的中山国产生的政治影响,首先可以从其中的中山王诏书铭刻窥其大概。诏书曰:
这份刻在铜版上的诏书,其大意是:中山王命令阴,在修建葬域中,要按规定的长宽大小标准去做,如果发生问题要依法处置,违法者死罪不赦,不执行王命者罪连子孙。该铜板一件从葬,一件藏在王府。由此可见中山国诏令的保存情况。这种重视法治的现象应该是李克主政后才有的,而且一直到中山国复国后仍然在实行。

隹十四年,中山王错命相邦賙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剂,可法可尚,以饗上帝,以祀先王。穆穆济济严敬,不敢怠荒。因载所美,邵矢皇功,诋燕之讹,以警嗣王。隹朕皇祖文、武,走亘祖成考,是有纯德遗训,以施及子孙,用为朕所放。慈孝宽惠,举贤使能。天不负其有愿,使得贤士良佐賙,以辅相厥身。余知其忠信旃,而专任之邦。是以遊间饮食,宁有怵惕。賙竭志尽忠,以左右厥辟,不贰其心。受任佐邦,夙夜匪懈。进贤惜能,亡有衅息,以明辟光。适遭燕君子哙,不顾大谊,不谋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勤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旃,寡人非之。賙曰:“为人臣而反臣其宗,不祥莫大焉。将与吾君并立于世,齿长于会同,则臣不忍见旃。賙愿从士大夫,以詗燕疆。是以身蒙幸冕,以诛不顺。燕故君子哙,新君子之,不用礼谊,不顾逆顺,故邦亡身死,曾亡逸夫之救。遂定君臣之位,上下之体。休有成功,创闢封疆。天子不忘有勋,使其老奖赏中父,诸侯盧贺。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即得民。故辝礼敬则贤人至,陟爱深则贤人亲,作敛中则庶民附。”乌虖!允哉若言明则之于壶而时观焉。祇祇翼翼,昭告后嗣。隹逆生祸,隹顺生福。载之简牍,以戒嗣王。隹德附民,隹宜可长。子之子,孙之孙,其永保用亡疆。[16]574-575
有的学者认为,夔龙纹方壶是中山王替命相邦賙所作[17],其实并非如此。仔细分析两篇铭文的中心意思,从表面上看是颂扬相邦賙的贤明和功绩,实际上是以燕王哙让位于子之,最终招致国破身亡之事为教训,告诫嗣子警惕相邦,避免在中山国发生类似燕国的政治闹剧。铭文中表面上肯定賙反对子之反臣为主,实际上表现出中山王对賙也是不放心的。
司马賙是中山国的重臣,他在中山王年幼即位时就辅佐王。中山王和嗣子都以燕国惨痛的教训为警戒,这表现在铭文中,就是反复提到子之使国君臣服于大臣是大逆不道之事!这充分反映出他们对位高权重的相邦司马賙其实也是心存疑虑,担心燕国禅让的事件在中山国重演。
於虖攸哉!天其又刑,于在厥邦氏以寡人倞赁之邦,而去之遊。亡懅惕之虑。昔者,吾先祖桓王、昭考成王,身勤社稷,行四方以忧劳邦家。含(今)吾老賙亲率参军之众,以征不宜(义)之邦,奋桴振铎,闢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寡人庸其德,嘉其力,氏(是)以赐之厥命:“虽有死罪及三世,亡不若(赦),以明其德、庸其工(功)。”吾老賙奔走不听命。寡(人)惧其忽然不可得,惮惮業業,恐陨社稷之光,氏以寡许之谋虑是从,克有工(功),智也。诒(辞)死罪之又(有)若(赦),智为人臣之宜(义)施(也)。於虖,念之哉!后人其庸庸之,母[毋]忘尔邦。昔者吴人并越,越人修教备信,五年覆吴,克并之至于含(今)。尔母[毋]大而肆,母[毋]富而骄,母[毋]众而嚚,邻邦难亲,仇人在旁。於虖,念之哉!子子孙孙,永定俘(保)之,母[毋]竝(替)厥邦。(3)释文据: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67-573.个别字句根据笔者的理解有校改。
据《战国策·中山策》记载,中山称王、其相蓝诸君用张登说齐一事。这件事发生在周显王四十六年,即公元前323年(见《六国纪年》),正当器铭中所见的中山王譬在位之时。学者们据此认为《中山策》中的蓝诸君就是器铭中提到的司马賙。《史记·太史公自序》回归祖上史时说:“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徐广曰:“名喜也。”[1]3990-3991《吕氏春秋·应言》中提到司马喜为中山相国和“王兴兵而攻燕”。《战国策·中山策》中有司马喜“三相中山”和新王选定王后之事,时在赵武灵王未攻中山之前,应在嗣子资之时。因此,笔者认为司马喜也就是司马賙[17]之说极是。
关于这组器的主人是谁,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从种种证据来看,这些器物应当是嗣位的中山国君祭祀其父及祖先的。朱德熙、裘锡圭二位先生认为:
本文讨论的四件铜器都出于一号墓。有的同志认为方壶、大鼎和圆壶是中山王赠给相邦賙的,由此推断一号墓是相邦賙的墓。我们认为尽管这三件铜器的铭文里都着重宣扬了相邦賙的功德,但这些器物都不是为他作的。方壶铭一开头就说“以享上帝,以祀先王”,显然是王室的祭器。下面说“诋郾(燕)之讹,以儆嗣王”,又说“祗祗翼翼,昭告后嗣,唯逆生祸,唯顺生福。载之简策,以戒嗣王”,都是告诫嗣王和子孙的话。鼎铭说“子子孙孙永定保之,毋竝(妨)厥邦”,圆壶铭说“敬命新地,雨(永)祠先王,世世毋犯,以追庸先王之功烈。子子孙孙,毋有不敬,寅祗承祀”,口气也是一样的。总之,我们从铭文里找不出什么事实可以证明这三件铜器是中山王赐给他的臣属的。
其实无论从墓葬的规模、出土的器物以及铜器铭文的内容来看,一号墓之为王陵本来是很明显的。[19]
这个观点是可信的。鼎和壶都是随葬的中山王室祭器。铭文节录了中山王生前册封立有大功的相邦賙的册命文书和告诫嗣王的简册的片段。正因为死去的中山王担心的事并未发生,因此这也成为其子祭祀他时津津乐道的功业。
被魏国占领的中山国在李克的治理下,采取了新的治国思想,既接受了周礼,又吸纳了儒家的思想,这从上引各器铭所反映的祭祖追孝思想等方面即可以看得出来。“禅让”本是儒家贤人政治观念的制度化表述。燕王哙在子之的劝说下因禅让而丢了国家,引起了内乱。这在当时是影响颇大的政治事件。上引铭文中中山王之所以担心相邦賙会效仿子之,也是因为中山在复国后,儒家思想的影响仍在的缘故。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子夏居西河后对传播儒学的巨大作用。
三、中山诸器铭与子夏《诗》学的传播
孔子称赞子夏长于《诗》学,已见于《论语》等典籍记载。子夏居西河,也借助传《诗》而弘道。《诗经》的传播也影响到该地的社会生活,尤其是语言使用与有关风俗。这从现存中山诸器铭文中可以找到明显的证据。中山国诸礼器铭文是战国时代少见的长篇铭文,与同时代其他地区的铭文有较大的差别。内容上既具有当时流行的“物勒工名”,同时也继承了春秋时期器铭的礼仪写作内涵;形式上则具有十分突出的整齐的四言化、韵文化特点。铭文的作者,有的学者认为就是作器者“左史车”,也有的学者认为不是他。不论是谁,作者显然是特别熟悉《诗经》或受其语言风格影响很深的人,因此铭文中化用或引用《诗经》成词和成句的现象很突出。这方面李学勤、夏传才、廖群及马银琴等学者已经注意到(4)李学勤,李 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J].考古学报,1979(2):147-169;李学勤.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J].文物,1979(1):37-41;夏传才.《诗经》出土文献与古籍整理[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1):66-75;廖群.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马银琴指出中山三器铭文共用《诗》8处,分别出自《诗经》之《商颂》《鲁颂》和《大雅》。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19.,并且有较为详细的比勘和精彩的论述。笔者不想就此再做补充,而是想由此出发谈谈《诗经》作为一种经典在战国时期的传播方式,以及其如何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影响的问题。
中山国的族属,共有三说:一以为周人同姓,二以为白狄,三以为殷商子姓。周人同姓说已为学者所证为非,白狄子姓说也无明确证据。其实白狄自春秋以来即与华夏杂处,时战时和,其族与华夏长期融合,故其族属有多种说法。蒙文通指出:“戎羌世接诸夏,与文教相习,故往往入居封内,杂于臣仆。狄之文化低而武力强,与诸夏习俗远,故初尚驰突为祸,历久而后服属也。白狄亦姬姓,又曰已姓,子姓。”[20]81又说:“白狄为犬戎之族,与赤狄殊种,故文野不同也。……《续汉志》以鲜虞为子姓,韦昭注《国语》以为姬姓,或又以为已姓,群书言各不同,则以音近而译互殊。若夫说中山姬姓,即以为周之别子,是未知狄之姬,固无与于周之姬耳。”[20]83近年在同一地区考古发现有殷商文化遗存,至少说明春秋以前鲜虞与殷商民族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中山族属不当以种姓论,而当与文化认同论。因其在商、周时,有文化上主动认同之举,故典籍中方有子姓、姬姓之不同说法。
战国时的中山国显然承续了鲜虞的游牧生活方式和以军事立国的根本制度,所以仍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然而,从中山王墓以及其中出土的遗物和青铜器铭文来看,中山王室完全接受了周人的丧葬之礼,且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运用于治理国家。这个个案一方面说明战国时代中原地区主流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之广;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个战国时期不同空间的族群之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型个案。中山国被魏所灭是因为其原有的文化与中原文化不同,而其接受中原文化后不久,则被提倡“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灭。历史似乎与中山国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在这一历史的表象之下,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在这个背景下,也可以看出,子夏之儒学在传播方式上已经完全超越了早期儒家师徒“授受”的传统方式,在李克、吴起等人身上变为注重现实政治效果的实用方式。2019年公布的安大简《诗经》钞本,共包括《周南》《召南》《秦》《侯》《鄘》《魏》六国国风和介于《秦》和《侯》之间的“某风”七个部分。与毛诗相比,此本《侯》对《魏风》的重编,以及《魏》对《唐风》的替代,有明显的意图。联系战国初年魏文侯的任贤使能和励精图治,学者们认为此本或是子夏为适应魏国的“制礼作乐”而编,其目的是通过《诗》以强化魏国的文化影响力。[21-22]以中山王墓铜器铭文对《诗经》的接受来看,其方式既不是“赋诗言志”“引诗足志”式的借用,也不似汉儒式地注重经义和章句训诂,而是直接拿来,为我所用。这种情形与孟子、子思一派的作风形成显明的对照,倒是和之后的荀子一系儒者的儒法并用有许多相似之处。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毛诗》者,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受赵人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23]由上述中山王墓器铭来引《诗》用《诗》来看《诗》之传授,即可知其何以独盛于燕赵。
其次,中山国对子夏儒学的接受,表面上是因被当时强大的魏国通过军事占领强行推动,实质上也是中山国为获得发展机遇和资源以及对抗在武力上日渐强大的邻国赵国而主动接受的过程。王明珂指出:“华夏边缘的扩张、漂移包括两个同时并进的过程:一是华夏重新定义谁是异族,一是原来的非华夏假借华夏祖源而成为华夏。”[24]上文所引《国语》等传世文献关于中山国族属的记载歧异,并不仅仅关乎狄姓还是姬姓,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观察角度导致的不同判断:即从祖先讲中山属于狄族,而从文化——尤其是魏氏中山时期的文化看,则无疑是华夏。中山王墓诸器铭,以及造型独特精巧的诸多器物,恰恰体现了王明珂所说的“两个同时并进的过程”。
综上,子夏之学因李克为相于中山而西进北上,客观上产生了移风易俗的效果。儒家思想在中山国深入人心,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举贤任能,重视礼乐;而且还体现重视法治,讲求实效上。钱穆指出:
魏文礼贤,其可考见者,略如上述。其间有二端,深足以见世局之变者,一为礼之变,一为法之兴。何言乎礼之变?当孔子时,力倡正名复礼之说,为鲁司寇,主墮三都,陈成子弑君,沐浴而请讨之。今魏文以大夫僭国,子夏既亲受业于孔子,田子方、段干木亦孔门再传弟子,曾不能有所矫挽,徒以踰垣不礼,受贵族之尊养,遂开君卿养士之风。人君以尊贤下士为贵,贫士以立节不屈为高。自古贵族间互相维系之礼,一变而为贵族平民相对抗之礼,此世变之一端也。何言乎法之兴?子产铸刑书,叔向讥之。晋铸刑鼎,孔子非之。然郑诛邓析而用其《竹刑》,刑法之用既益亟。至魏文时,而李克著《法经》,吴起偾表徙车辕以立信,皆以儒家而尚法。盖礼坏则法立,亦世变之一端也。[25]
“礼之变”与“法之兴”,在中山王墓所出器铭中皆有明确之体现。可以说,这种变化,是子夏之学西进北上的结果。
四、从平山诸器铭看“西河”所在之论争
秦汉典籍记载子夏在孔子去世后居“西河”教授儒家经典,但就“西河”之所在,古今学者有分歧,争议很大。围绕这一问题,在今山西陕西一带又形成许多传说。这些传说与文献记载纠缠在一起,形成许多解决这一问题的难点。
前文已经指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认为“西河”即战国魏国之“西河”。案,“西河”地处龙门汾阳一带,即今山西、陕西交界一线。晚近学者则认为“西河”为战国卫国之“西河”,在今河南境内。近些年,因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原因,这个问题又引发了争论和关注。笔者认为,要解决问题,一方面应该梳理文献记载;另一方面还要从子夏之学的实际发生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华夏文化中心和边缘扩张与漂移效应为参照。战国中山墓诸器铭提供的信息,以及由此发现的子夏之儒学与中山国对儒学为核心的华夏的文化认同所形成的互动关系,恰恰提供了这方面的实证。
最早关于子夏居“西河”的记载是《礼记·檀弓》,其中说:“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郑玄注曰:“西河,龙门至华阴之地。”孔颖达正义曰:“此一节论子夏恩隆于子之事。案《仲尼弟子列传》云,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哀其丧其子而哭,丧失其明。曾子是子夏之友,故云‘朋友丧明则哭之’。子夏丧子之时,曾子已吊,今为丧明更吊,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女于夫子’者,既不称其师,自为谈说,辨慧聪睿,绝异于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与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姓卜名商,西河之民,无容不识,而言是鲁国孔丘,不近人情,皇氏非也。”[26]
司马贞《史记索隐》亦曰:“河东故号龙门河为西河,汉因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处。”[1]2677又《史记·孔子世家》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下司马贞《索隐》曰:“此西河在卫地,非魏之西河也。”[1]2330-2331司马迁、郑玄之时代去战国未远,其记载当可信据;孔颖达《礼记正义》也无异议;而司马贞《史记索隐》对《史记》中两处“西河”的所在,也区分得甚为清晰,并无混淆。
《水经·河水注》载:“细水东流,注于崌谷。侧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两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结牖,连扃接闼,所谓石室相距也。东厢石上,犹传杵臼之迹,庭中亦有旧宇处,尚仿佛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丰周瓢饮,似是栖游隐学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即此也,而无以辨之。”又云:“河水又南迳子夏石室东,南北有二石室,临侧河崖,即子夏庙堂也。河水又南迳汾阴县西,又南迳郃阳城东。”[5]104-105胡渭《禹贡锥指》据此谓:子夏石室在今郃阳县界。[27]郃阳县北为韩城县(今韩城市),《寰宇记》谓子夏石室在韩城者,即《水经注》所言崌谷之石室也。
引发争论的焦点是子夏之籍贯。司马迁谓子夏魏人,或以为卫人。(5)其实子夏所出生之“温”,此前属卫,战国时属魏。参:缪文远.战国制度通考[M].成都:巴蜀书社,1998:194.《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卜商,卫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习于《诗》,能通其义,以文学著名。为人性不弘,好论精微,时人无以尚之。尝返卫,见读史志者云:‘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读史志者问诸晋史,果曰‘己亥’。于是卫以子夏为圣。”[2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据此言:“子夏温人也,其退老,何不于故乡文物之邦,而远至郃阳韩城,荒陬水澨,又复筑石室而居,此其退老之所堪?……子夏居河西教授,决不在龙门华阴之间,而实在东土。当在今长垣之北,观城之南,曹州以西,一带之河滨。”[29]按《孔子家语》记卜商此条史料又见于他书而有所不同。《吕氏春秋·察传》:“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3]619两者比较,明显可以看出《家语》该节文字乃是节取《吕氏春秋》而来;其次,由此处“子夏之晋,过卫”等语看,子夏当时经常渡河往来于卫和魏之外各地,足迹远至晋地。钱氏“决不在龙门华阴之间,而实在东土”之说尚有可商之处。其实,子夏“居河西教授”本与其是否魏人无直接关系。
其次,子夏之学影响魏国及“西河”甚为深远,而对卫地的影响甚微,由此逆推,子夏所居“西河”为何处,显而易见。典籍载李克、吴起等师事子夏,中山王墓出土诸器已然证实李克传子夏之学为事实,蒙文通据《左传》考证白狄中山之地曰:“宣之八年,晋及白狄伐秦,成之九年,秦人白狄伐晋,则于时白狄必处于秦晋之间,于势乃可,成十二年,晋人败白狄于交刚,交刚在晋西,为陕西之肤施,斯亦白狄在晋西之验。成十三年吕相之绝秦也,曰:‘白狄与君同州’,此尤为是时白狄犹在雍州之明证。……此由春秋之末,以入于战国之初,晋人之日以削中山为志者也。”[20]84由此来看,随着李克主政中山,子夏之学也已经秦、晋传播到更北的今河北平山一带。
子夏之学远播至“西河”,吴起亦与有功焉。据《战国策·中山策》等记载,吴起皆曾以仁德晓谕魏文侯及其子,为魏国上层所接受。并使吴起治理魏国之“西河”,子夏之学亦曾由吴起而传播于“西河”。而考之于史籍,卫国可以说是孔子和儒门之“伤心地”!且不说孔子多次求仕无果,子路死于卫国内乱,即以上引《孔子家语》之“卜商卫人……时人无以尚之”一语,亦可知子夏在卫之处境。依孔颖达疏,《礼记·檀弓》中曾子责子夏“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的原因,是因为子夏传经时,“不称其师,自为谈说,辨慧聪睿,绝异于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与夫子相似。”[26]意思无非是说子夏在“西河”声誉虽隆,但李克、吴起等人虽尊孔圣而术杂法家,皆非淳儒。“自为谈说”,实则体现了子夏之学重视适应当时社会与政治实际的特点。今天看来,这与其说是对子夏的批评,还不如说是对子夏超越老师孔子学说的“变相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