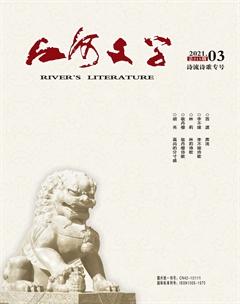呆呆诗歌
呆呆
极地:今夜无雪
我希望。
明天能在故乡桑林边的矮屋中醒来
天真冷啊。日头冒着白气
屋子在冻土上跺脚
一条河紧紧跟着桑林舌头被打了结
三只喜鹊在不知名的树上,光秃秃地叫着
屋檐下挂满鱼干
门板上,两尊门神正在拌嘴
妈妈坐在廊沿,往我的小袄里填丝绵。
风把屋子吹到树梢又吹落泥地。我希望
明天能遇见一个裤管边沾了苍耳的少年
他潮湿,空洞。
行走在这不属于他的人世
新雪
在一幅画前找到它。好像它需要重新被命名
画家留在他的时空里
而那条河。
正在朝窗外另一条河蜿蜒而去
我俯视画里的树木
满含忧愁的小路
一束光。正在推开画框毫无意外地射入
静谧的意义在于它不可移动
也不必移动。
新雪在光线中静静站立
它打开翅膀又将翅膀焚毁。
它投身一条河,又从一个人肺腑将自己掏出
它吹亂春天的长发。黄昏悬垂在树冠,被
妈妈走过的每条路
在风中飘摇:新雪让人如此期待
我们谈论过无数名词之后,忽然又想起了它
它以天人之姿闯入生活
它俯视,散落,升腾。最后无迹可寻:像一
个浴女,在黑暗中褪下了外袍
美物
清晨是一面镜湖。
布谷每叫一声,就浮起一间房子
我家的房子。
是第十二声布谷之后,出现在水面的
接下来,是小英家,阿凤家
老地主家
卢斌家是最后一间。他家的院子里有一株
大月季
用草木灰养着
我担心它被布谷掳去做了伴娘,一路急跑
瞧见月季花后面坐着干干净净的男孩
正在低头翻书
我呀我呀盯着自己黑呼呼的脚丫
——村子又不见了。细雨呀打湿了布谷的
婚礼。布谷的婚礼
春天的地铁
这不是一九四二年的巴黎
这是巴黎。
蒙面的小提琴手在演奏他今天最后一支曲子
音乐是过去式,音符来自未来
寂静中地铁来回穿梭
彷若无人之境:一九四二年左手是爱情,
右手是战争
一九四二年活着就是一切
呼吸会带来星空
星空独自编织着花环。一个人远眺故乡,
看见的是大海,落日和积雨云
春天是陌路的总和
哲学家堕入因果的密室
诗人在词语中没顶。春天蒙住了人类的双眼:
“到底是谁,取走了餐桌上的善和信仰?”
这不是巴黎。
我们乘坐着地铁在黑暗中狂奔
看看月亮吧,作为一只钟摆它停在了那里
哲学问题
月亮是一个真相。
但它不可能绕过自己去往另一个宇宙
坐在雨中辩雨的僧侣
成为雨的同时,又成了一棵神经质的槭树
早晨它穿上清风的朝服
到了晚上。
兰若寺的钟声,一会儿送来小倩,一会儿
又送来秋容
山下县衙养了白鹅
养了用尖指头拨琵琶弦的歌姬。假设祖母
手里的煤油灯
是深睡。母亲抓紧灯绳,她头顶的白炽
灯,是鸟笼。那么现在
电流嘶嘶轻响。它攥住月亮,假设月亮是
反对的
那么现在。唯有这松弛,绕过自己。去取
来幻觉中的芍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