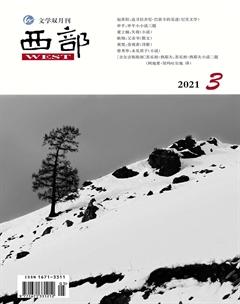遗书
李剑
这个想法是宋在早餐桌上提出来的。
这一两个月他一直沉郁。沉郁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源于跳跳的梦境。
那晚,跳跳梦醒,紧紧搂着我的脖子呜咽:“爸爸不见了。”接着又说:“妈妈,着火了。”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我说:“跳跳做梦了是不是?爸爸不是不见了,爸爸是去找水救火了。所以,爸爸一会儿就会回来,不用害怕。”
早晨起床,我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百度搜索周公解梦。百度上形形色色出现很多条内容,但我拣最愿意相信的那条说给宋听:“是好梦呢,是说咱们家要发财。”
光阴一天天斜掠过屋檐,我们没有看到发财的兆头,却也一切平顺,安安静静地过着日子。
但宋的内心并不安静。
他说,在跳跳那个梦之后,有一晚他也做了噩梦。梦境可怕到他不愿回想,更不愿跟我们提及,仿佛说了,梦就会顺着喉管爬出来,变成现实。
想法就是在那场噩梦之后产生的。他一直琢磨该怎么开口。
这天,他终于把它晾在了餐桌上:“我俩都写一封遗书吧……”
如他所料,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立马打断了他。我一拍桌子,话和眼泪一齐涌上来:“说什么呢?什么遗书?你没事瞎想什么呢!”
他噤声,看着我,等着我的情绪缓和下来。
一时间,餐桌上静默无声,连跳跳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吃饭。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了。”他再次捡起话头,试探地说,“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它并不在乎下一刻给你来一场风暴,给你创造一次生离死别。你的呼唤祈祷感动不了它,你的眼泪在它看来与一滴泥污并无不同。可正是如此,我才更加珍惜生,珍惜眼见的每一个太阳,每一场星光。我才如此惧怕死,惧怕失去,惧怕孤寂地活。
那么遗书呢?遗书似乎是一个象征。它预示着死亡就在前面。然而事实上,死亡从未挪过位置。它满不在乎地站在前方的某个路口,斜觑着眼睛,等着我们自动前往。
“其实没什么。网上也有很多人写过这个。”宋继续说,他宽慰我。
既然无可避及,他便选择直面,为未来争取多一点的从容,少一些的遗憾。
这让我想起她。她是我喜欢的一位老师。在一次出行那拉提的活动中,我们住一起。那天,活动间歇,我们在房间休息。我不记得这个有关“死亡”的话题是如何引发的。我脑海中至今非常生动的画面是她坐在床的一角,低着头,安静的收拾衣物。她说:“我常常这样整理东西,把东西清理归纳好,以备万一。”这个万一是“死”。她要在“万一”之后,给生者一个清朗明确的死后清单。
我当时内心很震动,甚至不理解在我们如此康健有力的时刻,为什么要让“死”大摇大摆地介入我们的生活。我看着她。她眉眼含笑,连眼角的纹路都安静温和。说到死亡,她仿佛只是在说,“我们把这个鸡蛋装进包里,路上饿了吃吧”一样,面上无波无澜。
我说“好”,我把鸡蛋装进了包里。可我没能把她说到死亡的那份淡然一同装进去。只是后来的岁月让我更加了解了命运之诡谲,生命之无测。我不能够同她一般淡然,但已然能够理解她时常纳死亡入怀的举动。
死亡就在身边,或远或近,时时发生。
而那个死去了多年的人,这些年却也在我心里越加鲜活。
当年,在我还是个少年时,不能说起他的死亡,一说便会哭。在他葬礼上没有流的眼泪,在那些年与人说起“父亲”这个字眼时,都补上了。可是我知道,那些眼泪并不是为他的离去而流。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生命的可怜和尊贵。我的眼泪所以滔滔不绝,汹涌而下,为的是自己年少逝父的命运,为的是心里的那份卑怯和自尊。
现在,我可以很平和地說起他。说起他的壮年早逝,说起他的无畏和怯弱,我不再哭,可是我却越加思念他。我理解了他死前对生的深深留恋,理解了他说“等我走了,你们很快就会忘记我”的那份试探和怀疑。我现在想起他,不再为自己悲苦,心里全是对他的疼惜——他裹着厚厚的大衣坐在门槛上,在死亡已经在他身体上攻城略地几近胜利的时刻,他眯着眼睛在初春的阳光里说:“我不能死,我还没好好享受天伦之乐呢。”与其说他在与命运进行最后的抗争,不如说他在向死亡做无谓的哀求。他贪恋美酒,贪恋与妻儿共处的日子,贪恋人世间的一切悲喜,贪恋最后那一口气。而彼时,我冷静地旁观着他的贪恋,不作声,只静静等待那个该来的日子。
我们都知道,它就要来临。
我现在为我当时的冷静感到内疚。而更为让我内疚和遗憾的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日子即将来临,却并没有终日守在他身边。
他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时刻里死去。这个时刻是几点?没有人知道。我们只是发现了他的死亡。他闭着眼睛,大张着嘴,或许是在对这个世界做最后一次呐喊。只是,他喊了什么?无从知晓。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言语,只在房间的四壁上空落下回音。他的人生的最后一眼,大约也只望见了比死亡更浓厚的悲凉。
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关父亲的许多画面都在时间的侵蚀下漫漶不清。可是,他死亡时的样子却在我心里被装裱成了一幅永不掉色的油画。这幅油画指向的意义是,父亲,父爱,生命,和人之死亡,人之尊严,以及对生的体恤。
对了,如果时间能回溯,我真希望能回到他临近死亡的那些日子,攥着他的手,陪他走过最后一程。如果这个做不到,也至少给予他建议,不如,写一封遗书吧。这封遗书不是为你而写,是为要揣着对你的思念继续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而写,是为减少他们内心的遗憾和内疚而写,是为他们能在任何一个需要的日子,凭借这些真切的字迹获得安慰而写。
我说:“好,我们写。”
宋的肩膀松下来。他缓缓道:“那我们写好后,把它们装进一个箱子,谁也不许看。如果没有意外,等到我们结婚二十五周年时,再一起打开箱子,一起看。然后,每人再另写一封遗书装进箱子里,怎么样?”
我说好。
箱子很快被宋买回来了,是一只褐色的四角有精美裱花的木匣子。他把它放在阳台上敞口晾着,只等着遗书写好,合盖,上锁,封箱。
到时,箱子会被高高地放在日常不及之处。剩下的,是时间如水过去。是很多很多年后,我们忘记了它的存在。待有一天,我闲来无事,挥着拂尘,四处划拉。然后,我突然看到它。我拂去它身上厚厚的积尘,拿给宋看,这是什么呢?
我们怀着好奇,搬张椅子坐在阳台上,琢磨着怎么打开它。当我们因为找不到钥匙而把匣子上的锁头用锤子砸掉,盒子“咣当”一声打开后,我们忍不住捶着彼此的肩头笑:原来,是我们当年写给对方的遗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