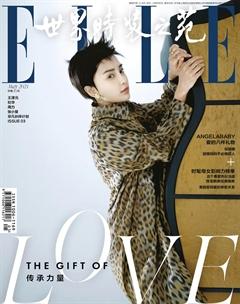周力:等生命的果子自己成熟起来

二十多年前,在法国东部临近瑞士边界的一座小山顶上,周力度过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下午。她在山顶的教堂里,静静地看着光从彩色玻璃窗中透进来,漫过墙壁,随着时间,有时如暗夜萤火,有时如纱幔拂面,光影与时间形成了最美妙的音乐,互相追逐,无比亲密。这是朗香教堂(La Chapelle de Ronchamp),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在这里创造的一个时间与光影的神秘空间。
时间和光影,是世间最难捕捉,也最难表现的事物,无形无状,不可描述,却又构成了所有人生命的本质,这让周力着迷。
2020年,周力创作了一批新作,以绿色为主色调,命名为《春》。在画面上,她用色彩和线条创造了一个深邃的空间,里面有时间,有光影,有2020年的沉思。她的这次展览,叫做《格林迷踪》。
对这个世界的运转,周力有自己的理解。这份理解形成了她的艺术,也描绘了她独一无二的人生轨迹。
1_
为什么要做艺术家?
“有些东西不是自己能选择的。”周力说是画笔选择了她。周力的父亲周石民是一位艺术家,对周力影响深远——从对艺术的态度,到对人生的选择。一开始,周力的父亲并未引导她走上艺术的道路,可她就是对父亲的画笔感兴趣,对哥哥练习书法剩下的小纸头感兴趣,拿着画呀画。
或许是因为父亲知道艺术的道路艰辛孤独,获取任何成就都需先经历无尽的付出,所以一开始,他不想女儿经历这条道路上的风霜,可周力有她的叛逆和坚韧,也有真正的天赋和因此而生的心气。父亲要求周力多多速写,她就常去码头和菜市场观察人,积累了极好的速写能力,在线条中获得了最初的快乐。
周力选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她画的是抽象绘画,用以表达的是线条,是色彩。市场流行的是更容易理解的具象绘画,是色彩鲜艳歡快的风景,但她只选择真正吸引她的课题。就像在登山时,固然有现成的亭子可供歇脚,但最美的风景总在险峻处。评论家皮力高度评价周力的抽象绘画:“周力的绘画把我们导向了一个长期被精英和理性的抽象绘画遮蔽的,感性与经验的荒原。因为荒芜,所以悸动人心。”
周力的绘画语言不同于欧美的抽象绘画:不似蒙德里安式的精心规划,也不似康定斯基、波洛克那样的运动轨迹;周力找寻到的独一无二的绘画语言,竟与她自小学习的书法和国画有着密切联系。她的绘画空透轻盈,更接近于中国绘画中的“虚”。她说:“我觉得线条是比较适合我的表达方式。这也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厉害的就是线条,它是书法和生命气质的精粹。”
周力至今保持着写书法的习惯,每天都写,就像一种身心的练习。她特别抄写了《二十四诗品》当中对“劲健”的描写:“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她写的是书法中应有的气韵,也是她在绘画中创造的新气象。这其中依然有父亲当年的教诲:“他说,书法也好,绘画也好,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气呵成的,把你的气息全部表达出来,这个很重要。”
2019年,周力成了首位在世界顶级画廊之一白立方(WhiteCube)的伦敦空间开办个人展览的中国女艺术家。她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抽象绘画语言,在西方文明的中心,坦然地、从容地对话着西方抽象艺术史,迎接最挑剔的观众和随之而来的热烈掌声。
在画布上以线条呈现世间万象和宇宙时空,这是关于线条的野心。周力选择了线条,线条也选择了周力。
2_
回想起当年去法国,周力说:“在艺术上,那完全是当头一棒。”
这是一个艺术创作者在卢浮宫、奥赛和乌菲齐美术馆里,仰望着历代大师的杰作时,心中的赞叹和感慨:“见了那么多博物馆里的好作品,你就知道在同一条路上超越前人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画得很好,但只是画得很好而已,但是哪一条路是属于我自己的?这就回到了怎么找到自己的问题。”
首先是找到真实的感觉。在回到课堂开始执教后,周力带着学生下乡,让他们回归自然,寻找第一手的感觉。“这个感觉才是最真实的。我们观看其他人的作品,只是学习的过程。只有回到这种真正的大江大海里学,你才知道山川有多宏伟壮阔”。
她带着学生走遍青海、山西、甘南、贵州,去观察古代建筑的榫卯结构,看一座桥是如何可以不打一个钉子也能建成;在山西永乐宫看壁画,研究古代的线条是在怎样的尺度和比例下诞生的。“我们油画系在永乐宫设了一个教学基地,研究那个年代所用的线条。在那里你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气息,气势磅礴。这是看画册感受不到的,只有到了现场才知道,为什么画家是这样画的。”
聊起山河给予的眼界和气魄,她兴致勃勃:“我们在青海湖,两边和前面有高山,前面是湖泊,人在那儿,就会觉得任何事情都不是事儿。后来和学生讨论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觉得—人太渺小了。人在城市里住久了会矫情,回到自然状态,会更自在一点。自然是一切的源头。就像文学作品,如果能看原著,一定是比看翻译的好。要打开自己感官的体验,就应该回到源头。”重新观看世界,恢复敏锐的洞察。然后,重新使用双手,去触碰大地、水果、蝴蝶的翅膀,再用这双手,在画布上、在装置作品上重新表达这一切。这是创造的起源。
周力强调的并非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找到自己的来龙去脉,再在这个时代找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个过程,未必跌宕起伏,却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磨砺自己的眼睛和双手。

3_
2000年,周力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反响极好,展览开到了德国,收获了鲜花和掌声。2003年,周力从生活和工作了8年的法国回到深圳,那是她生命中的分界点——深爱的父亲离世,让她陷入了长久的悲伤,甚至放下了手中的画笔。她要停一停,进行自我梳理,思考自己的艺术、自己的生活。直到2005年,她的第一个孩子出世,生命带来了喜悦和思考,周力从女儿成为母亲,生命之中出现了新的层次。
周力选择全心陪伴孩子。现在谈起来,那是“休息的7年”。那几年,她有了第二个孩子,喜悦和责任同期而至。她把画笔暂时放下,最少的时候,一年只画了两张画。对这段经历,她毫不遗憾,因为她在重新成为自己。
自我梳理,对周力而言极为重要。对一个艺术家而言,作品是树枝上的果子,有自己的成熟周期,果子等待的,是时光的滋养和内心的成熟。“创作不是说必须天天画画,而是回归到一种生活的常态。2000年中国美术馆的展览结束之后,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应该找到一个新的方向,要有进步。但我却不知道,如何能走得更远一点。”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瓶颈状态,對艺术家而言经常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周力做到了,她没有强迫自己去赶时髦,也没有不停参与新的展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她悄悄地隐藏了自己,到生活中去,到平凡中去,慢慢积累,直到生命的果子自己成熟起来。
“回过头看,那休息的7年是很富有启发的。我们不用每时每刻每一年都有进步,那是一种不必要的自我逼迫。我们是可以休养生息的,是可以停一停的……而且在这7年中,我并没有停止思考,只是没有把作品呈现出来。但我一直在成长。”
7年之后,周力重返课堂,开始执教,然后比从前更饱满地投入了创作。

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她在2005年的画作《蜕变》,变成了2015年为深圳机场创作的大型公共装置《尘埃-蜕变》。这是她对自己生命的内观和表达。她发现休养生息了7年之后,她的控制力和表达力都有了飞跃—从平面到立体空间,从书法线条到物理空间的表达。
2017年,收藏家余德耀拜访周力的工作室,看到作品后激动万分,于是就有了周力在上海余德耀美术馆的《白影》展览。这是周力想献给父亲的展览,她觉得自己曾经浪迹天涯,却对父亲陪伴得不够。而现在,她对父亲有了艺术家对艺术家的理解,也有了成为母亲之后,对人伦的深刻体悟。
那漫漫的7年,并非是荒废的啊。就像朗香教堂不同的窗户里透下的光与影,若没有小窗里那几抹淡淡的光束,大窗透射进来的那道光反而显得单薄,失却了丰富。
人的生命,也是光与影的协奏,是这一段时间和另一段时间的互相丰盈,而并非线性时间式的一味的高歌猛进。生命的河流,有急有缓,顺应时间和生命的本性,才能进入更开阔的水域。
一个艺术家拥有的最大权力是对世界的重塑权。周力重塑了组成生命的时光,时间于她,不再是一种限制,而成为了一种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