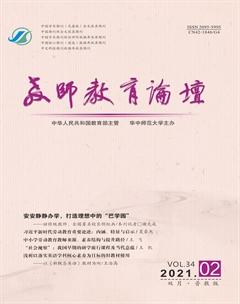从约翰·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视角浅析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
摘 要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一直备受关注。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具有必要性,也存在局限性。通过回顾近四十年来该政策的演进过程与相关研究,结合约翰·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辩证分析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相关部门需加强监督与审核,避免民族身份造假和“高考移民”等高考乱象;完善该加分政策应进一步着眼于考生的语言、文化、经济和教育差异,而非仅着眼于考生的民族身份。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其公正性,各地区应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权衡各方权益。另外,保障少数民族学生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也是促进全民教育公正的关键举措。
关键词 高考;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约翰·罗尔斯;正义原则
中图分类号 G40-01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995(2021)02-0070-03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旨在弥补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语言、文化、经济和教育差异,促进教育公平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该政策是加快民族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深远。一直以来,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备受关注,该加分政策的公平性也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本文将首先回顾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演进过程及相关研究,然后从约翰·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视角分析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探索该政策存在的问题,展望其发展。
一、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演进过程及相关研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是我国国情的特殊产物。新中国成立后,高考制度历经改革,但依然有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较甚远,所以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被沿用至今。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愈来愈多的学生拥有了参加高考的机会,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利益相关者不断增加。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旨在促进教育平等,然而没有政策是绝对完美的,该政策的局限性随着高考的大众化逐渐受到关注。国内学者常根据国内实情具体分析该政策,国外学者常将我国的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和国外的少数族裔高等教育录取优惠政策类比。
(一)政策演进过程简述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八〇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报告》提出少数民族考生可获得适当分数优惠,散居的少数民族考生会被优先录取,但没有给出具体的优惠要求和分值限制。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0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各省、市可依据自身情况降低少数民族考生投档分数,赋予了各地更多的自主权。该规定保留了对散居少数民族考生的优惠政策,对于聚居地的少數民族考生没有规定具体的分值优惠范围。结合《教育部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和《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这两年的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保留了各地的自主权,赋予了各高校更大的权力,明确了优惠分值上限,有关散居的少数民族考生享受的优惠政策被弱化。总的来说,近二十余年来的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不断明确了加分对象和范围,细化了优惠分值。
(二)政策相关研究回顾
罗秉正和范培廉于1980年发表的《今年西藏高考给人的启示》指出,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可促进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推动全民族的文化、教育及人才发展。文章还对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教育做出展望,提出了“重视教育质量”的观点。黄家庆对比分析了1989年至1992年新疆高考少数民族考生与汉族考生的录取分数线,同样指出“教育质量为少数民族教育的重中之重”,提出了“降低少数民族与汉族录取分数线差异”的目标。[1]随着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演进与完善,国外学者也开始进行该政策的研究。1998年,美国学者苏德曼发表文章《平权运动、少数民族与中国高等教育》,指出中国少数民族聚集地多为中西部经济及教育发展落后地区,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教育发展。文章还类比了美国的平权运动与我国的少数民族高考加分制度。苏德曼认为与平权运动相同,中国的少数民族高考加分制度存在一定局限性,即政策的模糊性、加分数值和方法的不统一性和不确定性。2005年,滕星和马效义发表文章《中国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与教育平等》,全面回顾了2004年以前的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根据田野调查的结果提出了少数民族高考照顾政策的问题与挑战,展望了市场经济下的少数民族教育。金东海和王爱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广,各地区教育发展水平不均,因此各省、市在实行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方面具有较强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多样性。[2]秦伟江和卫红娟分析了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局限性,指出绝对公平的教育政策是不存在的,只能尽力权衡各方利益,寻求相对公平。[3]卢永平从教育政策价值的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通过数据证明了该政策对于少数民族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影响。[4]2019年,陈丽发表了综述性文章《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研究回顾与展望》,文章回顾了该政策的起源和内容,总结了该政策的理论基础,分析了该政策的实施现状,展望了该政策的发展。总之,针对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研究随着政策的演进而发展,大部分研究不仅能够考虑到该政策的必要性,也意识到了该政策的局限性。
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原则”
约翰·罗尔斯以其著作《正义论》和“正义原则”闻名于世。
约翰·罗尔斯秉持“正义至上”的理念。他认为,正义的主体是“社会结构”。稳定、有序的“社会结构”是实现公正的基础,公民间达成的共识——“社会契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约翰·罗尔斯认为,人们生来就是不同且不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社会运行过程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以自身利益为重,难以达成“社会契约”。为避免这个问题,稳定“社会结构”,达成社会公正,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实验”:假设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个“无知之幕”,人们不知道自己的阶级、种族、民族和性别等初始条件,也不知道社会运行轨迹。此时,每个人都处于“原始状态”,为避免将自己置于劣势处境,人们会正义行事,不会有失偏颇。
约翰·罗尔斯认为,在“原始状态”下,人们会遵循如下两条正义原则:
第一条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享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制度,此原则是“正义原则”的根本与基础。该原则的主体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只有当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时,他们才有可能实现个人价值。
第二条原则包含两条小原则:
(1)“机会平等原则”:各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
(2)“差异原则”:允许差异存在,但所有人,尤其是“处境最差者”都要获利。
根据第二条原则,人们拥有均等的机会去争取不平等的职位与地位,当“处境最差者”获利最大时,允许分配不平等的存在。
约翰·罗尔斯相信,在“公正原则”的指导下,政策与制度会合理规划权利和义务,责任与利益会在社会运行中合理分配。
三、从“正义原则”视角分析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
根据“正义原则”的内容,笔者将对于该加分政策的分析分成了三个主题:
(一)教育权利与质量
“平等自由原则”要求保障少数民族人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少数民族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也增加了他们考入高校的机会。但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水平来看,不是所有少数民族学生都具备上高中的经济实力,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教育质量也有待提高。该加分政策仅为能够参加高考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一定程度的帮助,但不能保障所有少数民族学生都能接受基础教育。因此,该政策无法触及没有机会参加高考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利益,这些学生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并未受到此加分政策的保护。另外,少数民族聚居地教育质量与发达地区相差较远,即使有政策的照顾,优惠分数也是有限的,部分少数民族考生还是不能进入高校接受教育。再有,由于教育水平较低,少数民族考生的学业水平基础较差,即便在政策的帮助下进入了高校,他们也很难跟上其他同学的学习步伐。该政策尚不能从根本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水平。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是促进教育公平和推动少数民族聚居地教育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该政策仅仅是发展少数民族聚居地教育的一种措施,而非全部。若要全面促进民族教育的发展,在不断完善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同时,还要促进少数民族基础教育质量提升,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一定经济补助,保证他们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增加他们参加高考的可能。
(二)该政策引发的“高考乱象”
“机会平等原则”要求所有学生都能在高考中经过平等的角逐进入不同高校。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为少数民族考生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该政策存在一定局限性,引发了一些“高考乱象”,加剧了考生间角逐的不公平。例如,相关部门对该政策的监管和审核不完善导致出现学生民族身份造假、更改户籍参加高考等乱象。一些汉族考生为获得优惠分数伪造少数民族身份,如2009年重庆市有31名考生伪造民族身份,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查出高考中更改民族身份的考生有800多名。这种造假行为危害了各民族考生的权益,使得以公平公正为目的的优惠政策适得其反。由于各地经济、教育水平不同,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同,一些考生为缓解竞争压力,更改户籍,转移到录取分数线较低的地区(如少数民族聚居区)参加高考,进行“高考移民”。这种移民行为伤害了各民族考生的利益,加剧了教育不公。针对这些乱象,有关部门应加大考生身份审核和考试报名监管力度,不断完善相关管理政策,竭力保证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公正性。
(三)“处境最差者”的界定
“差异原则”要求参加高考的“处境最差者”必须获利。为更好地遵循这条原则,对于“处境最差者”的界定至关重要,但界定是复杂而又困难的。
首先,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接受教育的不仅仅是少数民族考生,还有很多汉族考生。这些考生接受的是同等水平的教育,如果单独将少数民族考生界定为“处境最差者”对之给予加分照顾,那么同地区汉族考生的利益就会被损害。另外,有些汉族考生聚居在偏远地区,整体教育水平较少数民族聚居地差之甚远。在此情况下,聚居于这些偏远地区的汉族考生相较少数民族考生而言处境更差。如果把这些汉族考生界定为“处境最差者”,他们显然没有从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中获利。再者,少数民族考生聚居地也存在差异,有些少数民族考生生活在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而有些生活在教育质量较差的地区,此时很难将所有少数民族考生都划分为“处境最差者”。
针对以上问题,各地区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竭力权衡各方利益,制定更为详细的政策。另外,少数民族身份不代表弱势群体,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不应仅针对民族身份,而应更多考虑考生间语言、文化、经济和教育的差别。
四、总结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历史较为悠久,该政策也在不断演进和完善,针对该政策的研究也随之深入发展。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既有必要性,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公正原则”为基础,笔者剖析了该加分政策存在的問题,提出了应对策略。为进一步保障该加分政策的实施,相关部门需加强监督与审核,避免出现民族身份造假和“高考移民”等高考乱象[HTSS];完善该政策应进一步着眼于考生的语言、文化、经济和教育差异,而非仅着眼于考生的民族身份。为进一步加强其公正性,各地区应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权衡各方权益。除该政策以外,保障少数民族学生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也是促进全民教育公正的关键举措。
(车赛西亚,伦敦国王学院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学院,英国 伦敦 WC2R2LS)
参考文献:
[1] 黄家庆.实现高考民汉录取线基本接近的途径与方法[J].新疆社科论坛,1993(1):59-65.
[2] 金东海, 王爱兰. 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学生高考优惠招生政策若干问题的思考[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84-88.
[3] 秦伟江,卫红娟.对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政策的政治学思考[J].考试研究,2007(1):41-52.
[4] 卢永平.少数民族考生高考招生特殊政策的价值分析[J].中国民族教育,2007(9):10-12.
责任编辑:谢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