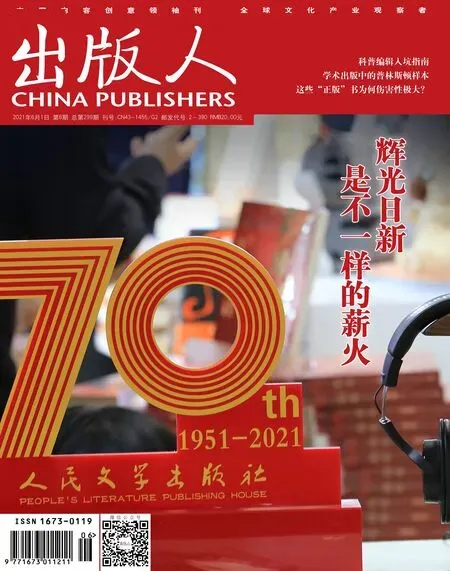科普编辑入坑指南
编辑整理 | 谭睆予
为什么想不开做科普?

十五年前,科学松鼠会理事长、果壳联合创始人小庄“入坑”科普,有了十多年做科普的经历铺垫,他仍然忍不住灵魂发问:为什么想不开做科普?
作为一位文科生,未读的主编兼科普工作室主编边建强告诉小庄,自己从只能欣赏“夕阳无限好”的诗意美,到打通诗意美和理性美之间的壁垒要归功于以前读到的科普读物。他现在觉得自己能做科普,“还挺幸运的”。
创办了混乱博物馆的刘大可表示自己不喜欢“科普”这个词,他觉得这是导致出版社做科学读物越来越浅显,甚至成了大家争浅显的竞赛的潜在原因,科学的、精确的、深刻的、复杂的一面没法带给读者。
究竟应该怎样做科普?科技杂志《离线》的主编李婷尤为推崇手握全球顶尖科学家出版合约的出版人杰姆·波克曼。这个人能找到顶尖的科学家,让他们用讲故事的方法将一些深刻的科学问题讲给读者,使后者体悟到科学之美。
在甲骨文主办的第四届译想论坛上,李婷、小庄、刘大可和边建强几位资深的科普领域从业者,将近几年越来越热的科普出版拿到了台面上讨论,他们的激烈探讨,或许可以成为一位科普编辑的入门或是“入坑”指南。
为什么“想不开”要做科普?
小庄:
我至少15年前开始做科普,它当时是很冷门的类别,莫名其妙地就做起了这个。刚刚也在想,在座的几位进入科普的途径或者契机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会都这么想不开来做科普呢?边建强:
下边我就顺着小庄老师的话题,借着这个机会回顾一下这些年做科普的心路历程。我刚才给这次分享想了一个题目,一个文科科普编辑的自白。说起来做科普,作为一位编辑,我之前做过书的类型是比较杂的,经管、生活都做过,后来我在未读创办的时候,加入了未读。当时我们未读的slogan叫“有趣、实用、长知识”,知识类图谱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产品线,所以我也是阴差阳错,冥冥之中是有一种缘分在里面。
我记得在十几岁,大约是青春期的时候,学了一些基本的物理知识,当时产生了一个疑问,你看到太阳的时候,是去享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种诗意的美呢?还是要把它看作是一团在核聚变的氢氦元素?后一种的美感完全没有了,当时我还是觉得那种夕阳无限好的诗意是美的。再过了一些年,我读到了那本《发现的乐趣》,突然就打通了诗意的美和这里边理性的美之间的壁垒。最近我们要出版的一本《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他最后一章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宇宙的视角,用宇宙视角看待整个世界,看待整个生命、整个人生。自己在从事科普方面的工作,反过来它又能给你一种洗礼,所以我觉得做科普还是挺幸运的,也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虽然我是一个文科生。
作为一个科普编辑,把那些书传播给读者,他是一种能量的传播,或者说光的传播,像我们主题一样,我们编辑可能是反光镜,刚才说的很多视角,能够通过我们反射给读者,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小庄:
你的这个经历可能会有很多人呼应,就像我自己开始对科学感兴趣,觉得我非要学理科不可,非要做这个不可,我忘了在初中还是高中,那个时候听电台突然间听到关于黑洞,你从来不知道宇宙当中有这个存在,当时是初高中转换的时间,带给我很大的恐惧,每天想起来觉得惶惶不可终日,你觉得你怎么会在这么一个大的虚无里,你要去把这个虚无搞清楚,你必须得去了解,就开始搜寻这方面的东西。我们那个小城市没有这个条件,我记得我进大学,进图书馆,就扑向霍金的书,找温伯格的《最初三分钟》这些书。现在说起来,早期的就像《第一推动丛书》这些书,他们有很多是谈宏观的,宇宙的,谈天文的这些东西,真的有点如饥似渴,他给你打开了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逼着你非要了解这些东西。刘大可:
严格地讲,我不是一个科普行业的人,我应该是说一个被科普的人,是把我被科普的学习成果分享出来这样的一个人。我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没有去找工作,就在大象公会做了一个撰稿人,接着就在那做了混乱博物馆的视频节目。2017年的时候我开始用微博,我当时不停地发这样的内容,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我应该是一个科普人士。
2018年,我从大象公会辞职出来。我开始想着我自己要写一本书,我在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不是一个科普作家,我不是有很多知识要把它介绍给公众的人,我是公众里面对科学充满爱的那个人,我希望告诉其他人,我能够通过互联网,通过现在21世纪的媒体技术,掌握很多很有趣的知识,这些知识虽然你看不出来它有什么用,但是它是能让你觉得活着有意义的东西。
“让科学流行起来”
小庄:
我现在觉得我在做科普,其实把很多科学文献里的东西翻译给大家看,因为我能看懂它,我比较有经验一点,我在看那些论文,看那些古老的,更久远一点科技史的东西,我看明白了,然后把它转述出来。现在我觉得我的写作也还是包含那个成分的,从大的意义来讲,我不一定翻出一本书,我讲出这番话,或者说我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段什么,都是对于一些已有文献的,已有的知识的翻译和解读。我是觉得翻译是在对照你已有的经验,对照你对一个东西的记忆,把它用你的方式讲述出来。我知道一个事情,原来它是这样的,我很想告诉你,是这么一个过程。
李婷:
我刚进入出版行业的时候,大概是2010年前后的时间,当时互联网科技这个概念刚开始流行,我在一家传媒公司,当时我们察觉到互联网科技的内容有可能在未来成为非常主流的东西,最早就去引进了互联网公司的传记,关于科学技术的应用这一类的偏商业和经济类型的书。这些书可能跟我们现在所谈的科普关系不是那么大,在那个时候,它跟科学技术相对来说联系还是非常紧密的,互联网从哪里来,可能要谈技术,技术从哪来,可能还要反过来谈科学。这个事使我发现科学和技术或者说科学技术在未来一定会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时代有非常强的影响,这个东西最终惠及到出版里面,惠及到每天阅读的内容里。
我后来去了译言网,在译言我做两件事情,第一跟翻译完全相关的“古登堡计划”,这个是把国外已经进入公版领域的书引进到国内,组织译者进行翻译。第二件事情跟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联系更紧密,当时在译言做了小的图书项目叫“东西文库”,我们总共出了大概有二三十种书,他们当中一些在科技或者科学技术、互联网领域,是开山类型的或者说奠基之作,比较知名的是凯文·凯利一系列书,都是东西文库出版的,最有名的就是《失控》,这本书是凯文·凯利在1994年写的,我们引进到国内是2010年,已经比国外晚了15年。
我们虽然晚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也跟上了,这个时代可能会赋予给我们新使命,除了要追赶,甚至我们还要去超越它。
我记得周五晚上那场论坛,几位老师在台上说,我们去做阅读的时候,肯定不是因为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我带着什么样的目标去看出版,他都会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可能你突然遇到或者别人介绍给你或者你去躲雨,来到这个书店里,看到了图书的介绍,这个东西只要你看了,他可能会以某些碎片的形式留存在你的身体里,我刚才说到的,我看到的一些书或者我做的微小的事情,就会成为我身体某些小的部分。
我自己生长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不管是科学还是技术,还是更充满想象力的虚构作品,他们是非常真切地在影响着我们。
小庄:
说实话,做科普这个事,包括那个时候做科学松鼠会,“让科学流行起来”,但是你做了那么久,科学到底有没有更流行呢?是非常存疑的。说到科普,其他类别的作家老师就会说,科普现在还不热?因为的确好像看到的每个出版社都想出科普,好多编辑觉得这是个热点,但是在我来讲,你其实很寂寞,你做的东西,人家知道的不多,包括现在,如果讲起标杆,还是只有《时间简史》。大量的科普,当它没有传达出去,它就被限制在那个文本里。我到现在还没有勇气重新来做这个事,我觉得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但我也很欣慰,这个事情一直有人在做,包括这几年能够出到那么多书,还挺惊讶的。
科普这个事你们觉得做起来难吗,你面临的,不管是市场还是面对大众,你们的共鸣多吗,支持你们做下去的力量在哪里?
边建强:
从我们作为出版的从业者来讲,包括我作为一个科普读物的读者来讲,从我20年前接触到的科普读物,一直到现在,科普市场是越来越繁荣,不管是从出版的数量来讲,还是它的种类,包括它的质量,过几年,就会有一个上升的阶梯。我小时候看到的科普书还很少,我记得从《时间简史》开始,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时期,国外的译著特别多,不光是科普,科普是顺带被引进进来的一个阅读门类。给人的感觉那时候的书是供小于求的,大家全都在找书看,那个时候科普书也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到一本书叫《可怕的对称》,好像是华人科普作家写的,我现在完全忘记那本书写的是什么,就觉得那本书好厉害,醍醐灌顶的感觉,那本书是在我同学的桌兜里发现的,质量不好,一提起来书页就掉了。现在科普书的种类、质量、出版量、以及书的形态,已经比那个时候要进步很多。从我自己做科普的这六年时间来讲,我也经历了科普书一次又一次小高潮。我觉得市面上很多的书还是像小庄提到的传统出版社出的《第一推动》这种类型的,因为它足够经典。
做科普不是竞争浅显的比赛
小庄:
大可是创作者的身份,在下面和他聊天,他说他很不喜欢科普这个词,我说我也不喜欢,这个词本身就会有些问题,大可可以从这方面谈谈。更多是从创作者身份来聊,你觉得科普到底是更流行吗,或者说你觉得存在隔阂,没有那么多人真的接受它,它的问题是在哪里?刘大可:
我为什么不喜欢科普这个词。我其实很反对在书店的货架上面专门标一类叫“科普书”,在另外一个货架上标“科技文献”,我们会找到科普读物和科技文献,但是从科普到科技文献之间有巨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是没有分类的,我希望这类书应该叫科学读物,就着科学这个主题可以写很多东西。如果我们专门就叫它科普的话,说明了我要面向一些无知的人介绍浅显的东西,它会有这样一种默认,写的人他会觉得我现在有很多东西,我知道很多东西,但是我不能讲,因为他们听不懂。看的人也会觉得这是科普,他不应该讲很深刻的东西。同时,我也只是想知道一些很浅显的、基本的东西。出版社在出这个书的时候,会想我要面向的所有人都能看懂这本书,这个书写得稍微深刻一点,这本书就会不好卖;读者会说,我是来看科普的,我不是要听你这么专业的东西,写的人是不是写得太专业了……会进入这样一个不停地往下压的过程。这样会陷入另外一种通俗大奖赛:既然不能把深刻的东西介绍出来,那我们就比赛谁能把话说得特别浅显。
当我们圈定是科普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虽然这个概念并没有一个人来定义说它就一定要比浅显的,但是我们在传播过程中,它会陷入这样的漩涡,大家都会比浅显。这样无法把科学的、精确的、深刻的、复杂的一面带给读者,读者就不能体会到科学最关键的东西。
边建强:
大可说的,我理解是,就像他们说的生物多样性的道理是一样的,科普图书作为一种门类,也会有多种多样的形态,比如说有给孩子看的,也要有探究科学终极真理的一些书。大可可能觉得不好的一种现象,大家全都在往下走,或者往浅显了做,或者往更加幼稚化去做。刘大可:
你这样一说,我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当我们陷入这样一种局面以后,就会变成所有科普读物都是给孩子看的,给那种我家长要买一套书给孩子做课外读物,让他在学习初高中知识的时候,有一个参照物可以学得比别的孩子更深刻,更透彻一些。但是一件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作为成年人,也需要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成年人的精神世界一定比孩子精神世界更大,不然何以成为成年人,但这个成年人的精神世界是谁来关照的?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一定要有科学的东西要让成年人的精神丰满起来的,我们不可能只靠文学作品,只靠文学、只靠艺术品是不够的。
比如说《第一推动》那套书,很多人都看,我觉得那套书就是很典型,不应该叫科普书的,相当一部分人说它是科学读物,它不应该分在科普书这样小的名字里。它是给成年人看,它要用很长的句子,很复杂的概念,很抽象的东西去解释一些关于宇宙本身的东西。概括地讲,科普书这个概念,它就像把科幻当做儿童文学,或者把动画片定义为给孩子看是一样的。这个名字里就带着这套意思。
到底怎样做科普出版?
李婷:
回到论坛本身讨论的关于引进或者译著或者翻译的平台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和必要去做国外的科学的写作或者科学书籍引进的,这点上,有两个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地真切,第一个是我们在做科学书籍引进的时候,会跟国外一个叫做波克曼的公司经常打交道,这个公司他的创始人叫杰姆·波克曼,他非常难打交道,但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斯诺以前说的两种文化,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杰姆·波克曼在1980年代的时候提出第三种文化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非常有启发性,为什么叫做第三种文化呢?科学家代表着一种文化,另外一边是知识分子代表的文化。斯诺认为这两种文化是水火不容的,他希望这两种文化可以产生交融。杰姆·波克曼提出的第三种文化,从表面上看,就是中间地带或者交叉的文化地带,但是从杰姆·波克曼自己做的事情,从80年代开始签下很多科学家的或者科学工作者图书出版的经纪约开始,你能发现他做这件事情的野心,而且他也在很多地方非常公开地说,第三种文化不是说科学和人文交叉的文化,而是科学入侵人文的文化。
我几年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问题,有个人是以色列大学的教授,他所在的大学和他所做的研究应该是非常顶尖的,他说他想出一系列的书,他觉得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去做出版的话有很多限制,而且出版之后,再去进行全球传播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限制。他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我想去做更多更广的全球传播的话,应该去找什么出版社?底下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回答,但是能看到排在前面的七八个回答基本上都是“find pokeman”,就这么简单、这么粗暴。波克曼在这个领域,在美国,甚至在英语国家里,他做到这个成绩,也许我们国内一些出版社是可以去效仿或者可以去追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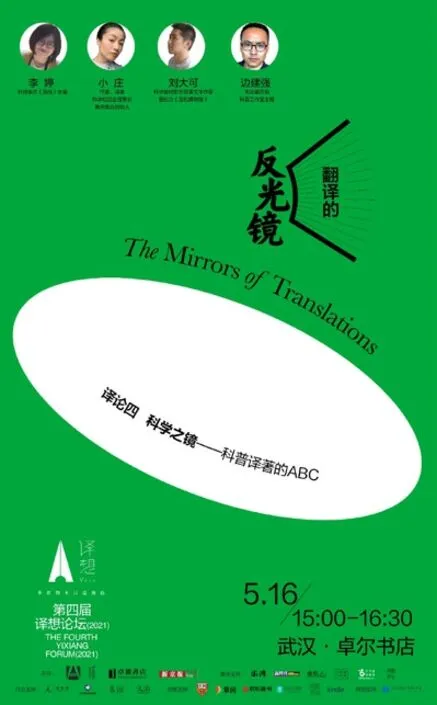
观众:
最近看了一本科普书是《一个天文学家的夜空漫游指南》,是越南籍的科学家,他也是把科学跟绘画、跟诗歌结合在一起。我作为文科生读起来是挺享受的。但是刚刚听到大可老师说他不太喜欢科普这个词,就是有知识的人去给一群无知的人写一些浅显的东西,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不是浅显的东西,因为那种比较深入的科普性的书,比如我之前看数学类的,我看不懂,我就想问问,如果科普不做得这么浅显的话,它怎么样大众化?刘大可:
我刚才说的深刻,它不一定是晦涩的,我在思想性上达到怎样的深刻,不见得我在语言上体现得多么难懂,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人真的把这个东西搞得很清楚,它有很深刻的思想,要讲给你的时候,他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个说得特别通俗,特别明白,因为他有充分的表达欲望,他强烈想把这个东西让你知道,这个时候他的语言应该是朴实的,你通过朴实的语言感受到越来越深刻的东西。我想说一个关于深刻的东西的例子,有一本书叫GEB,这本书很知名,它其实不是科普书,它就是典型的科学读物,它是讲哥德尔第二不完备定理的,这个定理是没有经过专门数学训练的人所能搞懂的最高深的数学理论,因为它是讲逻辑学的,数理逻辑的,而且是一阶次的数理逻辑,所以它不需要很多的符号,他慢慢用平常的语言可以讲出来,这个东西曾经解决重大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很厉害,我要把这个东西用浅显语言讲出来。
边建强:
这位同学的问题对我们出版从业者是一种要求或者是一种鞭策。我听到的意思是你们选的书还不够好,我看不懂,我看懂的书你们没找到,没有给我们出版出来。这就让我想到上午甲骨文分社的社长董风云老师说到一句话,如果没有译者,作者是不存在的。对出版人来讲,对读者来讲,没有我们,作者也是不存在的。但这就对我们提出了一种要求,什么样的是适合大多数人看的所谓科普书,是不是还没有引进进来?或者说我们没有找到作者去创作。这是我们出版人职责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