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出》中方达生从“影子”到艺术人物的生成
钟超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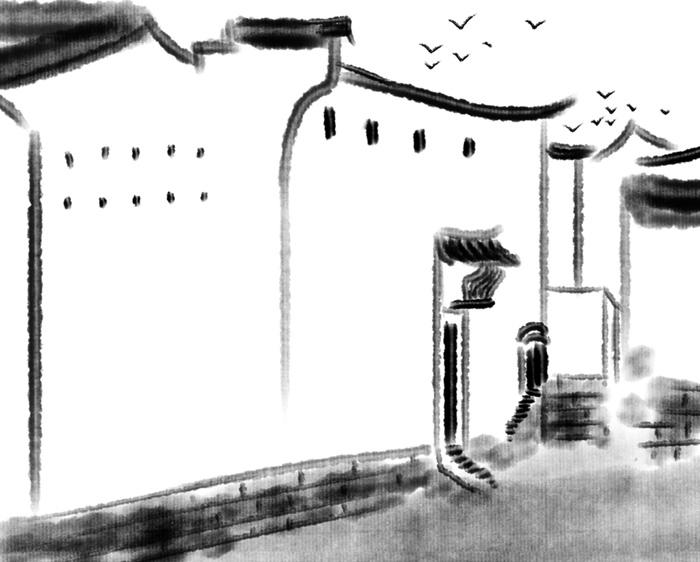
学界一般以为,方达生是章靳以与曹禺的“综合体”,虽有如此丰富的本事原型,但从剧本看,方达生在性格完整性与形象完成度等方面皆不能与陈白露相媲美。究其根由,并非作者写作功力见拙,而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在《日出》中,方达生的角色定位即在于“辅助者”,以辅助陈白露的“反对者”功能的完成,这种功能设置,对《日出》整体创作意图的实现无疑至关重要,具体通过三个形象实现这一创作意图。
一、“代偿”策略与“执爱者”
由于塑造陈白露形象的需要,方达生在剧中明显被设置成“执爱者”:挚爱于所恋之人,执着于已逝的青春、物事与梦想,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1)事关生活的单纯与热爱。方达生虽然憨厚如呆子,却有着正直的三观。他认为单身女子自己住在旅馆里,“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日出》,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8页)是放荡与堕落的。此外,他忠于自己健康的生活方式,不随波逐流。他不会抽烟,不会跳舞。他还敢于直面黑暗,看到旅馆里的人日夜颠倒,认为“这里的人都是鬼”(《日出》,40页)。总而言之,方达生喜欢一切富有生气的事物。(2)对陈白露的执爱。方达生和陈白露青梅竹马,青葱岁月里曾彼此相爱,但命运捉弄使两人最终分道扬镳。当他听到陈白露过着堕落生活时,依然坚信陈白露清纯如初。他坦承自己念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永远在心里头活着。”(《日出》,24页)他是全剧唯一一位真心待陈白露的人。(3)唤醒、保持陈白露内心爱与美的能力。方达生是陈白露的感情依托,在方达生面前,陈白露可以以“孩子”示人。此外,他对陈白露的每一次关于“离开”的劝说,都可以看到陈白露感情的起伏与递进,最终“灵魂”被方达生激活的陈白露,身体却无法逃离这个牢笼,最终选择永远离开了人世。三层整合,使方达生性格充满“爱”的因子。
以上三层“执爱”,使方达生的性格充满单纯、明朗之物,他热爱“他物”,并尝试努力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影响他人。这实际上也构成了《日出》之不驯服从现实、挑战现实的力量。考之现实,这三层设置有的源自原型章靳以,有的则属曹禺的改写。第一层有生活材料作为根据。在靳以作品中,无处不透露出他对生活的赤诚与生命的敬仰,常使自己心灵和自然合二为一。在他眼中,狗是“天下最忠于主子的动物”,他能听到“高摩天际的大树的高枝上,正有小鸟快乐地叫跳着”。这些生命之爱,与方达生如出一辙。第二层的根据亦十分充分。靳以曾说:“我有旺盛的生命,我有固执的爱情。我用我的爱情,滋育我的生命的树,使它在大地间矗立,不怕大风雨的摇撼。”这些话证明了靳以将爱情视之如命。因此在他早期作品中,有大量追忆爱情之作,如《往日的梦》,一边责怪对方的残忍与诉说自己的决绝,一边止不住关切对方:“听到说你是瘦了,又憔悴了,我的心就起始苦痛。”等等,可见方达生对于陈白露的执爱有着扎实的现实基础。第三层设定则多属艺术虚构。曹禺曾欲言又止地说:“靳以和这位王小姐好过。”此处提及的“王小姐”,即罗隆基的伴侣王右家,亦是陈白露的主要原型之一。但据现有史料,王右家与靳以的这段过往,鲜有提及,需要考辨。王右家曾因罗隆基一句“一定会给这死气沉沉的社会,平添生气”而决心追随,也曾因唐季珊并非和罗隆基“同一个圈子”,不必“被他(按:罗隆基)暗笑”而选择再嫁商人妇,但靳以仅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文人,无论在身份还是关注度上,均不及两位政商传奇人物,更不可能达到“给社会投下了一颗爆炸性的原子弹”的效果。因此,靳以也不能拥有保持王右家之爱的能力。
故,曹禺在話剧中采用“代偿”的故事策略,代替与补偿靳以受到“冷待”的事实。一方面,基于宽慰之需,对靳以爱而未满的事实进行补偿。情伤后,过往爱恋让靳以久久不能抒怀。面对好友的一蹶不振,曹禺用热爱生活的方达生转移靳以幽怨的爱情视线,用陈白露对方达生的爱来补偿现实中章靳以“无名无份”的哀伤。此外,这也是对以“多愁善感”示人的靳以的解读补偿。靳以的性格中,多愁善感的情绪非常浓烈,笔尖划过之处满纸愁容。其实靳以并非悲观倦世,他爱生活,只不过他的爱过于沉重,于是曹禺故意从靳以身上“提纯”甚至拔高“爱”的能力,而“过滤”其浓重“愁感”,以消除靳以愤“爱”嫉俗而带来的阴郁感,既塑造了一个感染人的方达生,也侧面向世人展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靳以。
另外,应悲剧性反面人物“否定的美质”的叙述之需,《日出》同样有用方达生“照亮陈白露之美”的艺术虚构代替靳以“在王右家心里毫无涟漪”的现实的必要。对于人物塑造,高尔基曾说:“每一种品质都未必能够完全决定一个性格。”中国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使人物“符合历史的正确反映”,文学中出现了只显露一种“品质”的“脸谱化”人物。但如果把文学看作“人学”,人就绝不可能只有一种性格,只向世人展示一种面貌。陈白露作为“悲剧化”人物,拥有着传统美德不乏却又不容的“美质”,深具“否定的美质”(别林斯基)的特征:“它不是真正的美,又有别于一般的丑;它具有某种美的外观形态,又受事物丑的恶的本质方面或主导方面所规定、支配和制约,以至就是丑恶本质的表现形态。”陈白露时常表露出她执于物欲、轻视爱情、蔑视生活、自甘堕落的“丑恶本质的表现形态”,但也不时展现出她善良、热心肠、独立的“美的外观形态”。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方达生作为“执爱者”的作用,他的存在,照亮陈白露身上的美好,推进陈白露“否定的美质”的叙述机制运作。陈白露在剧中是十足的弃世者,她总以“事不关己”的姿态示人,如此,更别指望她会对眼前的世界报以真情实意的爱。但在方达生的感化下,陈白露开启了在残酷的世界里对爱的感知。尤其在两人一次赏霜花与关于“名誉”的争论后,陈白露在无人之时的表现:“她悄悄地在窗上的霜屑划着痕路。……她快意地叫出来。她笑了。”(《日出》,126页)能快乐地玩乐霜花,显然她将方达生的话“听进去”了。这也为接下来陈白露帮助“小东西”,并连续用五个“喜欢”表达感情提供了合理的行为基础。遗憾的是,虽然在方达生爱的感召下,陈白露不时会成为众人口中“又一个——疯子”(《日出》,176页),却依旧不能抵抗“丑的恶的本质方面”的“规定、支配和制约”。她虽然提供给“小东西”容身之所,但随意一句“那我把她送给你了”(《日出》,126页)可看出其人情冷淡。第二幕末与方达生一同寻找“小东西”,但第三幕她已经回到了声色犬马的圈子。陈白露的“美质”犹如昙花一现般,终归消弭于现实,至此,方达生在“执爱者”的作用下,一个“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坏”的陈白露,便凸显出来了。
二、“人道主义”的来源
随着剧情推进,方达生在“行动”上已有所进化,不再局限于儿女情长。他除了被设置为“执爱者”的形象以外,被添加了“人道主义”元素。具体也体现在三个层面:(1)“不合时宜”的正义感。当知道黄省三带着孩子自杀,他感慨“这太不公平了”(《日出》,217页);当“小东西”不见了,他表示“我要找她去”(《日出》,171页),哪怕“小东西”是金八看上的人。(2)左翼倾向的人道主义批判。方达生是全剧唯一“醒着”的人,他质问“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这么残忍”(《日出》,261页),控诉“为什么你们允许金八这么一个禽兽活着”(《日出》,261-262页),能直面金八等人的丑陋行径:“臭虫!金八!这两个东西都是一样的,不过臭虫的可恶,外面看得见,而金八的可怕外面是看不见的,所以他更凶更狠。”(《日出》,262页)此时的方达生是敢于直面“人吃人”社会的左翼“先锋”。(3)揭示陈白露作为“人”的悲剧。他耿直揭开陈白露少为人知的伤疤:“我知道你嘴上硬,故意说着谎,叫人相信你快乐,可是你眼神儿软,你的眼瞒不住你的恐慌,你的犹疑,不满。”(《日出》,264页)方达生明白困住陈白露的还有这个强权统治的罪恶世界,他劝说陈白露“远远地离开他们”(《日出》,264页),实际是向世人揭露陈白露悲剧的实质。
考之史实,可知有的来自原型,有的则是改写的结果。其第一层有原型作为“刻模”。诗人姚奔回忆:“靳以给人的印象,是热情、诚恳、富于正义感,对人处事,爱憎分明。”他的散文中出现不少对被害动物及人类的哀怜,因此谈到靳以,亲友们不约而同评价:靳以是“多么正直”的人。第二层也有现实材料可溯源。曹禺与靳以作为挚友,他们不谋而合地将目光锁定在纷乱的黑暗社会。靳以眼中的社会,是“打着谎言或是欺骗着,几乎成为天性”的,是为达官贵人作“嫁衣”的。与靳以相似,曹禺眼中分崩离析的世界也让他“按捺不下的愤怒”,正是两人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渴求,对丑陋现实的唾弃,促使曹禺借用方达生之口,义正词严地揭露社会丑态。第三层则属于曹禺匠心独运的虚构。如对城市化的衍生物——“摩登”的理解,王右家认为:
“摩登”,并不仅仅在剪发画眉,穿西服,着皮鞋上追求,我们以为思想上,知识上的摩登更要紧,总之,各方面都要“摩登”才好。同时,一个国家全数妇女中,只有少数服饰上外表上的摩登,这个国家依然不算摩登的国家。
可见,“各方面都要‘摩登”是有物质前提的。故王右家关注的是已解决了生存问题的贵妇名媛的思想纳新问题,但靳以与曹禺关注的是底层妇女的生存问题,靳以甚至对城市化附带着更多的“仇视”心理。王右家的立场与靳以、曹禺极为异趣,对他们的社会批判与“人道主义”恐怕也很难以为然。因此,在现实中,靳以这类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文人难在思想上成为“唤醒”王右家之人。《日出》所建构的方达生与陈白露之思想关系,无法从原型人物关系上取得根据,必须进行技术上的改写。
而曹禺之所以让方达生披上“人道主义”的羽翼,与补偿心理机制有关,方达生的“人道主义之声”,包含了曹禺呼声。一则,妇女宿命感催生了曹禺同情心。曹禺同情一切不公,同情弱者,尤其女性。“我是妇女的崇拜者”,曹禺认为女人不管是从生理角度还是社会角度,都是最苦的。因此他认为“落在地狱的‘小东西,如果活下去,也就成了‘人老珠黄不值钱的翠喜”。“小东西”的失联,翠喜的失足,仿佛冥冥之中搭建了一条妇女命运轮回之路,更让曹禺痛苦的是,这种轮回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世界的映射。这让一向以妇女为敬的曹禺,对妇女同情心更为强烈。二则,实地考察后催生了曹禺强烈的同理心。为写好“小东西”情节,曹禺曾乔装打扮得到大量真实材料,但也饱受了很多侮辱:
我幸運地见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物,他们有的投我以惊异的眼色,有的报我以嘲笑,有的就率性辱骂我,把我推出门去。
以身份感和作家风骨傍身的曹禺,却被狗彘不如的市井无赖言语侮辱,自尊心被无情践踏,“我希望我将来能用一种符号记下那些腔调。每一个音都带着强烈地方的情绪,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的耳鼓里。”曹禺首次“易容”,身心均体会到了贫贱如泥的底层人民的苦痛,与往日心里不痛快相比,更多了一份感同身受。因此,曹禺在写作中也将自己之于女性与底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深深地投射于方达生这一人物之上。
无论是出于原型的现实依据,还是出于心理补偿,“人道主义者”方达生都见证了陈白露在这个罪恶世界里的沉沦。这表现在两层。(1)方达生的存在凸显了陈白露难以摆脱的人性弱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道:“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亚里士多德没有进一步对“错误”进行界定,但朱光潜认为此观点可表明亚里士多德不仅认为人物悲剧是命定,还有“悲剧的灾难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物性格弱点或过失的惩罚”。以此观之陈白露,其悲剧也是某种性格弱点所致。但陈白露的弱点不是在觥筹交错的人际交往中显现,而是在方达生“人道主义”的感召下暴露的。在“宝和下处”看尽人间惨境的方达生,对陈白露已经不拘于爱的怜惜,他更多的是对女性命运的同情。陈白露并非没有机会离开,因为方达生锲而不舍的解救,她机会很多但却亲自放弃,甚至在方达生给出了“先离开这儿”(《日出》,264页)的紧急方案,她依然无法勇敢迈出第一步。“对于悲剧来说,致命的不是邪恶,而是软弱”,哪怕陈白露有过与“黑三”们抗衡的经历,但在相同“摔倒”之地却不愿意重来一次,懦弱这一弱点暴露无遗,这也揭示了陈白露人生悲剧的第一层因素——性格悲剧。(2)方达生对陈白露人生悲剧揭露还表现为他们在“灰色地带”的“信仰博弈”。17世纪后期英国批评家托马斯·赖默提出“诗的正义”说,认为文学作品应坚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原则,最终以实现惩恶扬善的道德目的。但这种过于绝对的观点,在实际中却并未完全得到认同。生活中更多的是“善”与“恶”交缠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不仅体现在“善”“恶”在独立个体身上交替与抗衡,还体现在“惩恶扬善”的过程中,“善”不一定得善终,“恶”也不一定报应不爽。剧中“金八”们越活越有钱,但黄省三一辈子兢兢业业,却换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下场。在这样一个人人不得安生的“灰色地带”,陈白露倒是清楚“太阳不是我们的”(《日出》,328页),结束自己生命。曹禺对此解释为“她气馁了”。但方达生未然,他决心成为真正的“傻子”,在感化陈白露不成功后毅然出走,寻找“傻子”的前途去了。他们对“灰色地带”作出的去留,实际上是通过对“灰色地带”的各自解读而得出的具有个人特色的生存信仰。方达生和陈白露关于“信仰”的这场博弈中,没有输赢,而是各自检验何种方法能推进这悲惨社会里“惩恶扬善”的进程。如此看来,陈白露人生悲剧的第二层因素便也昭然若揭——社会容忍不下她这种在“善”与“恶”之间游离的人,这又是社会悲剧。
三、“我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
曹禺曾明确表示,希望通过《日出》“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如此,如何构建与观众之间心照神交的“未来”,方达生便成了最重要的中介人物,成为一位“理想追逐者”,这主要包含三层体现:(1)方达生承载了左翼式的社会抗争。当方达生看清楚了旅馆众生相后,表达出抗争愿望,“我也许要跟金八打打交道,也许要为‘小东西跑跑,也许为小书记那一类人做点事,都难说。”(《日出》,272页)但同时将自己和“诗人”作区分:“我不会变成诗人,但我也许真会变成一个傻子”(《日出》,272页)。乍听之下,仿佛是方达生语无伦次的“呼号”,其实这一切是他有意而为之的“隐晦”。“诗人”是抛弃此处“黑暗”,另觅一处光明。而方达生确实留在原地和“黑暗”斗一斗,“日出”虽然不是他的,但却丝毫没有阻挠他抗争的心。(2)方达生照亮了陈白露人生最后的沉没。当剧末所有人都有一个预示“归宿”时,方达生仍未放弃对陈白露的救赎,他邀约陈白露“一齐做点事,跟金八拼一拼”(《日出》,331页),方达生已成功将个人感情上升为家国情怀,但陈白露却依旧在沉溺在个人不幸中。(3)他暗示了一个公正美好的未来。苦思冥想“太阳是谁的”(《日出》,92页)的方达生,临近剧终在小工们身上找到了答案,并“转过头去听窗外的夯歌,迎着阳光由中门昂首走出去”(《日出》,331页)。这一切那么顺其自然,又让人信心满满。而观众随着方达生的落幕,看到了一个公正美好的未來。
对照人物原型可以发现,这三层理想设置有的有现实依据,有的则出于曹禺妙笔生辉的虚构。第一层多有现实依据。20世纪30年代,曹禺在与友人的交流中耳濡目染地接受了“左翼”思想的熏陶:“那时我知道世界上存在一种追求光明的人,都是些好人。但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并不明白。”正是在这样“模糊”心境下,曹禺在创作《日出》时不知不觉地让方达生渲染上了“左翼”色彩。这是一种热烈色调,使方达生拥有了积极、热情的色彩。第三层,也可在现实中找到证据。曹禺是否真的对这个“时日曷丧”的社会万念俱灰,看不到未来呢?不尽然也。曹禺在《日出》前面附录一段圣经语录,用一个鸿蒙沆茫的世界暗喻了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然而他并不打算将这一鸿蒙之状停留在“浑噩”的层面上,因为他认为“人毕竟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于是他在将目光锁定东方之野,日出之处,描写日出以前的事情。之所以如此设定,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过着“日出”里的某一类生活,“忘记了有一种用了钱必须在‘鸡蛋里挑骨头的工作,不然连这一点点的希望都不容许呈现到我们眼前的”。而为了保护那些“有了阳光的人们”,曹禺便将主角置放在了背后。
以上两层均有原型参考,而第二层更多出于虚构。方达生照亮了陈白露的人生沉没,但靳以与曹禺不见得是王右家的“明灯”,因为王右家没有像陈白露那样沉沦。20世纪30年代的王右家,因罗隆基在学界、政界穿梭游弋,她的生活也因此多姿多彩,成为“通天教主”。靳以和曹禺若想用“左翼”思想去“暗示”王右家一个不存在的“穷途末路”,未免显得牵强附会,所以曹禺对此进行了虚构。
之所以这样改写,首先是因为陈白露形象的完成需要,作者希望透过追逐理想的方达生来表达“否定的美质”最终会毁灭的立场。陈白露的形象,在前面两幕刻画下,“否定的美质”也已经出现,在曲终人散之时,必须要给她一个满意的“句号”。曹禺曾说,“陈白露的死,是清清楚楚的”。换而言之,陈白露必须死,她的人物形象才得以完整,若她继续找了另外一片“森林”,则必然是另一个故事了。由此可推断,“理想”加持的方达生既不希望陈白露死,又“希望”陈白露死。所谓“不希望”,是基于方达生这一剧中人物的本意出发而考虑的。方达生爱着陈白露,他在最后看到未来,找到光明方向,他希望陈白露重拾信心跟他一起拼一下。而所谓“希望”并非说方达生激进地“谋杀”陈白露,怂恿她了结自己的生命,而是继承作者思想的方达生,认为陈白露必须“死”。这颇有几分“历史的必然要求”的韵味。此处的“历史必然性”,不是指历史发展的潮流趋势,而是“人们历史性的必然要求”,是恩格斯所说的: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方达生所代表的理想倾向,是左翼式的“末日”倾向。他深知陈白露如果继续与丢弃太阳的人为伍,哪怕她拥有掩护弱小的“美质”,也终将迎来自己末日。他对陈白露说:“你这么下去,一定是一条死路。”(《日出》,329页)此时对陈白露袒露心声的方达生,已经不是“琐碎的个人欲望”的劝说者,而是置身于时代洪流的代表着被压迫阶级的预言者。陈白露“否定的美质”被毁灭,除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外,还有“否定的美质”具备的“自毁”特性。“否定的美质”不同于被充分肯定的“美质”,它更多是作为反面人物的某种“恶行”的“护法”,这“护法”随着“恶行”逐渐暴露,又成了反面人物堕落的“催命符”。那么谁可以启动反面人物“否定的美质”的“自毁”呢?除了反面人物自身外,还要有正面人物推波助澜。《日出》中的方达生便充当着这样一种“催化功能”。众人眼中的陈白露是聪明的,但方达生却有着和他人不同的判断。别人认为陈白露的聪明是在交际圈中的“通行证”,但方达生却认为陈白露的聪明是她误终身的“毒药”。方达生的一句“你太聪明,你不肯做我这样的傻事”(《日出》,331页),直接为我们揭示了陈白露聪明这一“美质”的实质:陈白露的“聪明”,是她看得真切,她知道太阳不属于自己,自觉抗争无门,她便无力去抗争。她的死,有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意味。通过方达生之口,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景象,“聪明”的人死了,独留下了敢于和金八“拼一拼”的“傻子”。“否定的美质”终会被毁灭,而留下敢于斗争的人继续描绘美好未来。其次,方达生“理想追逐者”的人物设定,还是左翼写作对未来主义的需要。1909年,意大利作家马里内蒂以探索“未知”为己任的“未来主义”思潮横扫世界,产生广泛影响,其中这种“旧世界在我们的造反中灭亡,将以微笑去迎接新生活”的希望式的态度,
正是左翼人士对未来的核心期盼。《日出》中也隐匿了这三个关键词,曹禺借助方达生抒发了本人“左翼”的“未来主义”情怀。第一,作者借助方达生解答“太阳是谁的”的问题。方达生是全剧唯一能听懂“夯歌”潜台词的人。方达生对夯歌由最初的喜欢到最后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他觉醒之路的进阶。方达生对无产阶级的认可,实际上也是曹禺本人对无产阶级的偏爱,因为太多的不可言说,曹禺不得不将“拥有光明和生机”的人推到幕后,又担心说得过于隐晦而让观众觉得晦涩难懂。所幸的是方达生在剧中代替作者充当了思想向导,引出“日出”之后的社会主宰。第二,作者通过方达生预告旧社会毁灭。方达生一直与旧社会格格不入,他的言语中对旧社会满是厌弃。他对陈白露说的“一定是死路一条”(《日出》,329页),既有对陈白露的预言,也有曹禺对众人“日出”前的预言:“这是一个腐烂的阶层的崩溃,他们——不幸的黄省三、‘小东西、翠喜一类的人也做了无辜的牺牲——将沉沉地‘睡下去,随着黑夜消逝,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推演。”第三,作者通过方达生描绘了一个灿烂的世界。方达生曾对陈白露疾呼“外面是太阳,是春天”(《日出》,329页),他看到了腐烂生活的一线生机,“迎着阳光由中门昂首走出去”(《日出》,331页),随后夯歌响起,“屋内渐渐暗淡,窗外更加光明”(《日出》,331页)。人与布景的结合,表达出曹禺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而真使我油然而生起希望的还是那浩浩荡荡向前推进的呼声,象征伟大的将来蓬蓬勃勃的生命。”
四、结语
综上可见,《日出》对方达生“执爱者”“人道主义者”和“理想追逐者”的设置,未必完全合乎原型事实,但能较为客观地契合作家的内在心理。曹禺曾表示“方达生究竟与我有些休戚相关”,因此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方达生,常常有作者曹禺的影子与心声。同时,方达生作为作者的心理投射,代表着曹禺乃至“左翼”知识分子对时下时代问题所作出的回应,与时代问题有紧密对接。这为《日出》的经典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