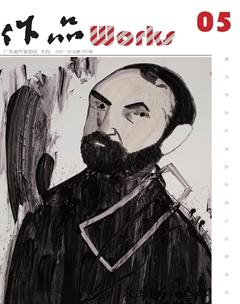老村旧屋往事(散文)
萧维民
乡村人居环境变迁,记录着农民的勤俭与坚忍,见证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题记
“五一”长假,妈妈翻出一叠旧红纸“日子书”——乡下建屋择日的单子,讲起当年祖父、父亲起屋的事,引得叔公叔婆们说了列祖列宗开基创业的许多艰辛故事来。
一
粤西萧氏始祖大鹏公,宋末官高州,流寓当地,后人屡次迁徙。元代中叶由高州迁吴川大寨村及廉江、电白、广西北流等地。明初,吴川大寨村又有迁北京、化州或廉江、电白随亲族而居者。明朝中叶,八世祖由大寨村迁山东村。萧氏一族频繁迁徙,不禁让后人思考究竟为何。
迁徙一般与户口赋税相关。《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10652870户60545812口,弘治四年(1491)、万历六年(1578)户口不增反减。美国学者何炳棣认为,洪武时数字接近事实,其后二百多年户口在6000万上下波动,是应付赋税隐漏户口的结果。《大明一统志》《广东通志》等记载,吴川天顺五年编户27里(每里110户),嘉靖三十九年(1560)2982户12833口,万历二十年(1592)3185户8570口,户数升而口数减。户均夏秋两税,洪武二十四年(1391)高州府3石,嘉靖三十九年吴川县3.1石;万历二十八年(1600)高州府6.29石,吴川县6.04石,另加各种税银高州府2.38两、吴川县2.03两,赋税上升。
先祖迁徙,大概是丁口日繁,居处逼仄,耕地不足,赋税渐重,只好另谋生路。七世祖惟昌公,大明景泰甲戌科孙贤榜三甲第一百六十三名进士及第,官户部山东清吏司主事,天顺八年致仕作《归里》:昔日同看上林花,出谷迁乔几岁华。飞倦归来寻旧隐,桑榆千亩乐生涯。“千亩”是虚言,但仕宦之家多占田地是实情,其他人远徙拓荒是不得已的选择。
山东村开基祖八世常荣公,字子青,号紫轩,邑禀生,进士公从子。进士公始编族谱,大明天顺丁丑科状元黎淳于天顺八年六月为族谱作序,进士公于成化五年作《修谱遗训》。子青甫《小引》:“谱之有文集,所以备稽考、示劝惩、广见闻也。然御制为朝廷纶音,故首列之以尊君父。其历代佳篇亦随采而载于后,以备考据之林云。”手工誊写族谱,颇费时间人力。大寨、山东两村道路不通,禀生公万难经常往返,故始迁当在谱成之后,最迟不过成化末年,禀生公41岁,率妻颜氏及三子三媳两孙迁居。
山东村是江心岛,木棉江由东北蜿蜒而来,先自北而南,再自东而西,转自南而北流去,三面环绕。村北水网密布,乡下称为“潦”(乡音读上声),村西有“江埒”,连通南边木棉江与北边潦,“江埒”隔着一片田野,便是转为南北流向的木棉江。岛上无山,“山东”之名,大概是刚修完族谱的禀生公,从萧氏由安徽萧县迁山东兰陵,再迁福建、广东的经历中取最辉煌的“兰陵世泽”历史,以祖居之地命名新村。
吴川曾七修《县志》,明万历《志》已佚,清六《志》俱存,均记大寨而未载山东村。《县志》载进士公进阶敕命:“奉天承运皇帝敕曰:户部司养民之政,其任匪轻,故置属详于诸部。苟非其人,曷称厥职?尔户部山东清吏司主事萧惟昌,发身贤科,擢任斯职,历年既久,式著忠勤,是用进尔阶承德郎,锡之敕命,以为尔荣。夫朕正治官以责庶务之实,尔益懋廉谨慎,用殝来效,毋怠朕命。其往钦哉!天顺八年七月十二日。”此道敕命原载族谱之《文集》,可见明万历二十八年始修县志时“县学生”曾到大寨村采访,自然知有族人迁居,但山东村处茫茫大江中,往来全靠舟楫。民国期间村民蜗居西南一隅,尚且高低凸凹,崎岖泥泞,始迁时必十分荒凉,“县学生”没到过就不足为奇了。
迁居不到廿年,甲子(1504)年六月八世妣颜氏卒,享年五十九;同年十二月九世时蔚公卒,得年三十七;次年七月禀生公卒,享年六十。《诗·大雅·文王之什》:“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冗,未有家室。”萧氏在山东村瓜瓞绵延五百多年,禀生公如古公亶父一般,率家人居彼小岛,何其不易!黄遵宪《台湾行》云: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
二
叔公叔婆们说,我家还有我没有见过的祖屋,是公祖婆祖(曾祖父母)所建,饱含着辛酸悲壮的故事。
公祖幼孤,随他的母亲依外祖生活,帮舅父们放牛干活,长大后才返回本村。生计艰难,公祖经常半夜到村西“江埒”摸鱼摸虾。有一个晚上没摸着多少鱼虾,好几次在江埒与木棉江接口处摸到一块石头,往旁边扔去,后又反复摸到,遂将石头恭恭敬敬地捧至木棉江岸边一棵榕树下,祈祷“保佑多摸几只鱼虾”,摸到不少后再祈祷“保佑我中几手‘花会(旧时一种赌博,类似现在‘买码)”。公祖连中多手“花会”,就买个小小的石香炉,在木棉江岸边的榕树下敬奉石头。
敬奉“石头公”后数年,公祖婆祖建了屋,坐北朝南,“一沓两臂”(一正厅两房两小房,正厅连着天井再接着门厅),但地不够,开不了正门向南,便开横门向东,东“臂”便成为门厅。
晚清以降、民国期间民风剽悍,经常械斗,我们村就因十八世祖葬地问题,每到清明节都与隔着“潦”的郭屋村打架。叔公们说,新中国成立前邻里纠纷也多,公祖常常见欺强邻。有一次,村里某老人被人扔砖块砸破头,他四个儿子说是公祖责罚爷爷而误伤的,就用“禾枪”(一种长约两米、两头尖的木制工具,用于插进大捆的柴火中挑走,也是旧时械斗之“械”)围困我家祖屋,逼索赔偿。幸得村里读书人培鲲力证公祖当时在他书房聊天,不可能伤人,方才作罢。这是祖屋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叔公们对此记忆很深。
爺爷娶奶奶,是祖屋办的一大喜事,而祖屋是爷爷奶奶婚事的关键。当初六舅公与培鲲的弟弟培钦是同学,知道我们家见欺强邻的事,对爷爷也有所了解,不大赞同奶奶许配给爷爷,奶奶的父亲认为“有这样一座屋,当也是勤俭积德之家”,做主同意。奶奶有嫁妆,最重要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书箱书篢”,长辈们至今还津津乐道。
山东村是“革命老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陈信材、李仕芬、潘乔棪等同志就到村里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在村里发展了3名党员,其中一名是公祖的叔叔。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员杨子儒、陈以铁(爷爷的襟兄)同志深入山东村发动群众。1943年2月日军侵占雷州半岛及广州湾,中共南路特委决定组织武装,展开游击战争。1944年12月下旬,广东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更名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第三大队成立,陈以铁为大队长,爷爷就随陈以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1945年1月,南路特委和张炎将军举行抗日起义。1945年2月24日,南路特委命令陈以铁进军茂西,3月4日陈大队到达木坑塘村,遭敌重兵包围,陈以铁被捕,4月16日下午被枪杀,头悬城门。爷爷侥幸逃脱,扮作哑巴挑着一担柴,一路走一路躲,或宿丛林,或睡墓穴,逃回山东村,然后逃亡外地,东躲西藏。国民党伪政府乡公所、联防大队隔三岔五来搜捕。公祖忧惧惊惶,1946年3月21日逝世。
农历戊子年年关,爷爷返家。除夕(1949年1月28日)晚上,伪联防大队顽兵迹至,爷爷从天井越墙而出,再次逃亡外地。爷爷的二弟不幸中弹殒命,婆祖被拘禁。大年初二,奶奶哭哭啼啼去梅菉找六舅公,六舅公出钱买了“薄箱”安葬死者,然后奶奶带着八岁的长子和两岁的长女回娘家避难。爷爷三弟十四岁、四弟十一岁,只好寄食他们的姐夫家。爷爷三弟跑去大寨村,求长老普昌、茂芝出面保释他们的母亲……
生活艰辛、苦难频作,让公祖婆祖将希望寄托冥冥虚空,虔诚祈求神灵保佑。公祖四子二女,一出生就拜“石头公”请“钱贯”求保佑。婆祖得过一场大病,在公祖向“太平堂老爷”(乡下称神祇为老爷)许愿后就好了。婆祖对祀神祭祖极为周到,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亦步亦趋。
婆祖极端节俭,“半斤豆腐下三位家先”(下家先,意为祭祖)。农历十二月初六、初七、初九是三位先祖祭日。初六那天,婆祖就买半斤豆腐煎好,外加三四条“羊婆鱼”(即“剥皮牛”,价格便宜),再摘点青菜,有三四个菜就是“崇盛帝”(非常丰盛的意思)了。傍晚祭拜后,婆祖就把常吃的咸菜拿上桌,那半斤豆腐就装入竹篮,吊上“二架梁”,人不敢偷吃,猫和老鼠也够不着,等过一天、再过两天,热一热再“下家先”,十二月初九祭祖后才吃掉。
婆祖辛勤操持,居然买了几块田地,1952年土地改革时被定为“地主”,43天后改为“中农”。那43天里,婆祖随时被人叫去干活,有个人嫌干得慢,用扁担打婆祖背脊,“阿母虽痛,却一声不哼”,八叔公说。那人几年后得麻风病,右手僵成“鹰爪手”,村里便有人说是报应。
土改后,面对家徒四壁,爷爷想尽办法,凭着错划地主补偿的50万旧币(当时一石谷7万元,一斤盐700元)重新创业。几年后六叔公、八叔公成了家,1960年兄弟分家,祖屋三家共住。爷爷奶奶住东房;六叔公将西房做了厨房,在东边另建茅屋一间;八叔公家住在西“小臂”,将厨房设在“小臂”门口与门厅之间。屋里两个厨房,没窗户,全靠天井通风,十分闷热。曾祖母没安身之所,就在厅里支个床,半夜起来,摸黑“搓索”(索,小麻绳)。“每天天亮起床,见到婆婆身边盘着一大堆‘索呢,我们‘搓索要么坐高架上让‘索垂下来,要么在空地上让‘索滚动远些,否则都搓不好,不知她又怎样搓得转?那时‘搓索还没有‘大腿皮(用旧轮胎切割出来的薄胶皮),婆婆长年累月在大腿上搓,腿上搓出一个深深的坑窝”,八叔婆说。
乙巳(1965)年十二月初五,“半斤豆腐下三位家先”前一天,婆祖在祖屋去世,如平常一般躺在厅里,只是不在床上,头不再朝南,而是躺在草席上,头朝北对着神龛,头顶和脚前各点一盏灯油——为老人家照亮前去的路。这是老祖屋办的最后一件大事,五年后爺爷兄弟便拆了祖屋,两位叔公在原址各占一半,建了新屋。
三
1950年6月,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在全省农林水会议上提出“以工代赈,堵口复堤,恢复生产,渡过灾荒”。随后,吴川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1950年新筑老巴山堤,1951年堵塞鉴江叉流木棉江口,1952年修筑三柏等六段堤岸,1954年修筑鉴江海堤、积美坝引水工程,1955年修吴阳防洪工程,1956年鉴西水利工程完工。
1951年冬天,堵塞木棉江口,灌渠截弯取直,新修的西干渠从山东村北边流过,经振文至黄坡入海。西干渠高于北边潦,也高于木棉江,“江埒”便由原由南流北改成由北流南。北边“潦”废弃为若干段,成为养鱼或蓄水的“塘”,江心岛成了半岛,后来又修路建桥,到我记事时已不觉得住在岛上。耕地之名有“潦头”“潦尾”“老鸦潦”之类,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改天换地的历史记忆。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指示:“现在我们准备在广东茂名(那里有油页岩)搞人造油,那也是重工业。”为解决用水问题,遂建设高州水库。高州、信宜、化州、电白、吴川县组织12万人,群众自带口粮,吃住在工地上。时值“大跃进”,群众焕发极高热情,“大雨避一避,小雨不停工,晴天加油干,北风当南风”,一个又一个竞赛,涌现一批又一批典型。“三芳(共产党员梁秀芳和共青团员丁运芳、冯莲芳)摆擂台”,引出“三妹”“三英”“五勇士”“五虎将”“十姐妹”等战斗小组来“打擂”。一时间“学三芳、赶三芳、超三芳”家喻户晓。爷爷是修水库的12万农民工之一,自带口粮,常吃不饱,就将“裹腰布”缠紧一点干活。轰轰烈烈的水利工程,让爷爷想到解决居住难题的妙招,盯上了“西头角”。
“西头角”是神奇的。土地低洼,蓁蓁莽莽,长满簕古、芦苇、狗尾草、天灯笼、地胆头以及不知名的杂草。几丛青翠的簕竹伴生在一棵樟木旁边,不远处还有一大一小两棵乌桕。叔公们小时候是不能到“西头角”玩的,因为地势极低,从村边下来有两米多的陡坡,一不小心就会摔着。而且故老相传,夜里常影影绰绰,时有硫火流萤,甚至听到什么声音又听不清楚。这片地里的老樟木,被采去造了“老会”的“老爷”,留下两句民谣——“山东老爷沙尾庙,上窦锣鼓下窦轿”,说的是几条村组成一个“老会”,共同敬奉一堂神祇,神像源自山东村,供奉在沙尾村庙里,出行巡游的轿与锣鼓道具存放在两条窦姓村庄。因为低洼和“不干净”,村里从没人想过在“西头角”起屋,爷爷曾出生入死,墓穴都躺过,怕什么“不干净”?连高州水库都可以建好,低洼又何妨呢?1960年分家后,爷爷便在“西头角”的西南边稍高处建起“三间(间,音jiǎn,三间即一厅两房)”泥砖茅屋。低洼地的落差苦了婆祖,她从老屋来新屋,得爬下两米多的陡坡。“婆祖用柴刀在木屐面上砍了三四道口子,这样爬下来就容易些” ,妈妈说。
建好茅屋后,爷爷便率领子女在“西头角”填土种树,种的是不用花钱又易生长的朴仔(学名黄槿树)、番桃(学名石榴)和簕竹。生产队要干活,爷爷、爸爸、姑姑就利用上午出工前、上下午之间的“工夹”、下午放工后以及春节放假时,到村边“沜”(滩涂地)挑泥来填“西头角”。屋地长宽各20多米,近500平方米,要填土数百立方米,泥土每立方米重2.3~2.8吨,滩涂湿泥还重些。“最初是爷爷、你爸爸和大姑姑挑,后来二姑姑、叔叔、三姑姑参加,我嫁来后也参加,一家子挑了十多年、填了十多年”,妈妈对我说。
爸爸早年告诉我这样的场景:大年初一,天色微明,薄雾氤氲,春寒料峭,鞭炮声三三两两,断断续续。爷爷、爸爸腰间束着“裹腰布”,一把大铲当扁担,挑着两个大畚箕,走向木棉江“沜”上取土,装满畚箕,沿村边坑坑洼洼的小路往回走,偶尔遇上大人小孩,互道一句“恭喜新年发大财哈!”天色大亮时,“西头角”茅屋门打开,叔叔和小姑姑从门口出来,一边揉着眼睛。大姑姑、二姑姑拿锄头,将卸在地上的一堆堆泥平推开来……
在爸爸不止一次的叙述中,我想起《愚公移山》“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山,箕畚运于渤海之尾”。
四
1970年一个上午,山东村“西头角”,阳光透过竹林照射下来,地上草儿还顶着露珠,竹木深处偶尔传来一声两声鸟鸣,清幽婉转。红的石榴花、黄的黄槿花都开了,随风散发着丝丝清香。小溪从西北蜿蜒流来,浅水汩汩流向村边田野。“西头角”斜坡还在,已不太陡,坡边几棵黄槿散漫地生长着,往西是那丛1934年曾生出竹籽又重新长起来的簕竹,绵延十多米,竹根盘缠处依然看出南北的地势落差。
“西头角”的东南处,一头黄牛牯双角用红绳挂着“红包”,牛驼峰套着牛轭和耙绳,爷爷左手执缰扶耙,右手扬鞭,“唏、唏、唏”地赶牛,就着建屋的四至,一圈圈地“耙屋地”——“西头角”不干净,就得耙干净,才大吉大利。耙过地,便“开墙路”,泥瓦匠在四角打小木桩,用线连成施工图样,爸爸他们就用锄头和铲沿着线挖出“墙路”。接着便“起手”——开始建屋。爷爷恭恭敬敬地递上红砖,“成行”(牵头的泥瓦匠)“二爹儿”将砖接过去,糊上灰浆,安放在东边正中的“章公”位,鸣炮——一小串炮仗,十来声——礼成。
这次建屋的故事,爸爸妈妈跟我讲过多次。大工三人,“三把泥刀”,要付钱的;小工便是我家人,邻居偶尔来帮忙,不用钱,将来人家建屋,我们去帮忙就行。屋北面是沿村小路,“成行”之外的两名大工争着砌这面墙,砌得好,一村人都能见到,就当广告。红砖不够,受力重的南北墙是“双而绵(双重墙)”;东西墙是“单而绵”,怕不够坚固,就将小竹子剖成两半,放在砖之间做“砖筋”。两堵间心墙是“红砖走脚”的泥砖墙,“走脚”用的是祖屋拆下来的草砖。即使这样,砖还不够,就向村支书借了一点,过后再还。
新屋是典型的“三间”,长9.36米,宽5.5米,斜坡式屋顶,屋脊引雨水前后分流,瓦面分39行(湛江地区传统的“三十九坑瓦”制式),中间厅两边房,结构简单实用。大门与厅相当的位置凹50厘米,建成门廊(乡下叫“凹墙”)。门廊两头角位各一个灰雕——一朵简单而传神的向日葵,这是我舅舅和他师父“二爹儿”的杰作。“万物生长靠太阳”,“一颗红心向着党”,形象的历史印记。
新屋在村里两个“第一”。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紅砖瓦房。我家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叔叔八个劳力,工分挣得多,爷爷统制收入,奶奶极端节俭,积下起屋的钱。二是村里第一座坐东朝西的屋,“西头角”填了一米多,仍低于南边,只能朝西,往前不足百米便是“江埒”,越过田野,就是南北流向的木棉江。
新屋建好一年后我出生,爸妈在老宅连生两姑娘,搬新屋立马就生个带把的,一家人异常高兴。1973年某日,外婆和她婶母士直六婆路过我家,六婆逗我说“外甥,阿婆来了,还不煲晏(煮午饭)?”两岁的小豆丁说:“饥荒时年,哪有晏吃?”当年8月,吴川刮台风,暴雨成灾,浸水稻146600亩,塌屋6005间,死伤若干人。木棉江排涝功能强大,山东村没伤人,但稻禾损失惨重,大人时常唉声叹气。多少年后六婆还笑话我,问“如今去你家可有晏吃?”
我上小学时,“西头角”周围渐渐建了房子,我家屋后成了戏场,屋前空地成了“大话馆”。盛夏初秋,月亮升起来,叔叔伯伯们吃过晚饭,陆续到来,爷爷早早摆好椅子凳子,准备“大碌竹”(水烟筒)。淡淡的月光下,好多人围着坐,那“大碌竹”在大人们手中转圈儿,轮流抽,一直“咕噜咕噜”着。孩子们呢,或绕着大人转来转去,或溜到旁边“捉鸡猫”(抓迷藏),或安静在听大人讲故事。常开讲的有两人,一位是沂昌四公,教念《人之初》和《天地玄黄》;另一位是沂和十公,常讲故事。有一次讲:古代有两个狐狸精变幻成美女,引诱一个男人养在洞里,称作“如意君”,大狐狸外出打食时小狐狸吃掉男人。十公背了一段狐狸姐姐与妹妹的对答:“如意君安乐否?”“窃以啖之矣。”十公翻译后,小屁孩们好几个晚上都不敢单独睡觉……
五
1972年夏秋两造都丰收,年关时爷爷将一担担稻谷粜了换钱,蒜头等明年开春值钱时再卖。爸爸考虑小孩多,怕明年收成不好要挨饿,建议先卖蒜头。爷爷不听,训斥“等你当家才有今年的粮食吃到明年”,1973年真的“饥荒时年无晏吃”。有一次下雨,年近不惑的爸爸建议趁大家有空煮顿饭吃,奶奶却认为既不劳动,喝粥就行。节俭的奶奶把一条“羊婆鱼”分三段煎,妈妈一顿喝六碗粥、吃两段鱼,奶奶就批评“大味”。过了几年,叔叔娶妻,婶子不好相处,爷爷掌管家族渐渐力不从心。
1978年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按手印,开启了农村改革进程。1980年吴川贯彻中央文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妈妈觉得,国家都分田到户了,我们也得分家。妈妈从来都听爸爸的话,唯独这次闹分家,是妈妈做的主,爸爸也默认。
最大的家产是两座同款的“三间”屋,“长子不离旧居”,爸爸得东南1970年建的屋,叔叔得西北刚建的屋。粮食和劳动工具等分为三份,爷爷、爸爸、叔叔各得一份,浮财留给爷爷奶奶。长孙应得些“着数”,当年爷爷与叔公分家,爸爸作为长孙分得老祖屋的大梁,这次就分给我。爷爷觉得少,加一只公鸡。
“分田到户”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双亲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干活,爸爸是村里几个“沤烂垌”(“垌”指田野,干农活就叫“出垌”,“沤烂垌”是长时间“沤”在田野劳动的意思)之一。我家没养牛,却耕六亩地,犁地时妈妈扶犁,爸爸和大姐拉,大姐出嫁后就是二姐拉;耙地时爸爸压耙,妈妈和大姐或二姐拉。我有时也参加拉耙,站在两根耙绳中间,反手抓住绳子中别着的小竹棍使劲拉。家里养一头母猪两头肉猪,妈妈每天吃过晚饭,就得熬明天的猪食,第二天天未亮起床喂猪,天亮就跟爸爸“出垌”,中午、晚饭都是边喂猪边吃。长期操劳,妈妈休息不够,眼睛得病,常莫名其妙地流泪。
分家时大姐在读中学,看着父母辛劳不堪,就辍学了。大姐看着村里人种藿香、圆椒,就说服爸爸种经济作物。爸担心种不好,大姐就打包票。大姐打听到藿香喜热喜湿怕雾重,也怕水多沤烂根,就将每畦的间距拉大,畦也起高些,天天早起担水淋,给藿香解雾。大姐一担一担地担水,飞快地在藿香地里窜来窜去,喷桶里的水洒在藿香苗上,再往下流,汇集到畦与畦之间的沟里。大姐裤腿卷得高高的,光脚板满是泥巴,一畦畦地淋,淋完天就亮了。大姐精心打理,我家藿香长得又高又壮,每次捡藿香叶去卖,蹲下来会淹没在藿香丛中,闷热难忍,汗流浃背。艳阳高照,大姐挑着满满一担藿香叶从地里回家,红扑扑的脸上渗着汗珠,身材高挑,步履轻盈,青春无敌……
天道酬勤。分家头一年,我家打的粮食就多,真实现了爷爷当年的气话——今年的粮食吃到明年。爸爸先用“风车”把秕谷除掉,拉最厚实的稻谷去交公粮,别人都笑他傻。蒜头丰收的时候,我们家厨房上边的“火熏架”太小,不得不分多次熏干蒜头,每次熏好一批,爸爸就爬上“火熏架”,将熏好的蒜头移下来,再装上新的蒜头,烧火去熏。一次两次三次,爸爸上上下下,那身上脸上便被烟灰弄得黑不溜秋的,一张嘴就露出一口白牙,让人忍俊不禁。有一年花生丰收,边拨边脱粒来不及,就白天先拨好,把花生苗铡断,留下根部和果实晚上再脱粒。爸爸把连根的果实堆在屋里时,大姐在门外大声叫,“爸,留条路儿进去拿筷子哈!”那时乡下压根没消毒碗柜之类的东西,筷子洗干净后就放在“箸笼”里,“箸笼”钉在墙上,爸爸堆花生的时候,把“箸笼”附近堆满了,姐姐就焦急提醒。这是我们家多少年都津津乐道的丰收故事……
六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爸爸就像他爷爷、我爷爷那样,面临着起屋的问题。1982年我考上中学,不愿再和爸爸挤在一张床上睡。爸爸便将房间顶上堆放柴火的“架”一分为二,里面一半放柴,外边一半用木板铺好,供我作睡觉和学习之所。窗户很小,不甚通风,闷热之极。每到夜晚,常常听到那半“架”柴火里老鼠“索索”走动或者吱吱叫,我就学猫叫,老鼠一下子就安静,然而一会儿又照旧热闹起来。而下边,是爸爸的呼噜声、弟弟的磨牙声,另一间房里患支气管炎的爷爷咳嗽声、吐痰声。夜间下雨,暴烈的雨点打在屋顶上,噼啪作响,大风吹过,呼呼有声,真如东林党“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为了起屋,爸爸妈妈一步一步打算,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分攒钱,分家第三年便“打砖”。“打砖”是技术活,爸爸请堂叔乾锦来帮助。先将耕地刨开一米多,去掉沃土,取深层有韧性的黄泥,几次三番地踩,把泥踩实踩柔软。踩好的泥高高堆着,边上是一个半身深的坑,坑前铺一块长木板,右边是一小堆沙。堂叔站在坑里,在木板上垫上底板,架上砖模,右手抓一把沙往砖模里撒,左手用“大泥弓”刮出一坨泥,两手搓实,用劲往砖模里拍打,“啪”的一声,再用“小泥弓”往砖模一刮,刮掉多余的泥,把砖模提起来,将底板往前推,一个砖就“打”好了。爸爸将湿砖连同底板,一块一块架起来,五块一起运走,到空地里放成一排排,抽走底板,形成空隙,以便晾晒。过两三天晒得半干,我和弟弟将每行中偶数砖抽出,斜着架在原来那行砖上,这叫“翘砖”。“翘”过后,一行砖便成了两层,上层斜着空,下层横着空,一行一行规则排列,煞是好看。一家子人在太阳底下忙碌着,挥汗如雨。堂叔在坑里打砖,“啪啪”有声;爸爸运砖晒砖,往返小跑;妈妈和两位姐姐在踩泥,左一脚右一脚;我和弟弟在“翘砖”,边“翘”边东张西望……三万块砖打好后,便去买煤来“烧砖窑”。这要很多人手,爸爸请村里人帮忙,好酒好饭招待,我第一次喝酒——菠萝啤,也酩酊大醉……
之后,每年攒一点钱,就买点沙、石灰、鋼材之类,1986年就建了新屋。那时,依旧是大工付钱,小工不用。“装模板倒楼面”,工程量大,时间紧,人工多,请邻里要给钱。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了嘛。
新屋坐落“西头角”东北、1970年建的“三间”屋右边。坐东向西,长宽各9.36米(含阳台1.2米),中间是长长的厅,两边各有一大一小两个房,北边两个房的中间是楼梯,因此北小房便凸出,占了阳台位。这样“一沓两臂”是改革开放后对传统“三间”制式的改良,厅房的大小基本没变,没天井,有阳台,每个房都开窗。传统“三间”制式只盖一层,新式可建若干层,但我家钱不够,就只建一层,外墙和屋里也不批灰砂,不装房门,挂个门帘。妈妈想让爸爸借点钱再建一层,夏天可少点闷热。爸爸说,两个儿子在念书,不应使过头钱,否则交学费不及时,影响读书学习呀!
“入伙”那天是农历十二月廿五。早上八点,新屋开着电灯,厅正中间“五方五土龙神之位”点着长明油灯。爸爸、妈妈、二姐(大姐已出嫁)、我、弟弟,每个人手提着一个红塑料袋,装着两盒红纸包的“糕”,鱼贯进入新屋。爸爸带着我们,先在大厅转一圈,往正中“章公”位的香炉里点上三支香,再在南大房、北大房、南小房、北小房都转一圈,每到一个房间就点亮放在桌上的煤油灯。场面充满仪式感,二姐却觉得滑稽,每转到拐角处,就冲我抿嘴微笑,弄得我想笑又不敢笑出声来,硬生生憋住。转完圈,爸爸指挥我们搬东西进宅,妈妈到厨房点火,煮糖水吃,便是礼成。奶奶备好“三牲”祭品和香茶宝蜡,让爸爸去木棉江边拜“石头公”。爷爷准备宴请亲朋……
那张旧红纸“日子书”,工整地记录着起屋过程:
福宅坐东向西甲庚兼卯酉
宅父辛酉年十一月廿四子时
宅母乙未年七月廿六日子时
宅主庚辰年十月初八日戌时
宅相癸未年十月初五日亥时
男辛亥年八月廿四日子时
男甲寅年正月廿六日申时
女戊申年正月廿二日亥时
平基开墙路择丙寅年八月廿四日辰时动工大吉
行墙砌砖择丙寅年八月廿五日辰时仝时采梁头指东西方大吉
安门择本年九月初二日巳时大吉
进人入火择本年十二月廿五日辰时仝时作灶点火煮食顺利
七
1990年8月,爸爸在新屋举办了他有生之年最大的宴席,共十三桌,又给全村放电影两晚,因为长子上大学了。爸妈从不惜力,无论大小事情都愿为邻里帮工帮忙,因此办酒席时来的人很多,十三桌坐不下,一些亲人便挤在一起随便吃,不讲究上席礼节了。
1995年3月祖父大去,1997年1月父亲驾鹤。祖父和父亲去世后,妈妈与奶奶相依为命,照顾奶奶极为周到。奶奶一次起夜,摔断了股骨颈,要换人造骨,妈妈衣不解带地服侍。奶奶换骨后,长时间不敢下地走路,又自认大限将至,执意住旧“三间屋”,妈妈常三更半夜起床,到旧屋照顾奶奶。后来,奶奶又患老年痴呆,不认得人了,还动不动就骂人,妈妈无怨无悔地服侍,直到2012年10月奶奶94岁去世。一向迷信的妈妈说,老太太高寿,骂人的话都会变成福报的。
1998年,我与弟弟举债将新屋加建一层,好让高堂少受暑热之苦。2003年再稍加装修,用围墙将两座屋连起,起名“厚园”,以纪念祖父父亲的遗德遗教。这两次修建,大工、小工都得给钱。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交换意识已经深入到农村了。
八
解放如东风吹醒中华大地,改革开放如春风绿了人间。人居环境不断改造,民生不断改善,山东村繁衍生息,与国咸休。1949年吴川人口31.2万,山东村不足300人,占0.09%;1990年全县人口76.5万,山东村1100人,占0.14%;目前全县人口129.9万,山东村2100多人,占0.16%。父老乡亲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新房子越建越多,村边由西北流来的小溪,一而再地往北移,成了由西流东,从我家到小溪之间,整整齐齐地建成十几排新房子,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的都有,高高低低错落村边,如同奏响新时代新农村的新乐章。
“五一”节清晨,晨曦初露,凉风习习,我信步走上天台,远眺那片高低错落的房子。忽然想,我家“西头角”东南“三间”屋,像祖父穿著加贝短衣,留着山羊胡子,背着双手,伫立在黄槿树下;东北“一沓两臂”屋,像父亲穿着简式中山装(“农民装”),手握锄头,准备“出垌”;西北是堂弟前年新建的两层小楼,新式“两间式别墅”——厅在左边,房在右边,设有厕所——还没装修,像堂弟身穿打工仔的“单吊西”,还有点慵懒式的褶皱。这如同农村房屋博物馆,形象记录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村的发展呀!
傍晚,我和弟弟在村中溜达,村道巷道都平坦整洁。近年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里开展“厕所革命”,收集生活垃圾,提升村容村貌,初见成效。往村南木棉江走,水很浅,河道已不足十米,“沜”上建起一排排房子,又占河道修了环村路。顺着环村路往北绕,便是1951年堵塞木棉江口截弯取直而成的西干渠,堤高了,水很满。隔江望去,“垌”里一望无际的水稻,在夕阳下随风摇曳,如绵长的地毯,亦如微澜的海面,“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列祖列宗的老村,生我养我的旧屋,一代代生生不息,一天天辛勤劳作,一茬茬填地起屋,一段段奋斗故事,从“有得住”到“住得好”,如同换了人间。乡村振兴了,生活越来越好了,乡亲父老会继续改善人居环境,把农村建设得更美,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田园乡愁。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