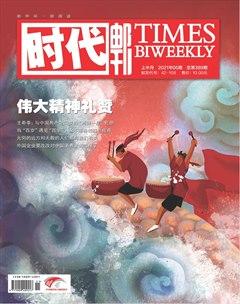中国超级小镇的“兴”与“新”
张隆锋

在全球视野里,“中国小镇”一直是一种神秘又可怕的存在。
几个冷知识——日本90%的棺材都生产于山东菏泽,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假发都来自河南许昌。从长三角地区到珠三角地区,像这样所产商品覆盖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乡镇和小城,中国还有几百个。
在2021年全国两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里,国家进一步强调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乡镇产业里,其实蕴藏着许多机遇。
在上个十年,一代人拼搏奋斗打响了“超级小镇”的名声,而要让小镇产业更适应时代变化,还得靠新一代的力量。至少未来五年,乡镇崛起将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大城市“内卷”激烈、人满为患,小城镇人口流失、生产力不足,在“事少离家近”和“钱多福报多”之间能不能有个平衡?
紧贴超级小镇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小镇的财富密码
上世纪90年代掀起了“下海潮”,很多人走南闯北,去石狮批发服装,去温州批发皮鞋,去义乌购进饰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小镇产业约等于“中国制造”。
在这里,“小镇产业”中的“小镇”只是一种泛指。其实,小到村落,大到地级市,很多地方产业都有很高的相似性——一个村只做一种买卖,一个镇主打一种产业。
这种模式在区域经济学里被称作“同乡同业”。举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福建东部有不少小镇很流行生产打火机的点火器,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在干。“帮奶奶数当天到底做了多少点火器”甚至是许多福建人的童年回忆。
当然,生产点火器还是小规模产业。真正的产业集群还要看晋江,比如大家所熟知的361度、安踏、特步等品牌,其背后的老板都姓丁,多少都有点沾亲带故。同为运动品牌,这些晋江特产似乎更能体现国货力量。
发展到现在,这些超级小镇,一个镇上能出三四家上市公司,更厉害的像佛山的北滘镇,一个镇就有14家上市公司,直接把当地新房均价炒到22000元/米2。
别看它们现在这么风光,在过去,这些小镇也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方。穷则思变,变则通,许多人觉得南方人会做生意是天资,其实很多南方人是受環境和生活所迫,不得不往外走。
拿义乌举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有这样一个关于义乌小镇的片段:在早期,义乌人用手工红糖,到每家每户换鸡毛、鸭毛等废旧物品,再去收购站将废旧物品换成钞票。“低买高卖”的技巧,义乌人民早在四五十年前就玩得得心应手。
小镇人民懂利益交换,更懂人情往来。但是,在那个“倒爷遍地有,做事没什么规则可言”的年代,乡镇百姓做生意最信赖的还是同乡。
同乡关系比什么都靠谱,说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点——方言,这就不是外地人能够随意“插手”的。
也许有人曾注意到,在学校附近开打印店的,通常是一对南方夫妻,再一问,他们十有八九来自湖南新化。他们基本都使用家乡话交流,方言就是他们的商业密语。怎么定价,怎么采购机器,外乡人想从中窃取信息基本不可能。
新化人最开始开打印店是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小批新化人到处跑江湖、修理打字机,结果无意间发现了台湾有大量来自美国的旧复印机可以引进。在当时,进口一台全新复印机要花上十几万元,但购买二手复印机只要几千块,而二手机器经修修补补后一样能用。看到商机后,新化同乡之间通过师徒关系传承修理手艺,也传递二手机器购买和开店选址等重要信息。
赚钱的生意,其他地方的人当然也想做,有的人就常在打印店附近徘徊,探听开店技巧。但凭着方言这堵高墙,最终只有新化人才能掌握开店的核心设备来源与经营诀窍,他们也渐渐垄断了全国的文印生意。
以前,很多媒体上会有一类专门的报道叫做“商业地理”,专门探寻全国各类小镇产业,包括胶囊小镇、拉链小镇、情趣内衣小镇等,无奇不有。
超级小镇的生意,沿着地缘的脉络在中国地图上一点点开枝散叶。
小镇光环褪色,危机袭来
掌握了“同乡同业”财富密码的超级小镇在当年风光无限,但近几年,它们身上的光环却渐渐消褪下来。
如今颇具热度的话题,不是薇娅、李佳琦等头部带货主播,就是微商、外卖、电商这类新的商业模式,这毫无疑问给原本风光的超级小镇带来了极大冲击——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是不行了,还得爬起来紧跟潮流。
要说当年超级小镇中的“顶流”,还得数义乌,不过,现下的义乌也正在转型的泥潭中挣扎。
如今,“宇宙小商品批发中心”义乌还有个直播村——北下朱。村子不大,花20分钟就能走路绕一圈,但在鼎盛时期,村里最多同时容纳了将近20000个电商从业者。在2020年,他们仅靠直播就为义乌创造了200多亿元的收入。
即便如此,直播也没能真正带动义乌的整体产业转型。在义乌做电商的人多是外来淘金者,许多义乌本地人并不为直播带货所触动。毕竟,义乌曾创下3000多亿元的年进出口总值,相比较而言,200亿元的直播生意似乎也没那么有吸引力。要让经历过大风大浪、挣过大钱的义乌人换一种逻辑重新开始,这似乎有些困难。
义乌的转型困难,也是中国超级小镇普遍面临的问题。上个十年,它们已经完成了“从0到100”的进化,但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又是另一重挑战。
如果说义乌面临的挑战,是“同乡同业”影响下的个体户该如何突破传统思路、适应新时代,那么“快递之乡”桐庐则正在经历一种不同的、“产业做大”后的烦恼——同行人生意靠得太近,也会互拖后腿。
桐庐距离义乌只有80多公里,这个小县城是圆通、申通、中通、韵达共同的发源地,“三通一达”有个共同的老大哥——聂腾飞。
邓小平南巡之后,外贸生意火爆。1993年,桐庐人聂腾飞无意中获知,许多杭州的外贸企业无法把报关单次日送达上海。发现了这个痛点后,聂腾飞赶着凌晨2点的绿皮火车,做起了派送报关单的生意,他很快便成立了“神通综合服务部”,也就是申通快递的前身。
桐庐的快递生意也因此开始裂变式扩张。在聂腾飞的老家夏塘村,全村约650人,有400多人在从事快递行业,几乎做到了全员上阵。其中,飞升最快的还要数聂腾飞的亲友们,聂腾飞的弟弟、妻子、大舅子、大舅子的同学的丈夫等一批桐庐老乡,陆续创办了韵达、圆通、中通、天天(已被申通收购)等快递企业。“桐庐帮”几乎占据了快递业的半壁江山。
然而,“桐庐帮”的快递帝国看似铁板一块,实际上内部充满了暗算与较量。超级小镇做到了极致,但内斗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乡情被利益冲淡,小镇等待下一个跳板
“三通一达”虽然来自同处,但生意做大之后,原本“抱团”的同乡之间渐生嫌隙,乡情只得给利益让位,较量带来的直观后果就是——快递小哥都懒得把快递送上门了。
为了抢占市场,“三通一达”之间大打价格战。从2021年1月份的快递行业数据来看,韵达、申通、圆通单票收入下降幅度都高达20%左右。干一票快递,只能收個2.5元不到,而顺丰的单票收入是它们的将近8倍。
某快递公司的高管曾透露,别的快递公司都希望能够共同涨价,但互相掐着脖子的“三通一达”,谁都不想先松手,最后的结果自然就是谁都涨不成价。
不涨价,听着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但快递行业终归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压价首先压的就是快递小哥的收入——收入被削减了,还怎么保证提供更好的服务呢?谁还愿意送货上门呢?
再看看“三通一达”的老对手——顺丰和京东物流,它们的时间和精力大多投入在冷链运输、物联网等科技含量较高的领域,这样一对比,“桐庐帮”的快递事业似乎都差了点格局。
回过头来看,“桐庐帮”的崛起,完全可以算是“同乡同业”现象里的终极形态。然而,再强大的乡土社会,大概都难以与“资本巨无霸”匹敌。现代商业社会与老派商帮文明的摩擦,是时代高速发展下的独特景观。
尽管“三通一达”毛病不少,桐庐这个小县城却吃到了快递产业的红利。因为快递产业,桐庐的发展已今非昔比,2020年5月,“三通一达”抱团回归桐庐,与顺丰共同打造了国内首个快递物流装备物资集中采购中心,不到一年就实现了101.53亿元的交易额,这是过去靠经营传统产业发家的桐庐人无法想象的成绩。
在新的十年,超级小镇的传说再难复制,“同乡同业”的老路也很难走得通,“鸡毛换糖”的传说在互联网世界里已经难觅踪迹。但靠勤劳与智慧致富,在任何年代都可行,问题只在于如何抓住时代的机遇。2020年8月,一个义乌的95后“厂二代”返乡创业,卖拖把卖到行业第一,这在他的父母辈们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回乡发展,年轻人创业有想法、有激情,但就是缺资源和实操经验,而这和小镇经济刚好形成互补——小镇不会消失,它们只是在等待迭代,变得更高、更快、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