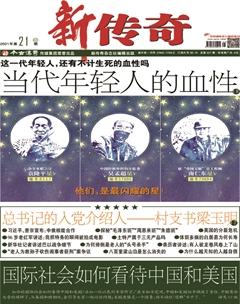八百里梁山泊是怎么消失的
公元1344年,黄河再次决口。在元代水利专家贾鲁的治理下,河道重新南流入海,湖泽彻底干涸成陆地,梁山泊最后只剩下泥沙了。由于土壤极为肥沃,人们迅速来此定居开垦,断绝了此地再变成水域的可能性。
对于水泊梁山,人们的认识大多来自小说及影视剧《水浒传》。当年,宋江等众好汉被逼上梁山,凭借八百里水泊天险啸聚梁山,演绎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那么,在历史上,梁山是否真的那么壮观?
曾经宽阔无边的大野泽
梁山,也名良山,在古代属济州地界。济州治所位于巨野县,“巨野”才真正关系到梁山的地理面貌。“巨野”本称为“大野泽”,据《左传》记载,鲁哀公曾来此狩猎,证明这里起初是水草丰美、野兽聚集的地方。后来,汉朝设置巨野县,“巨野”这个名称就一直传到了现在。
那么大野泽是如何形成的?据《禹贡》记载,其为平原积水而成,这离不开黄河及其支流的输入。东汉水利专家王景通过将黄河与汴河分流,保证了当地济水的通畅,向北东流入大野泽,最后入海。除了济水,还有濮水、洪水、汶水等支流,使得大野泽极为广袤,成为河网纵横的地带。
大野泽水路交通便捷,在战乱频仍的魏晋时代得到充分利用。公元369年,东晋的桓温北伐前燕,命人在此开凿了一条300多里的运河,后世称之为“桓公沟”。这条运河把泗水和大野泽挖通,军队就能进入黄河。
梁山泊的形成与“八百里”的说法
最初,梁山并没有被水域环绕,只是一座平平无奇的山。它被称为“梁山泊”,与黄河在唐宋时的频繁决口密切相关。王景治水后,黄河总体上维持了几百年的平稳。直到唐末,决口重新频繁起来。黄河泛滥必然携带大量泥沙,导致大野泽的位置不断南移,最终移到了梁山脚下。
五代十国时,各个政权为了争夺天下,多次人为决堤,加剧了黄河的不稳定性。公元944年,黄河在滑州处决口,波及汴、曹、濮、单、郓五州,洪水“环梁山,合于汶水”,“梁山泊”实质上已经形成。
据《资治通鉴》记载:“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发畿内及滑、亳丁夫数千以供其役。”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五丈河(广济河)的疏浚,使得济水与梁山泊相通。同时,梁山泊在漕运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然而,即使宋朝结束了中原的战乱,黄河水患仍然变本加厉,梁山泊也不可避免地充当了黄河的泄洪区。
至于“八百里”的说法则发生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当时,王安石想要兴修水利,有小人进言:“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这个建议十分荒唐,会从根本上改变居民的生活习惯,在朝中也引起了争议。苏辙还特意写了诗进行讽刺,诗中自注“时议者将干此泊以种菽麦”。
苏辙的讽刺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士大夫们看来,梁山泊是一个盗匪遍布的地方,最早可以追溯到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彭越。受五代以来黄河频繁决口的影响,当地百姓的生活环境要恶劣许多,民风也普遍彪悍。北宋大臣陈师道曾提到,这里的青壮年很多都不从事农业生产,热衷于饮酒作乐,喜好拦路抢劫。所以,朝廷常常派遣武官治理,监狱里人满为患,曹州、濮州被称为“盗区”。
北宋末年,宋徽宗昏庸且不理政事,大权旁落。宦官杨戬将梁山泊绵亘数百里的水域全部收归于掌管公田的“西城所”,百姓凡捕鱼、割蒲草都要依船只大小交税,违反者按盗贼论处,哪怕有水旱灾害也不进行豁免。当地本就民不聊生,杨戬这种与民争利的举措无异于雪上加霜。梁山泊内河道纵横、港汊交错,无法维持生计的农民、渔民以及藏匿于此的盗匪,逐渐形成了对抗朝廷的武装力量,宋江起义就是其中最有名的。
不过,现实中的宋江起义远没有发展到《水浒传》中所说的那样。首先,宋江是来自淮南的盗匪,流窜到了梁山泊。其次,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宋江一伙在梁山站稳了脚跟。相反,他们一直在流窜。再次,起义者起初只有36人。虽然他们一度攻陷10余座县城,但最后还是被张叔夜率军剿灭了。
夺淮入海与梁山泊的消亡
金灭北宋后,黄河仍然频繁决口。其中,公元1168年,李固渡决口导致黄河下游发生了分叉,新河道夺淮入海,旧河道反而成为了支流。12年后,旧河道完全断流,梁山泊彻底失去了水源,就此走向消亡。
水域萎缩后,取而代之的是大片良田,金世宗就要求地方官员安置百姓屯田。百姓之前已经有自发开垦的行为,但是害怕被朝廷征租导致逃亡者很多。为了巩固统治,金世宗决定免除他们的租税。
到了公元1310年,河北、河南道廉访司在给元武宗的奏折中明确指出开垦的隐患,黄河反复无常,一旦再改道回来,还需要梁山泊作为泄洪区,如果不早作准备,曹、濮、济、郓等州必然会再遭水害。只是人们已经在此繁衍生息形成村镇,怎么可能再让他们退耕还湖呢?这一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公元1344年,黄河再次决口,由此引发了农民起义。
也正是在这次决口后,梁山泊宣告完全消亡。有许多著作记载,决口期间,河水曾短暂淹没过巨野。但在元代水利专家贾鲁的治理下,河道重新南流入海,湖泽彻底干涸成陆地,梁山泊最后只剩下泥沙了。清初史地学家顾炎武在巨野、寿张等地游历时,曾感慨地说:“古时潴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他还嘲笑了寿张县县令的无知,因为县令在修志中认为梁山泊不过方圆十里,“八百里”的说法是骗人的。由此可见,曾经的梁山泊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综上所述,梁山曾经拥有八百里水泊,这绝非施耐庵空言。梁山泊干涸后的土壤极为肥沃,人们迅速来此定居开垦,断绝了此地再变成水域的可能性。如今的梁山其实还是回归了本貌,可谓沧海桑田。
(《大河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