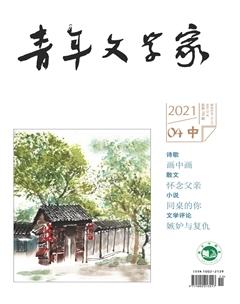困境与超越:《城堡》和《围城》的空间叙述
周苏涵
空间叙述是《城堡》和《围城》共同的写作手法:事不关己、尔虞我诈的社会空间显现出现代人被悬置、被压迫的命运;麻木不仁、缺乏沟通的精神空间导致个体一度被排挤在生存边缘,所有人都是孤独的存在。主人公的空间困境不仅是客观世界的外在反映,更是作家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探索反思。本文以《城堡》和《围城》为分析对象,通过对文本空间符号的解读,探讨其指向的生存困境,从而探寻超越的可能。
《城堡》是卡夫卡的遗作,讲述了一个土地测量员费尽心思进入城堡却无果的故事,它象征着一个无法进入的代表权力机制的物理空间,也映射了人类无法突破精神困境的心理空间。《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主要描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像,其中也有多种空间的叙述,它们映射了人生的困境、人性的弱点。不论是《围城》中的方鸿渐,还是《城堡》中的K,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然而结果却是“从某一点开始,便不复存在退路”,一旦开始追寻,便注定要体验一场落空,甚至连退路都没有,而这种困境带有普遍性的意义。笔者拟从两部作品的文本空间进行解读,通过社会空间、情感空间、空间境遇、后世借鉴意义这四个方面的比较研究,了解作品的文本含义和深层寓意,从而对人类的生存困境有一个更理性的判断与体悟,并进一步探寻超越的可能。
在文学空间领域,布朗肖提出“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返回到深刻的存在”,他认为文学空间不再仅仅是现实世界物理空间的再现,而是一种生存体验的空间,其生成来自于作家生存的内心体验,触及到人类内心的深层感知。“文学作品中的场景环境描写,并不是客观物理空间或地理空间的简单机械式再现,其中渗透着人们对于空间的理性规划和社会历史性理解”,象征场景是小说空间叙述的特征之一,通过解读上述两部作品的空间场景,主人公的生存困境得以具象地呈现,其指向的是人类的生存困境。
一、“拒人千里”的社会空间
《城堡》中,“城堡”这一空间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涵:作为改写人物命运的权力机关,它神秘而冷漠,影射了现代人类可望不可即的空间存在。小说中,主人公K并未被城堡聘用,却被城堡认可了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当他找到自己的顶头上司——村长时,却被告知自己并不被需要。面对村民的冷漠,K没有放弃留在当地的诉求,而是积极探求进入城堡的方法,然而,K越是努力,距城堡却越来越远。为达成目的,K企图接近掌握任职权力的城堡官员克拉姆,甚至不惜勾引克拉姆的情人弗丽达。然而,在K与弗丽达共享爱欲的那一刻起,弗丽达与克拉姆之间的纽带早已切断,K企图通过弗丽达联系克拉姆的计划就此泡汤。后来,K又将希望寄托于信使巴纳巴斯,而巴纳巴斯只是个不被重视、日复一日等待工作的闲散职員,经过漫长等待,K只收到了两封来自克拉姆的非正式的慰问信件。更为荒谬的是,在他还未真正实行土地测量员的职责前,信件就表示了对K辛勤工作的嘉奖,并且那些信件本身也存在问题,似乎是从一堆发黄的旧档案里随机抽出来的。而随着K与巴纳巴斯一家的深入交往,K逐渐发现了“城堡权力运作的秘密”,并因为他与这个家庭的密切联系,村民对K的成见愈加强烈,甚至连弗丽达都开始反感K的所作所为,并且在最后与K分手,重新回到了酒馆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顶头上司村长、酒馆老板娘、学校教师等其他村民的排外行径,更是让K的境遇雪上加霜。
面对村民和城堡相结合的坚固壁垒,K的积极进取反而使他距离“山坡的圣地”愈加遥远,社会地位一再被悬置、孤立。正如布罗德所言:“他是个异乡人,碰巧来到一个对异乡人抱有猜疑的村庄,没有做更多的交代;然而人们很快就感到这种几乎带有普遍性的‘身居异乡的心情在一种非常特定的情况下变得具体化了,‘谁都不是谁的同伴。”
《围城》中,方鸿渐辗转于各个职场空间,但每一次“出逃”都未能称心如意,反而使得方鸿渐的精神世界不断萎缩。因与周家夫妇日渐隔阂,方鸿渐辞去银行的工作,将职场的期望寄予内地,可刚到三闾大学,“我愿意请先生来当政治系的教授,因为先生是辛楣介绍的,说先生是留德的博士,可是先生自己开来的履历上并没有学位——并且不是学政治的”,面对校长高松年的文凭质疑,方鸿渐自知学历是假,只好忍气吞声,委身降职。然而,这仅仅是方鸿渐任职生涯的一个小坎。随着教学生涯地不断深入,方鸿渐逐渐发现三闾大学的另一副面孔:校长高松年看似通情达理,实乃酒色之徒;汪处厚老奸巨猾,官僚风气残余浓厚;顾尔谦、陆子潇等人一心飞黄腾达,爱耍小手段。最为讽刺的是,他发现韩学愈同是出自克莱登大学,他却招摇撞骗、“大摇大摆”,甚至当上了历史系主任。由于没有收到下一年的任职聘书,方鸿渐又折回上海任职。虽然能力不足,但他却心气颇高,意气用事下辞去了报馆的工作,从此生活再无收入,还需要靠孙柔嘉补贴家用。在收到赵辛楣的回信后,方鸿渐又打算重返内地,在那谋一份生计,“可是他也一步步高上去,自己要仰攀他,不比从前那样分庭抗礼了”,由此,方鸿渐的未来走向又一次陷入了漂浮与悬置。
不论是周家银行、三闾大学,还是报馆,“封闭”的职场空间使得人的嫉妒心理和权力欲望充分展现,方鸿渐拥有应对人情世故的敏锐触觉,却缺乏处理社会关系的勇气和能力,一度被排挤在生存空间的边缘。
二、“视同陌路”的精神空间
“空间生产压抑了人性,将人变成麻木冷漠的人。”作为构建城堡权力结构的基层人员,城堡的村民长期处于情感荒芜、缺乏沟通的精神空间。小说中,村民谨小慎微,胆怯怕事,他们不敢大声交流或成群结队,常常用惶恐的眼神盯着K,深怕K或自己触犯哪条不成文的法律法规。在对现有秩序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村民还忠实维护着克拉姆的绝对权威:他们不惜孤立阿玛丽亚一家,导致全村最好的鞋匠没有生意、失去了当消防员的资格。尽管城堡没有采取任何谴责或惩罚的措施,阿玛丽亚一家却不得不四处求助,恳求城堡的饶恕,为了能找到城堡官员的跟班,奥尔加不惜跑到客栈,委身于卑贱的仆役……而起因仅仅是因为阿玛丽亚拒绝当克拉姆的情人。从朝气蓬勃到身心俱疲,阿玛丽亚一家的遭遇似乎是K追寻之路的“镜像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