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医古典目录学概论》
孙天胜 王逢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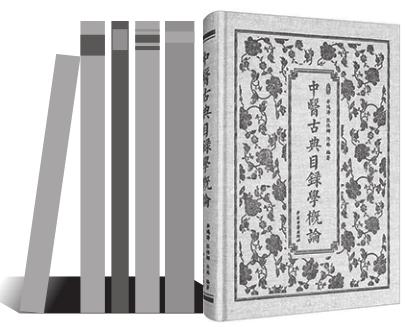
目录是连接文献与学术的重要桥梁,不仅可以反映历代文献之繁衍、学术之兴替,还可以指导治学门径,启迪治学思路。在中医文献数千年的传承中,中医古典目录学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和任务。
我国是世界上目录学起源与创建最早的国家,目录学是传统学术治学的重要门径和方法。两千多年来,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料。但这样一门重要的方法与实践并重的学科,多少年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用,实在是中医学术的一大损失。
值得庆幸的是,由中国中医科学院李鸿涛、张伟娜、佟林三位学者编著的一部30多万字的《中医古典目录学概论》,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了。
该书以中医古典目录学的基本知识、学科方法和实践应用为纲,以中医典籍为例证,围绕古典目录学所涉及的著录、分类与提要等基本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关键问题,通过揭示目录学在中医文献传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引导学人自觉运用目录、整理文献、发掘学术,进而推动中医药学的传承与弘扬。有“述”有“作”,授人以渔,实在可喜可贺。
中医古籍,是指古代抄写或刊印的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一般指辛亥革命(1911年)之前的历代写本、刻本、稿本、拓本、抄本、活字印本等。主要包括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内、外、妇、儿、眼、鼻、喉、口齿等)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综合性著作等,而且每大类又可以细分为许多小类。与其他古籍相比,中医古籍存世数量众多、收录散杂,内容丰富、门类体裁多样,传承版本繁杂,讹误较多。
由于中医古籍专业性和实用性较强,故导致长期以来抄写本多于刻印本、坊刻本多于官刻本,经典名著翻刻多于个人专著刊印,并且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辗转传抄与多次翻刻,或误写,或承前人之误,或为校订人删改,易失原貌。因此,难免以讹传讹,在内容和文字上存在着讹、漏、倒、衍等现象。萧延平在《兰陵堂校刊医书三种 黄帝内经太素·例言》中言:“自来校书,苦无善本,医书尤甚。”主要是因为科举兴起之后,士人们为了步入仕途,多趋重辞章声律之文,对医学则鄙视为方技而不屑于去研究。结果最后导致的就是“晦盲否塞,几近千年,纰谬纠纷,问津无路”。分类的目的,是为了让学者更好地根据书目的性质去应用目录,开展研究工作。
世界上如果只有三本书,是用不着目录学的。可从两汉至今两千余年,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各类文献约18万种,而1949年以前的中医文献已达万余种。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还有大批中医古籍流传海外。没有目录学,我们后人该如何是好?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献给世界人民健康的厚礼。两千多年来,世代相传,生生不息。歷代医家通过著书立说,将医疗实践中获取的理论总结、技术方法、经验体会诉诸文字,传播于后世。这些历经千百年积累下来的中医古籍,是真正的知识宝库、信息宝库、文化宝库,既是中医学术的重要载体,又是医药科技创新的不竭来源。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其发展水平与成就远远超过了同时期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国家。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撰《别录》《七略》,奠定了系统分类目录学的发展基础,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刘歆在我国最早的一步综合性分类目录《七略》中,即设有“医经”“经方”两个医学专科类目。
目录是揭示文献的重要工具,为治传统学术者所必须学习和深究的一门学问。古往今来,历代鸿儒巨擘、史官翰林考校经籍,纂修文献,均离不开目录的支撑。因为作传统的学问,必然离不开传统的认识和传统的方法,虽然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各种检索工具功能非常强大,但是就文献整理与利用来说,仍然离不开传统学问的支撑。了解目录学、掌握目录学方法,遵循文献传承的基本规律,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医学人要做好中医古籍的传承与创新,势必离不开古籍专业知识的储备,离不开传统方法与实践能力的提升。唐代王冰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说:“将升岱岳,非径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面对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中医古籍文献,没有掌握一定的知识、工具和方法,对于研究和传承来说,必然难以达到预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十分重视中医古籍的整理和传承。这些年经过校点注释、仿真影印、辑复整理、索引辞典、电子出版等形式,已经整理出版了大批的中医古籍。特别是2018年,国家正式立项,启动了《中华医藏》的编纂项目,这项全面揭示中医药发展源流、系统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学术建设工程,受到了中医药学界的普遍欢迎。
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认为,我们国家很早就有目录之学,也有目录之书,但是却没有研究目录学的书。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过去的学者都是熟读深思,时间久了自己心知其意,于是本着自己的经验所得著作成书。他们自己心里明白,但却没有拿来示人。现在好了,有了这个学科,使得治学的人有了研究的工具,省却了自己搜讨的工夫,等有一天自己著书,就有规矩可循了。
宋代郑樵撰《通志》时,有感于目录在文献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直言:“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
中医古典目录学的目标和任务,是以历代医籍目录、目录工作和中医目录事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历史与源流、编撰原则与方法,以及实践应用和发展趋势的一门学科。是一门便于人们辨途觅径、登堂入室的致用之学。
《中医古典目录学概论》一书,汲取了古今众多学者有关目录学知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真知灼见,并结合著作者多年的学习与实践体会,通过立题选材,僭述编摩而成。该书可作为中医古籍科研人员学习中医古典目录学,并利用中医古典目录学研究和传承中医文献,提供借鉴。让它为当今中医古籍文献的传承奠定基础和指明方向,并为培养中医文献专业人才,进而提高古代文献的检索和利用效率,提供专业知识储备。
我们知道,一书目录,对于检读这本书很方便有用。但要了解某类典籍有哪些书,某些书的大致情况如何,以及怎样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书等问题,就必须求助于群书目录。目录学就是将众多书籍,通过一一考察它们的学术性质,判别门类,并按照一定的次序,汇集于一处,编辑成目录。如此,使得看书的人先查目录,可以知道书籍的所在,明白书籍的大概,决定该看什么书,应该在什么地方找。而且明白某种学术应该读什么书,某种书籍是值得读还是不值得读。
观书知名,因书判类,成为编目实践中较为直接的经验。中医典籍之命名可谓独具一格,既有赫赫显貌者,又有渊博典雅者;既有直抒胸臆者,又有隐曲委婉者。因此,观其名而知其书,不在少数,然而必兼有一定文史功底,或借助工具书方能领悟其蕴意。如渊博典雅者,唐代王冰的《玄珠密语》、明代孙一奎的《赤水玄珠》,书名均出典于《庄子·天地》。没有一定的文史功底,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当前,在国家重视古籍整理和中医文献传承的大好形势下,中医古籍目录学越来越成为文献研究者所必须储备的学识之一,其基本知识、基本既能和基本方法为中医文献的保护、整理与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在《中医古典目录学概论》书里,我们还看到中国历代有那么多的藏书家,他们视书籍如生命,爱书、护书,研究书籍的校勘和源流,甚至毕生殚精竭虑于此,乐此而不疲。最后将一生心血無偿奉献给社会,让我们后学者感奋不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医古典目录学概论》对学术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一个中医古籍分类的统一标准。
长期以来,中医古籍分类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种分类法兼容性差,类目繁杂多岐,致使各收藏单位著录数据参差不齐,给馆内管理和馆际交流带来诸多不变,造成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也给读者查找和使用带来障碍。有鉴于此,著作者从方法上寻找突破点,通过对各种古籍分类法的全面调研,分析存在的问题,本着全面性、科学性、实用性的原则,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从而制定出了一套统一完善的《中医古籍分类标准》。这一行业内标准,为中医专业图书馆,乃至公共图书馆进行中医古籍文献的编目,提供了统一规范的依据,有利于明显地提高古籍编目工作的效率,也为行业信息化建设和资源共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分类标准,还充分考虑到了分类当中出现的集中与分散的问题、交叉问题、类目顺序问题、类目下数目款目的组织问题,对于中医古籍的资源建设、分类管理、检索查询,以及开发利用各个环节,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能促进中医药信息的标准化,有利于中医古籍的保护、传播与利用,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中医药教育、科研和文化科普宣传等方面的作用。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然而,中医文献存世数量庞大,撰著情况复杂,每令学人望洋兴叹。因此,有必要通过目录学的门径和方法,提高古医籍的阅读和使用效率,以加快中医文献的研究,进而促进中医学术传承和创新。
通观全书,从字里行间你会发现,李鸿涛等三位学者,处处都在肯定前人的成就,同时毫不吝啬地讲出自己的心得体会。通过编著此书,他们认为,通过研读历代目录学著作,可以学习和掌握前辈目录学治学方法,增广见识,提高学养功底,将此运用于中医文献传承中,可以提升中医文献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效。
该书图文并茂,印刷精美,装帧设计古朴典雅,与书的厚重内容恰相映衬。金代著名的文学家,那位曾经为李杲的《伤寒会要》作序的元好问先生,在他的绝句《论诗》里说:“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有的版本写作“鸳鸯绣取凭君看”,或“鸳鸯绣罢从君看”。)意思是你可以将绣成的鸳鸯交给人们去欣赏,但不会把那枚能绣出五光十色仪态万千的金针传授给别人。今天我们看李鸿涛、张伟娜、佟林三位学者,不只绣出鸳鸯给同仁看,还把金针度与众人,让大家绣出更多更美的鸳鸯来。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
宋代学者程伊川说:医不读书,纵成仓扁,终为技术之流,非士君子也。且让我们用该书,走进千万本中医古籍,领略前圣先贤浩若烟海的智慧结晶吧。
(作者简介:孙天胜,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王逢春,山东淄博职业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