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思想市场的杰出企业家
邓中华
并不是每个人、每个学派都尊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比如,约瑟夫·熊彼特曾言,《国富论》一书虽然伟大,但它“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和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前是全新的”,“抽掉先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有意思的是,如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评价斯密,会得出一个结论,就算斯密并非思想市场的原创“发明家”,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创新者、企业家。而且,毋庸置疑,他是思想市场中的顶级企业家,无愧于“大师”二字。那么,他的创新之道是什么?对当今中国思想市场的积极进取者,又有什么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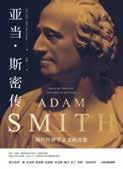
確认身处大变革的时代
任何一个在市场上觅求开天辟地的人,都要判断“范式革命”是否真的发生了。如果既有范式的根基的确被破坏掉了,就像马德堡半球实验让亚里士多德的真空观——“大自然厌恶真空”在公众面前彻底破产一样,那么,选择一条破坏性创新、建立新的价值网的策略才有可能奏效。反之,如果一种范式刚刚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就试图另起炉灶,通常只会自取其辱。
亚当·斯密很幸运地就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启蒙运动的火焰从法国烧到了英伦半岛,也烧到了苏格兰。当时,教会的势力和掌控力虽然仍有较大的影响,但已大不如前。例如,弗兰西斯·哈奇森是斯密的恩师。哈奇森的老师——约翰·西姆森,在18世纪20年代想要证明新教徒信仰的基础在于人类的理性,而非上帝的启发或恩典,结果遭遇一场骚乱和两次由教会召集的审判大会,最终被迫停止教授神学。自1730年担任道德哲学教授的哈奇森,也因为宗教观点被长老会起诉,却没有成功。
如果斯密的兴趣不是足够广泛,那么,即便他提出了新的框架,也不足以将它真正建立起来,他的理论就会像透风漏雨的茅屋,经不起风吹雨打。
在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斯密的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在1726年开始了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对组织架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都进行了改革。例如,由一个学监管理一个班级四年学期的体系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专业教授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都分别设置了专科教授。斯密后来也担任了两个学科的专任教授。
此外,与亚当·斯密紧密相关的大事件,还应该包括三件大事:(一)1707年强大的英格兰和弱小的苏格兰组建联合王国,但反对联合的人在后续三十多年里进行了多次斗争,让联合对苏格兰的红利直到1746年发生残暴的卡洛登战役之后才开始显现出来;(二)英法自1756年开始七年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英国战胜法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但另一方面,“如果法国人在北美获胜,可能就不会有美国的革命战争,也就没有美国的出现”;(三)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与《国富论》的出版均在1776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斯密看来,美国独立,是英国在重商主义指引下实施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的。虽然亚当·斯密没有赶上“经世济用”的好时机,但正是英国肉食者们的错谬,为他提供了极佳的素材,可谓“国家不幸思想家幸”。
实际上,正是因为身处新范式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好时代,哈奇森、大卫·休谟等人才野心勃勃地想建立“人的科学”,取得像牛顿一样的成就,“如果成功的话,可以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相提并论并与其相洽”。例如,哈奇森试图将自己独特的道德心理学、自然法理论的政府概念以及当时经典的辉格派政治诉求融合在一起。“这种理论的独特气质、具体想法、远大的雄心,都对亚当·斯密产生了深远影响。”
避免专家思维
将亚当·斯密称为“经济学之父”,其实有些不公平。因为受“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哈奇森的影响,斯密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学。或者说,如果说经济学有帝国主义式的霸道,那么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兴趣非常广泛。他最早感兴趣的是自然哲学,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授业者是约翰·西姆森的侄子罗伯特·西姆森,格拉斯哥的数学教授,牛顿的粉丝,也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专家。而哈奇森在美学、伦理学发表了大量文章,研究逻辑学、思维和知识,创新性地用英语而非拉丁语教学。
1748年,斯密受邀在爱丁堡举办讲座,邀请者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亨利·霍尔,后获任凯姆斯勋爵,一直致力于将苏格兰建设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国家和商业国家。尽管他很傲慢,但非常擅长人际关系和建立组织,是年轻人才的绝佳赞助人。斯密的讲座首秀题目是“如何在写作和演讲中有效沟通”,之后增加了法理学主题的讲座。

在现实生活中,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是常态,人们常常争论不休甚至势不两立,但对于创新者来说,这是一个创新的机会。
在修辞学讲座中,斯密表示,有效的交流需要具备简明和恰当两种特质。所谓恰当是指对语言的正确使用,既符合言者的本质特征和交际意图,又符合听者的期望。斯密提到了“共情”,预演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的核心观点。
后来,《道德情操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斯密写道,“我将在另一场讨论中尽力讲述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则,以及它们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代和不同时期经历的不同革命,不仅涉及什么是正义,还涉及警察、税收和军队,以及任何其他与法律相关的对象”。
如果拘泥于专家的角色,那是在玩詹姆斯·卡斯所说的“界限内的游戏”,是在既定的进化轨道上做改进、完善的工作;相反,在范式变革面前,必须大胆地把他人设定或默认的边界踩在脚下,是“和界限游戏”。如果斯密的兴趣不是足够广泛,那么,即便他提出了新的框架,也不足以将它真正建立起来,他的理论就会像透风漏雨的茅屋,经不起风吹雨打。正如一个产品,就算设计得很好,但缺乏良好的体验,恐怕很难成功。
跨越非此即彼的藩篱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有一句妙语:“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呢?
其中一个办法是,跨越相互竞争、对立的想法,走第三条路,把它们容纳其中。这第三条路一旦走通了,就是极大的创新。
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是连接两大知识体系的结果。一是人造真空,最终的结果是萨弗里的“矿工之友”——利用真空抽水的真空泵;另一体系是大气压驱动的活塞运动,代表人物是发明了高压锅的法国人帕潘,他的思路是利用膨胀蒸汽操控活塞。纽可门没有在两个对立的方法中选边站队,而是添加了一个横梁,解决了萨弗里和帕潘的矛盾,实现了伟大的突破。
任何一个试图在“人的科学”中自成一派的人,都必須对人的本性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当时,斯密就面对两种对立且颇为显赫的学术思想。
一面是悲观派,代表人物是霍布斯、卢梭、曼德维尔等。霍布斯认为,人生“孤独、贫穷、污秽、野蛮而又短暂”,人们的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唯有社会契约足以拯救众生;在卢梭和曼德维尔看来,正义不过是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而已,“公平正义的法则,最初都是由狡猾和拥有强权的人发明的,原本是为了让他们获得维护自己、压倒别人的不公正的优势”。
另一面则是斯密的老师哈奇森的乐观主义。他认为,人的关键属性是社交性,核心是“道德感”,一种源自本能但受神启发的道德感受能力。
简言之,悲观派过度理性化,认为道德不过是理性算计的结果,是典型的性恶论;而乐观主义者认为道德是一种本能,与利益无关,是性善论。
斯密既不站霍布斯一边,也拒绝了哈奇森的核心概念。他选择了“共情”(compassion或sympathy)作为自己的立论之基。正因为人们能感受到他人的快乐或悲伤,喜欢或反感,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看待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将自己反对或赞同的情绪同他人对比,同时也让自己被人看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斯密的观念,大概是“知人不欲,勿施于人”。最终,共情带来了互惠、付出和责任的交换,促进了商业和贸易双方的安全,从而塑造了社会道德。由此,《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就这样一脉相承,构建起宏大的理论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是常态,人们常常争论不休甚至势不两立,但对于创新者来说,这是一个创新的机会。斯密也许有意为之,也许是无意为之,抓住了机会,跳出了性善性恶的窠臼,并大肆吸收其中可为自己所用之处。例如,曼德维尔关于“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的寓言,就与“我们的晚餐并不是来自屠夫、啤酒酿造者或点心师傅的善心,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异曲同工,尽管考虑自身利益并不等于恶德。而这一点,创新者——要素的新组合者,比发明家更容易做到。
无惧竞争
无论是否愿意,竞争都不可避免。而且,思想市场的竞争还具有一个近乎残酷的特点——赢家通吃、恒吃。
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发现美洲的时间,比哥伦布晚五年,但是,美洲大陆叫America,而不是Colombo,为什么?因为阿美利哥把新大陆定位为独立的大陆,与亚洲分开,引发了地理学上的革命,同时,他卖力地宣讲自己的发现与理论,其中一篇文章在25年内被翻译成40种文字。而哥伦布则志在寻找黄金,所以对发现缄默不语。同样,斯密率先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就永远属于他了。
无惧竞争,有两个面向:第一,要敢于应对竞争者的挑战,守土有方;第二,要敢于批评错误的思想,进攻有力。
18世纪50年代,斯密二三十岁时,是他高产的年代。他“总是敏感地保护自己思想的优先地位,常对其他人可能的抄袭发出警告”。1755年,他向当地一个学会提交了一篇文章,“那是一份很长的清单……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一些主要原则,他急于建立对这些理论的专属权利”。这篇文章的一些表述让他青史留名,例如,“让一个国家达到最高程度的富裕和最低程度的野蛮的前提条件,除了和平、宽松的税收、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没有其他,其余的都是由自然过程带来的”。
而《国富论》本身,是建立在对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重商主义的批判之上的。例如,斯密认为,重农学派对农业过度重视,会导致资本被投入到无利可图的地方。重商主义是英国当时的主流政策理念,《国富论》则是“对英国整个商业体系的猛烈攻击”。例如,重商主义助长了制造商和商人的垄断精神,使他们学会了利用政府,促成了游说集团和特殊利益团体的形成,损害了消费者和劳工的利益,这些人是“为了自身利益促成欺骗甚至压迫公众的人”——这哪里是什么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分明就是战斗檄文。
选择正确的关系策略
任何创新者都不应该轻视、忽视“关系”或“社会资本”。关系可以为社会资本的所有人带来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前者包括通路、先机和举荐;后者则帮助关系人成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第三方。用结构洞理论的提出者罗纳德·伯特的话说,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只关乎生产等式,而社会资本涉及生产等式中的回报率,“社会资本是在竞争中获胜的最后仲裁者”。这条原则,对思想市场的创新者尤其重要,而斯密很好地践行了它。
人的科学,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所需要的信息分布严重不均,噪声繁杂,且价值迅速衰减。因此,要想在思想市场上大获成功,你必须:(1)离信源越近越好;(2)获得信息的速度越快越好;(3)受到信源的信任越多越好。
《国富论》讨论的议题如此广泛、宏大,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数据”、切实的经验分享、一流头脑之间的碰撞,绝不可能如此精彩。
斯密当然很聪明,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读万卷书,因此,他的人力资本存量很充足,但斯密的成功——他不仅身后名满天下、不见来者,生前即大获成功,与他拥有的关系网络和恰当的关系策略是密不可分的。斯密虽是一个遗腹子,但他的父亲在“托孤”时,把他托付给了一个相当有实力的关系网络,让他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他周围的长辈人脉丰富、乐于助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富有远见”。斯密上学进的是当地一所不寻常的学校,那是一位教育家治下的学校。因此,他在《国富论》中对苏格兰的教区体系不吝褒扬。后来,他成为巴克勒公爵的游学导师,陪伴他在欧洲大陆访学。
众所周知,我们有一个“钱学森之问”。其实,想让钱学森之问变成伪问题的人比比皆是,想成为当今中国大师级人物的雄心勃勃者并不鲜见。遗憾的是,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在关系网络的打造上不够明智,或者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在接近信源时所选择的角色和姿势不足以赢得对方足够的尊重,所以未必获得了真实的信息。有的教授声称要创建东方学派,但实质上仅仅是充当一个媒体人,为人提供媒体的价值;还有人致力于“诠释”信源当下的行为,充当一种类似高级文字秘书、助理的角色;还有人日日笔耕不辍,粉丝众多,著作等身,但那不过是远离信源的芸芸众生制造的虚假繁荣罢了……这都在触犯高质量关系的大忌——“轻易向食物链下游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