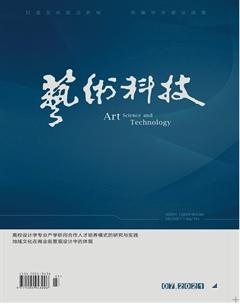《聊斋志异》公孙九娘悲剧成因分析
摘要:《聊斋志异》中的女子被称为“聊斋奇女子”,她们或婉约柔情,或妖媚惑人,或英姿飒爽,她们各有特点,平分秋色。她们的“奇”体现在与寻常女子大不相同上,书中的女性具有独立的女性思想,多是狐魅妖鬼,其中公孙九娘就是十年怨鬼。本文对公孙九娘的性格成因切入对其展开研究,深入分析她与莱阳生的爱情悲剧,解析其中深刻复杂的思想感情。
关键词:《聊斋志异》;公孙九娘;性格;悲剧
中图分类号:I2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7-0-02
《聊齋志异》是中国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编撰的短篇小说集,构思奇妙,谈狐说鬼。志怪小说虽记录为鬼神之事,却是人们价值观与世界观的集合[1]。这部奇书中很多篇章都描写了曲折凄美的爱情故事,塑造了多个性情各异的“奇女子”形象,这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蒲松龄的爱情观[2-3]。受所处时代的制约,蒲松龄选择将不能讲述的人世秘密交给鬼神,一切看似荒唐又浪漫,实则现实又残忍[4]。《公孙九娘》讲述的是十年怨鬼公孙九娘与莱阳生的爱情悲剧,从一见钟情的恋慕到红袖添香的热恋再到人鬼殊途的诀别,他们的爱情终以分离落幕。两人爱情悲剧收场不仅有两人的性格原因,还有不可避免的外部因素的影响。
1 悲剧的内在原因
1.1 知书达理,才华横溢
九娘初见莱阳生“笑弯秋月,羞晕朝霞”,一双明眸水波盈盈,笑起来宛如秋月似的清冷中见娇颜,羞涩的娇颊有如同朝霞似的红晕点缀,令莱阳生恍如惊见天人,一见钟情。加上甥女的介绍——“且是女学士,诗词俱大高作”,使莱阳生顿觉此女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在二人来往间,公孙九娘的身世背景得以明了,她是栖霞公孙氏的大家闺秀,是于七起义被连坐的冤魂,才华横溢又具倾城之貌,两人的姻缘在不知不觉间初见端倪。
九娘与莱阳生在甥女的撮合下喜结连理,一时间两人热恋情浓,难舍难分。新婚之夜,缠绵过后,九娘忆起过往,遂成绝句“昔日罗衣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取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由此处可见九娘的文学造诣之深。之后数日,两人情谊更深,恩爱非常。
公孙九娘才华横溢,生前的教养注定了她不与世俗妥协的性格。九娘与莱阳生的爱情是九娘仍然坚持自己追求所爱的初心的印证,即使身为冤魂,她也有为爱情奋不顾身的意志,哪怕知道结局已定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爱情不过如此。遇到所爱之人,九娘抛开了世俗的约束,不去想未来如何,也不去想自己的命运,在确定自己和对方的心意后,奋不顾身,勇敢追爱,这是其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体现。
1.2 身有冤屈,哀怨偏激
新婚之夜,九娘经历了由喜到悲的大转变,在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夜读者可以大致窥见九娘的性格。即便是在大喜之日,九娘仍不忘自身的冤屈,她所作的绝句,句句泣血,从中可见其执念之深。鬼魂在身死之时应当回归地府或是消散人间,九娘却在人间徘徊十年,可见其固执偏激的性格。她因于七起义被无辜连坐,家破人亡,支撑她到现在的正是她心中的怨恨,这怨已深入骨髓,融入她的性格之中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她的爱情观也走向了极端。
若她只是追求与莱阳生的爱情能修成正果,是可以不顾莱阳生安危,与他日日在这莱霞里做对鸳鸯,逍遥快活的。但正是因为爱,九娘选择了放手,由此可以看出九娘仍然怀有一颗温柔善良的心,不愿无辜之人因她丧命。
在这一夜,公孙九娘这一人物形象的高度远远超越莱阳生,一个是经历悲惨依然保持善良的女鬼,一个是在爱情与世俗伦理间摇摆犹豫的普通人,从蒲松龄的笔下,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对前者的欣赏。中国的女性“在历史中往往处于历史的遮蔽之下,所以只是作为男权的边缘中的一个消逝者和缺席者,甚至只能作为一个亚文化群漂移在父权制度的边缘,长期以来成为父权制度的陪衬品,因此,在历史中,女性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和思想品格”[5-6]。所以,《聊斋志异》中各位“奇女子”女性意识的觉醒已经难能可贵了,或者说,蒲松龄所具有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女性意识的思想已经是超前的了[7-8]。
深究下去,她与莱阳生成亲除了是因为爱情外,还是因为她的执念没有实现,“千里游魂,蓬游无底”,她的魂魄漂泊无所依,九娘希望莱阳生能收拾她的尸骨,埋在爱人墓侧,“使百年得所依栖,死且不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想洗脱冤屈已然不可能,连坐虽然惨无人道,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个人也无力反抗,历经多年,证据也早已不再,真相只能被掩埋在尘土中。九娘也清楚地知道,莱阳生只是一个普通人,能为她做的恐怕只有收拾骸骨。
2 悲剧的外在成因
2.1 人鬼殊途,悲剧已定
他们的分离早已注定,一大外因便是人鬼殊途。古代中国的哲学体系以阴阳二分为基本原则,作者笔下的生命也相应地出现了阴阳互补、相吸相斥的态势[9]。自古人鬼相恋的故事,凡修成正果者,必有还魂、死而复生、生子等荒诞的情节,本质上还是代表人鬼殊途,作者所能想到的大团圆结局仍是使去世的一方回归俗世,使“鬼”回归“人”的身份[10-11]。
《公孙九娘》以“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始,以“坟兆万接”“鬼火狐鸣”终,首尾呼应,故事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伏笔。九娘死于国家动荡、民族危难之际,其爱情又怎么可能以完美的结局收场。乱世的背景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性,突出了故事的层次感和命运的不可抗力带来的无力感,难免使读者为之怅然[12]。读者心里清楚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九娘这样一个惊世绝艳的女子落入如此境地,然而却无可奈何,只能叹惜。
两人的一见钟情似乎是一场倾城之恋的开始,然而一切开端不过是书生们对“才子佳人”故事的欲求[13]。在古代小说中,爱情故事的主角多为书生与美人,男子为色,女子为才,琴瑟和鸣、志趣相投只是后话,历经波折时的种种借口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世俗欲念的纠缠[14]。小说话本里从不缺有才华的落魄书生,然而能从一而终者却寥寥无几,无非是初见时的两相欢喜,热恋时的海誓山盟,厌倦后的始乱终弃,这出奇一致的路数,仿若只是作者在臆想自己的一段风流,笔下男子再寒人心肠,最终也能得到女子的原谅。
莱阳生对九娘的容貌甚是倾心,而后才去了解她的内在,由此可以看出莱阳生与普通男子也无甚区别,此外,他在得知九娘鬼魂身份后的犹豫也为之后两人的分别做了铺垫,尽管那一刻他的犹豫是人之常情,但却配不上九娘的一腔情意。后来,在面对九娘的收尸迁坟之托时,他又因未问清地址而失信,也可见其粗心大意,甚至可能是其并未将九娘放在心上所致。莱阳生对这个“鬼妻”的爱意终究难抵他心中的伦理纲常、男人本性,最终只能人鬼殊途。
2.2 承诺难继,陌路不识
两人分离之时,九娘以罗袜相赠,罗袜是女子向男子表示爱意的象征,这一信物既是兩情偕好永志不忘的象征,也具有向社会公示的道德或舆论的意义。分别之时,九娘相赠罗袜以示自己的赤诚爱意,或许是希望自己的爱能有等同的回报,或许是对莱阳生的一次考验,而在莱阳生因收拾尸骨迁往祖坟一事失信于九娘后,罗袜便随风而散。
九娘离开之后,莱阳生欲寻九娘之墓,却发现忘记询问墓表,“及夜复往,则千坟累累,竟迷村路”,至此他失去了九娘的踪迹。由此便可以看出九娘的心智之坚,即便莱阳生可能是因为分别之时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分离之事、九娘其人上,但九娘还是因为他没有详细问墓表所在而毅然选择不复相见,甚至再见之时亦做不识——“色做怒,举袖自障”,可见九娘的心智坚定,对纯粹爱情的追求。
九娘面对爱人的一时疏忽,毅然选择断去彼此的联系,即使莱阳生有心弥补也不给机会,除了因为她对纯粹爱情的执着追求外,也是因为其性格中带有偏激的部分,她追求的是极致、理想、完美的爱情。或许她的确爱过莱阳生,但她还是选择坚持自己对理想爱情的追求,这种冲破伦理束缚的勇气实属难得[15]。
在这一点上,公孙九娘与曹雪芹先生笔下的林黛玉有异曲同工之妙,她们都是为自己而活,不为世俗礼教约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恣意而为,活得潇潇洒洒,活得轰轰烈烈。两人对爱情都很执着且专一,且都具有独立的女性人格和独立的爱情观,她们独立的思想是其有别于普通女子的最大特点[16]。
黛玉死前烧毁诗稿手帕,不愿与宝玉一段情的见证留于人世,九娘最后的“烟然灭已”也是她决绝忘情的体现,她亲自给这段爱情画下了句号。即使魂无所依,终日漂泊不定,她也决不回头,这升华了这段爱情悲剧的主题。其独立的人格、思想和爱情观都是超前的,是具有深远意义的[17]。这一刻的九娘,摆脱了传统的柔弱女子的形象,展现出了女性身上刚性的一面,而女子最让人敬佩的地方往往在其坚毅处[18]。
这样的悲剧结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像血色溅出的花一般破碎[19]。长久以来,男性掌握话语权,他们笔下的女性鲜少有这样的悲剧美,骄傲的女子也会折损个性而苟活。蒲松龄创造的九娘却在呐喊:性格不该被性别定型,人物不该为大环境而让步[20]。若为瓦全,何若玉碎,既相负一时,便不复相见。
3 结语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宋明理学盛行之后,封建礼教尤为严格,女性被要求从夫、从子,在文学作品中常常才华有余而个性不足,《聊斋志异》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则反其道而行之。公孙九娘是悲剧性的,她蒙受冤屈化身为鬼,又所爱非良人,一身才华却恰逢乱世。但就形象塑造而言,公孙九娘是成功的,若只是人物背景具有悲剧性,其形象往往会缺乏层次感,而公孙九娘在决意离开后的每一步都在坚定地做自己,这样一个超时代的角色,用她的性格成就了另一种圆满——情节与立意的圆满。此后,所有读者都将记得,在几百年前,那个落魄文人跳出时代狭隘,写活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一个刚强的女鬼,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孙九娘。
参考文献:
[1] 沈嘉欣.从《搜神记》《阅微草堂笔记》看志怪小说的教化色彩[J].汉字文化,2020(14):32-33.
[2] 浦景昀.论《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及蒲松龄的女性观[J].汉字文化,2020(12):55-57.
[3] 翟嘉尔.浅析《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形象[J].汉字文化,2020(07):56-57.
[4] 程溢春.浅谈《聊斋志异》复仇小说写作模式及人文内涵[J].汉字文化,2020(18):72-73.
[5] 赵阳.清代闺阁女性笔下的才女陈素素——以名媛题咏《二分明月集》为中心[J].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20(04):59-61.
[6] 张静怡,张韵.唐、宋传奇中女性形象对比研究[J].汉字文化,2020(S2):48-49,83.
[7] 徐志豪,吉玉萍.所谓伊人:《聊斋志异·侠女》中高扬的女性主义意识兼蒲松龄的女性观[J].蒲松龄研究,2018(04):49-55.
[8] 苏盛祺.《聊斋志异》“狐嫁士人”故事中的狐女与士人形象分析[J].汉字文化,2020(20):63-64,69.
[9] 基语馨.《桃花扇》悲剧溯源——浅谈“阴阳”二元性模式的运用[J].汉字文化,2020(12):49-50.
[10] 徐菲.浅析《聊斋志异》中婴宁的人物形象[J].汉字文化,2020(20):65-66.
[11] 顾雯清.论《搜神记》人鬼恋故事的思想内涵[J].汉字文化,2020(22):42-43.
[12] 基语馨.美学视角下浅谈《桃花扇》“多层次”之美[J].汉字文化,2019(15):52-53.
[13] 叶雨涵.浅析唐元时期士人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思想变化——以《莺莺传》和《西厢记》为例[J].汉字文化,2020(07):156-157.
[14] 朱新雨.探究唐传奇中文士形象的思想内涵[J].汉字文化,2019(15):40-41.
[15] 金珺垚.浅析《十二楼》中李渔的婚恋观[J].汉字文化,2019(08):46-47.
[16] 孙玥.由“钗黛合一”浅谈钗黛人物形象的对峙与交融[J].汉字文化,2020(S1):60-61.
[17] 许愿.浅析《红楼梦》怡红院中的四位“奇”女子[J].汉字文化,2020(16):48-49,75.
[18] 薛芳芳.浅论刚性美、柔性美和美育[J].大众文艺,2019(09):252-253.
[19] 雍远,王志鹏.感悟《红楼梦》的悲剧意蕴[J].汉字文化,2020(22):34-35.
[20] 赵阳.美国电影《毒液》中女性边缘化塑造及文化反思[J].戏剧之家,2019(36):66-67.
作者简介:贾宇菲(2000—),女,江苏泰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