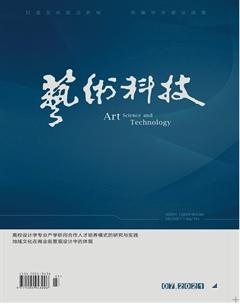从罪感书写到耻感文化:《解忧杂货店》的文化意义探析
摘要:《解忧杂货店》中主人公的一系列行为集中体现了作者对日本当代人的罪感书写,小说主人公来自社会底层,他携带了一种作者由赋予的社会罪感的东西,小说中的罪感主要包含破坏法律和道德意义的作恶和对这种作恶意识和行为的深刻反思,罪感既是主人公人性上的东西,也是社会的某种缩影。本文聚焦于东野圭吾在《解忧杂货店》中对主人公罪感意识的书写,旨在通过对作者笔下的罪感意識的理解,体会日本社会耻感文化的内涵。
关键词:《解忧杂货店》;罪感意识;耻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7-0-02
1 作品中的罪孽书写
1.1 主人公的罪犯身份
《解忧杂货店》的主人公是3个戴罪潜逃的罪犯,他们闯入了一个能够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杂货店中,他们好奇杂货店前主人用书信为人解忧的方式,也在杂货店收到了许多受生活所困的人的来信,3个人在一来一往的收信和回信过程中获得了自我的救赎。作品中,“看似宏大的选题,实则细小动人”[1],虽然主人公们都是罪犯,但他们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他们只是为了糊口被迫偷东西的人,“这些底层小人物们在艰苦的生活中相互取暖”[2],他们游荡在堕落边缘,任由他们胡作非为,随时可能滑入地狱的深渊,但若有人施以援手,他们就有可能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3位主人公被赋予独特的罪犯身份,一改传统作品中正派的主人公形象,在故事中,由于经济窘迫和孤儿院面临被收购的残酷现实,他们在成年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具有罪孽感的3个人也变成了作者剖析当代日本社会的形象范本。
1.2 求助者的生存烦恼
作品中除了对3个主人公的罪犯身份及行为的描写,还着重描写了身处于生存烦恼中的求助者们。在作品背景中,随着时代的变迁,日本社会逐渐呈现出尖锐的社会矛盾,这给社会中的各个群体都增加了生存压力,而这种压力的不断加大,“必定会造成社会情感化的漠视”[3]。作品共分为5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描述了一位无助的求助者,他们的困惑折射出了日本社会复杂的经济和生活环境,5位求助者的故事发生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都因为“烦恼咨询杂货店”的存在而交织在了一起。这部小说以每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为特征,汇聚了生存、梦想、亲情、爱情等一系列人生难题,用圆环式的叙事方式向各位读者讲述故事,笔触温和细腻,“营造了理性而又暖心的情感”[4]。小说中的每个故事都显现了一种超越时空的荒诞感,“虽然这种创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荒诞的绝望感,限制了对荒诞的暴露”[5],却丝毫没有削减小说的吸引力。小说中5位求助者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代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人们在情感、精神等层面存在的困惑,他们和3位主人公一样,代表着存在精神困惑与罪孽感的当代日本人。
如果说小说中的3位主人公代表了日本社会特殊的社会群体,那么那些求助者则代表了日本社会普通的底层民众,在此类小说中,“突出底层人物的弱小与悲惨是惯用的塑造模式”[6],作家东野圭吾从3个犯罪者的视角看待求助者,取得了与众不同的叙事效果,“从审美建构的角度,个体审美心理结构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7]。作者以有道德瑕疵的人物的视角为叙述视角,使小说有了一种荒谬、滑稽的叙事效果,这种叙事风格是符合当下时代读者审美期待视野的,当下是一个文化消费盛行的时代,在这样的语境中,很多文学作品创作不得不带上某种文化消费品的审美特征,如幽默、刺激、悬疑等,这些审美元素在小说《解忧杂货店》中都存在,这也是小说能够抓住当代读者眼球的原因。
2 日本文化中的罪感意识
其实,无论是小说中人物表现出来的罪孽行为还是求助者们面临的生存烦恼,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日本文化中隐含的罪感意识。在小说中,人物身上的罪感意识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个体问题,“更多的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因素”[8],而这种问题往往是由诸多的外部原因导致的。
2.1 二战阴影对日本造成的罪感意识
“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对个人发展、社会风气及国家气节来说都至关重要”[9],日本官方尽管对二战历史采取了歪曲和遮蔽的方式,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个体对二战的反思。二战不仅在经济上给社会带来了重创,还给民众带来了情感上的伤痛和精神上的荒芜,比如二战后他们将何去何从?小说中小男孩浩介的人生困惑很能体现日本人的这种战后心理,父亲公司倒闭并且欠下巨额债务,当父亲告诉浩介要潜逃时,浩介陷入了巨大的人生抉择之中,对于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少年来说,这是极其痛苦和艰难的,甚至有生命无法承受其重的感觉,他的父母最后选择跳海自杀,更是给他带来了不能缓解的伤痛,但是作品中并没有描写浩介父母自杀后浩介的生活状态,这种创作中的留白却像是作家故意给读者留下的引子,把读者带入浩介的生存处境,使读者对浩介的经历感同身受。
2.2 当代的社会生存压力
二战之后的日本社会,尽管有过辉煌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生存和生活压力的急剧上升,再加之近几年日本经济的逐渐恶化,当代日本人的生存压力变得更大,于是,小说中出现了在照顾情人和发展事业二者之间陷入两难选择的求助者“月兔”、兼顾正经工作和陪酒小姐身份却身心俱疲的“迷途的小狗”等人,“类似这样的叙写使得小说中的世事炎凉之感扑面而来”[10]。这也是典型的当代都市精神症候的体现,“作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可能会产生新的思索,同时也更容易抓住一些稳定不变的东西”[11],比如能够拯救社会人性的温暖而又强大的力量,通过对这些东西的描写,能够“从而促使大众本土意识的觉醒”[12]。
2.3 都市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消失所带来的心理罪孽感
从地理角度看,日本属于农耕文化圈中的稻作文化圈,稻作文明的不断发展使日本人形成了独有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对日本人勤劳意识的养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意志品质在《解忧杂货店》这部作品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小说中,求助者武藤晴美为了挣钱报答自己的亲人,她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还要到小酒馆去做卖酒的工作,这种“重复和枯燥使她感受不到自身价值的存在”[13],但她却坚信自己只要足够勤奋、足够努力就能获得回报;浪矢爷爷作为解忧杂货店的主人,他仔细认真地解答每一位咨询者的烦恼困惑并将保密性强的信件放到店后的牛奶箱中,二者身上的勤奋和细致是日本农耕文化时期所形成的民族性格特征的缩影,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它们“固守着传统文化的生存和传播”[14],但当代快节奏的都市文化正在慢慢遗忘这种传统的文化品格,小说中怀揣音乐梦想的克朗最终选择音乐,放弃鱼店继承人的身份的做法便是明证,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作品中人物精神深处的罪感意识的出现,“以至于人心甘情愿地主动进行自我惩罚”[15]。
3 罪感意识和耻感文化的辩证关系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的文化属于耻感文化,因为日本人依靠外部的促醒来发展人的良心”[16],所谓的“外部的促醒”,是指人物自身的觉醒和反思往往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但是《解忧杂货店》中人物的罪感意识与日本社会的耻感文化略有不同,二者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
3.1 罪感意识和耻感文化的辩证统一
在小说中,罪感意识使人物受到了来自他们内心罪恶感的鞭挞和谴责,日本社会不以事情的好坏来判定善恶,而是以生活在集体中的个人的行为是否影响了集体的利益或对集体造成了影响为判定标准。外在行为的约束使个体内心形成一套认知体系,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体的“罪感意识”。
由于二者都是对大众的内心产生的作用,所以小说中人物的罪感意识和日本社会反映出的耻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统一性,二者都属于精神层面,是无形地对人产生影响和约束的意识形态。正是因为作者笔下的人物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内心的罪感意识,才能进一步构成日本社会的耻感文化,一方面是因为罪感意识受到了来自个体本心罪恶感的拷问,才能使它达到规范个人行为的目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性的不断介入,人物的复杂程度却在急速上升”[17],而耻感文化则是个体的“知耻”,这指个体因担心行为受到外界的指责而“形成情感距离”[18],比如小说中的浩介父母的自杀行为就可以清楚地解释这一点,浩介父母自杀的直接原因不是破产后的自责,而是讨债的人们对他们的指责,“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的瞬间情绪”[19],遂采用“自杀”这一情节安排来终结这种外界赋予的“耻感”。
3.2 厘清罪感意识与耻感文化关系的现实意义
厘清罪感意识与耻感文化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学理角度理解当代日本民众的行为和心理,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日本的耻感文化对日本的风土人情、国民性情、社会发展等都带来了很多影响,《解忧杂货店》这部日本小说中对于这种耻感文化的描写就是一个日本社会的缩影,“真情流露与理性记录相结合”[20],有助于我们用科学、理性的态度深入地研究日本文化的国民性和民族性,把一些有关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问题纳入广义的文化理解和把握。
4 结语
东野圭吾在《解忧杂货店》中描写的众多的人物内心的罪感意识,多是由社会和人造成的,尽管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罪感意识,但是他们并没有一味地堕落和沉沦,而是有鲜明的救赎行为。在东野圭吾笔下,人在救赎过程中往往是主动和被动相结合的,他描写了人在面对自己的罪恶时,应该怎样主动地救赎自己,从这里可以看出,东野圭吾对罪感意识和救赎行为有其独特的理解。小说中的救赎行为有的表现明显,有的则较为隐晦,但救赎行为的存在,在为小说中人物形象赋予人性力量的同时也赋予了作品强大的人文关怀力量,还为现实社会的活动提供了鲜活的理论参照。
参考文献:
[1] 罗倩倩.《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因素分析[J].大众文艺,2019(13):181-182.
[2] 孙雅婷.论汪曾祺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J].大众文艺,2019(10):29-30.
[3] 鞠凌莉.探讨电视慢综艺的节目导向与观众的心理认同关系——以《向往的生活》为例[J].大众文艺,2019(13):195-196.
[4] 鞠凌莉.融媒体时代公益微纪录片与情感营造——以《三十三》为例分析[J].汉字文化,2020(12):189-190.
[5] 王贺明.论沈从文爱情小说中的荒诞感[J].戏剧之家,2019(26):222,224.
[6] 吕淑雯.韩国电影《寄生虫》的叙事内容与社会关注[J].汉字文化,2020(19):116-117.
[7] 田艳丹.论陆文夫《美食家》“吃的艺术”及其审美意义[J].戏剧之家,2019(26):220-221.
[8] 徐梦晓.《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情绪及其命运走向[J].汉字文化,2020(20):54-55.
[9] 孙锦鑫.论明代八股文考试利弊及其当代启示[J].汉字文化,2019(14):22-23.
[10] 童程.论20世纪日本艺伎文学形象特征[J].戏剧之家,2019(26):229-230.
[11] 童景熙.《黄昏》中的悲剧气氛与沈从文的悲悯情怀[J].大众文艺,2019(11):47-48.
[12] 陈镌锜.《礼记·学记》中的教育原则及其现实意义[J].汉字文化,2019(18):34-35.
[13] 蒋雨涵.电影《我们俩》中的独居老人与人文关怀[J].汉字文化,2020(19):114-115.
[14] 罗倩倩.新媒体时代下国产纪录片的发展策略探析——以《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例[J].大众文艺,2019(14):195-196.
[15] 徐紫薇,薛芳芳.从“自然的人化”到“人的自然化”——生态美学视域下人的解放[J].大众文艺,2019(05):228-229.
[16] 王虹娜.浅议日本和欧美罪感意识之差异[J].广角视野,2010(06):164.
[17] 李弋.动物世界——浅析《荒蛮故事》中人物的動物性[J].艺术科技,2019(08):82-83.
[18] 张刘刚.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难点和路径[J].新闻知识,2019(06):84-87.
[19] 商奕.《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情绪与讽刺艺术[J].汉字文化,2020(20):52-53.
[20] 罗泳镱.《徐霞客游记》的文史价值与人文情怀[J].汉字文化,2020(20):42-43.
作者简介:解文峰(1995—),女,山东济宁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