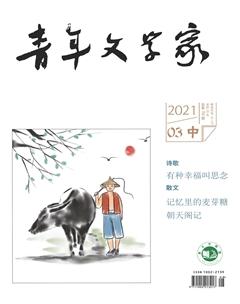从灿若夏花到静如素莲
摘 要:安妮宝贝是最早一批出身于网络平台、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她的作品始终围绕着爱与生死的主题,在旅行的路上、在不断地前行中完成她的写作,这一过程与她的人生轨迹高度结合。特别是在经历一连串的生活方式转变、亲人离世、经历生死、饱尝离散的伤痛之后,她的文风逐渐由晦涩迷离趋向至简还真。本文将结合安妮宝贝人生经历的变化,探讨其作品内容及创作风格一路蜕变的历程。
关键词:自我探寻;写作风格;爱与孤独;成长与成熟
作者简介:王鑫禹(1987.10-),女,汉族,山东淄博人,淄博张店建桥实验学校教师,研究方向:小学语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8-00-02
安妮宝贝这个名字是在网络文学中逐渐被读者接受和熟悉的,她是典型的网络女作家,她由网络成名后开始向纸质媒体发展。安妮宝贝于2000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合集《告别薇安》开始,在此后的几年中,她一直保持一年一本书的频率,并以此来呈现她的人生进程,可以说,在这期间每一本书都是她生命旅程的足迹。最初的《告别薇安》的呈现出隐藏在网络世界背后的不羁,《彼岸花》的爱恨纠缠,《蔷薇岛屿》的哀思与迷惘,转折点《莲花》超脱与自我救赎,直至《素年锦时》的通透。安妮宝贝的叙事风格随着她生命旅程的不断丰富、情感的不断内化与深邃,叙事技巧的不断完善,文化底蕴的不断沉淀,审美趣味的不断深入,指引她渐渐走出自我重复的“死循环”。此时的安妮已走过内心的煎熬和困顿,如蛹破茧,整个生命得到蜕变与升华——将个人的成长与转变完美地带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完成了一个网络作家的华丽转身。
安妮宝贝的小说是一种“私语小说”,作品中的“我”在城市中随遇而安,作品外的她在成长中孤独漂泊,在空旷的大都市,不断游离行走。她在肯定自我存在价值的前提下,对个人的生命状态、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探究和描写,“她用绝望的姿态和涩哑的声音唱出了爱与死亡,相遇和告别的永恒的主旋律”[1]。本文将从安妮宝贝创作期的三个阶段:青涩、成长、成熟,进入作者为我们创造的那个虚无的精神世界,通过分析作品的故事情节,写作风格,题材体裁和作品中的情感内核等方面,来浅析这位女作家创作风格的演变过程。
一、青春期的躁动与迷惘
2000年版的《告别微安》,书的版面很好地诠释了我们迷茫与矛盾的青春期——那是个浓烈艳丽的年纪,赤脚,白棉布裙,裸露着柔软的手臂。一个女子颈以下的身体,线条模糊暧昧,没有脸和表情,背后是宏大的深蓝色背景,像一片海洋——此时得她被称为“互联网黑暗中绽放的花朵”,网络是载体,安妮用手指敲开了一个通向城市边缘者内心的通道,如深海暗涌的一股激流,黑暗深渊中蠕动犀利的蛇。
《告别薇安》收录了23篇小说均成于1999年前后,她坚持爱与生死的主题。《告别薇安》、《七年》、《最后约期》、《下坠》,几乎每一篇小说里都描写了死亡和残缺的爱。“安妮成功地构造了一个个别具悲剧气息的故事,得到无数人心灵上的共鸣”[2]。这些发生在大都市上海的故事,一个叫安的女子,一个叫林的男人,“林”通常是一个有着干净的平头,笑容内敛,穿棉布衬衣用清淡的古龙水,固守自己生活方式的男人形象。“安”则是一个神情淡漠,带一点慵懒,穿着宽大的洗的发白的旧牛仔裤和黑色T恤,有着大把漆黑浓郁的如海藻般头发的女人。在上海这座大工业化城市熙攘的人群里,似乎每个人各自生活在自己独特的圈子里,各有各的哀愁和迷惘,这种特殊而独特的情感很难融入普罗大众的生活中,他们各自在时间和情欲的道路上流离失所,每个人都像是孤苦无依的灵魂流浪者,所幸他们始终没有停止思考。
这就是安妮刚出发时的姿态。用她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洞察力,用细致的细节描写将都市白领的爱情用一种虚幻却又真实的笔触一一书写下来。单一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她的重复,相似的人物、受制于她生活及成长的视野有限,她在冗长幽暗的青春期中徐徐匍匐。
二、成长期的等待与纠缠
成长悄无声息,随时光流逝,《八月未央》虽然看似延续了《告别薇安》的风格,但内核已经发生了改变。
安妮宝贝在《八月未央》再版的序言中说《告别薇安》与《八月未央》是她写作“青春期”的结束。接下来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彼岸花》用一种近乎撕裂的方式宣告,她终于告别了漫长的青春期,在语言和叙事风格上固守自己的风格,并再度将绝望推向极致。
在《彼岸花》中,生活在大都市里,有着冷淡神情、灼热灵魂和选择边缘生活的城市游离者,依然是她所熟悉的那类人:躁动不安、肆意妄为的南生有着源于被生母抛弃而产生的恐惧,看似冷静、理智,但又极端自我的林,显得矛盾而又真实。安妮用个性化的手法,使整部小说脱离了深埋网络背后,充满意识流的不真切,推动故事在现实情节和电影叙述这两条线索中交错前进。令故事变得饱满、内涵丰富,光影交织,画面感喷薄而出。
在《告别薇安》与《八月未央》的短篇小说里,安妮曾经零星地讨论过她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在这个长篇里,她的探索之路则走得愈加深远了。安妮已经逐渐成熟,在《告别薇安》与《八月未央》的短篇小说里,安妮曾经零星地讨论过她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在这个长篇里,她的探索之路则走得愈加深远了。她已经逐渐成熟,她开始理解所谓生命的意义,并趋向于真实而又琐碎的生活。而且似乎已经触摸到了自己的灵魂。她开始理解所谓生命的意义,并趋向于真实而又琐碎的生活。
三、转型期的沉寂与承担
可以说,《彼岸花》是安妮宝贝早期阴郁风格的极致,也是暂时的终结。告别《彼岸花》安妮宝贝又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她离开了充满小资情调、迷离而又不真切的上海,来到了北方城市北京。在北方厚重而坚硬的土地上,安妮的心也逐渐变得沉稳。恰在此时,最亲密的父亲去世,突逢变故,她与并不亲近的母亲之间开始变得亲密,这一系列的变故,让她深入生命内核,加深思考,同时也激发了这个年轻作家的新一轮创作成长。2002年《蔷薇島屿》和2004年《二三事》、《清醒纪》更像是一本本旅行日记,一路行走、一路思考、一路成长,它们标志着安妮已经不再是那个隐藏在网络背面骗得红男绿女沉浸哭泣的阴暗制造者,带着对生命更深层次的思考,她的语言更加清减,逐步向内探索。她的文字脱离了狭隘的情欲陷阱,一路疾走,奔向更广阔的天地。
文字风格的明显变化,首先出现在她的第五本书《二三事》里,这本书中描绘的故事与之前的《七月与安生》(《告别薇安》中的一个短篇)略有勾连,但无论是语言还是故事构架,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暗黑的夜、极端的人格在这本书中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历经世事之后的漫不经心、云淡风轻。她的写作风格至此走向了成熟期。深入去看,宗教因素使她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情感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升华。借助基督的“爱与恩慈”,她变得平和、内敛,更加包容。并用这一清淡的内核赋予主人公们姓名:莲安、良生、沿见、盈年、恩和。像七月与安生一样,良生与莲安更像是原有人物的加强版。灵魂高度契合,红白玫瑰般的模式嵌套其中:莲安的张扬、妖娆而丰盛;良生看似桀骜不驯,又内省自持,剧烈凛冽,兼具堕落和放纵的激情,让人想起早期浓烈的薇安和安生,她也正像她们一样,寻找像莲安一样的港湾,来完成对自我的休整和救赎。但人终归是个体,这也注定是一场沉静而分明的生命棋局,结果不言而喻。“一幕一幕的画面在心里掠过,犹如不定格的镜头。带有一种隐约的肯定之感。”揭开故事内核,你会发现她和我们一同成长,仍能准确击中读者内心不安并掀起波澜。一切不过寻常二三事,看似至简却又意味深长。
27岁的安妮宝贝经历了生与死、乐与路,告别那个支离破碎、沉浸在黑暗中的孤独灵魂,依托信仰、路上、城市中真实而赤裸的一切,营造起属于自己的、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堡垒,并蓄势待发。
四、成熟期的清淡与通透
《清醒纪》代表安妮写作风格的彻底转变,也是她最终成熟的标志。这是一部散文体小说,仍是依托城市生活,诉说人的内心成长。“纪”代表时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安妮都以一个内省者的姿态,用一个个瞬间,用一段段独白,向读者展示她的敏锐、聪慧及清醒,不被世俗所裹挟,锦衣夜行,遗世独立。
莲花,这个名字,非常映衬安妮宝贝此时此地的心态。她说写作最终需要的只是静默。她刻画城市,本来就并非流俗对于声色狗马的沉迷炫耀。比如她写善生对异性的态度,“只因未曾识别爱欲欢愉的表相,却被迫进入它的内心。他知道它的真相,所以不会被迷惑诱引。他说,我不爱惜她们,我对她们没有怜悯。”——这种“色空观”的世界观类似佛教教义。安妮的墨脱之行恰似一场盛大的修行,在行走间,将内心的不安宣泄,将压抑的情感释放,都市、密林、高山、边缘互为镜像,将这万物间的落差磨平,将一切归于起点,归于虚空,使自己的路途获得圆满的终局,在行走间获得新生。
如果说任何路途都必须获得终局,那么这个终局,对于安妮来说必将是完满的。零七年的九月下旬,安妮宝贝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杂文集《素年锦时》。这一次,她坐下来,就在我们的对面,开始近距离对话。《素年锦时》正是人与人的一次清谈。这本书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心灵疆域和思考力——“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文字如同穿越月光夜色的清越笛声。她在缓慢而交错的叙事线索中,将自己的一切展开来,平铺在新旧读者面前:有父亲的家,孤独的童年,回忆中再也回不去的南方生活,剥离回忆中的黑暗与难解的深情,平铺直叙却直叹人心。我们又一次被她带入她的世界,同时就像一面镜子,在她的人生历程中找寻自己遗失的过往,在她的行走中共同抵达心灵的救赎。
五、生如夏花之绚烂
她在漆黑的夜晚里告别薇安,在热浪滔天的越南海边负重行走。她以苦行僧的方式云游西藏,寻找莲之隐逸之地。最后她又回到都市中,开垦一隅荒地,隐居山中相夫教女。
这便是我们熟悉的安妮,她的句调一贯清冷自持,叙述仍旧纯简如刃。丝与刃彼此撕裂,发出如丝脆响,一种诡异的冷调美感始终贯穿在她的文章中,形成一种独特的精神内核。这位喜欢旅行与隐匿的年轻女作家,作风低调,态度边缘,她的笔触总是截然决断,却又温暖流连。她也在探索中不断创新,在叙述风格的成熟和作品结构的创新上,带给读者源源不断的惊喜。
参考文献:
[1]戎丽霞.从《彼岸花》看安妮宝贝小说中的虚无意识[J].安徽文学,2007,06: 29-36.
[2]王立欣,常春辉.安妮寶贝作品集《告别薇安》的悲剧意识略说[J].沈阳大学学报.2005:05.
[3]田德云.从喧嚣抵达静默——以《二三事》看安妮宝贝[J].枣庄学院学报.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