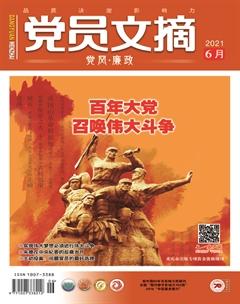警惕环保整改“纸面销号”
梁晓飞 张磊
相隔几个月,两份不同问题的验收销号公示材料完全一样;有的验收销号材料是县生态环境局抄袭县委办的,竟然还抄错了8处;有的销号材料声称“严厉整治”,被免职的责任人却在两个月后得到提拔;有的问题刚刚销号,就被媒体重新爆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一大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然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高压”常态化背景下,仍有个别地方和企业敷衍整改、“纸面销号”。
第二轮第二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前不久向有关省市、企业和部门的督察反馈显示,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推进落实不够,第一轮督察指出的部分问题解决不到位。个别地方和单位甚至弄虚造假、虚报数据、伪造台账。这些环保整改中的形式主义,暴露出部分地方在销号验收方面存在管理漏洞。
个别地方整改“纸面销号”
中部某县级市的一处偏僻小山村,曾有企业打着土地复垦的旗号露天采煤,大片山体遭到破坏。在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中,露天煤矿破坏生态、土地复垦及生态综合治理标准低等问题,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之一。
2020年12月初,这个县级政府密集发布多个针对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整改任务销号验收的公示材料,称这一生态修复项目工程已完工,并由市政府组织了验收。
记者在前往村庄附近的马路上看到,原先违法采矿的区域种着几排松树,但地形地貌并未恢复。矿区遗留下来的道路边随处可见散落的石块,绝大多数边坡连荒草都没有,仍有几处十余米高的堆场未平整,矿区尽头一处巨大的采坑尚未回填。走到那几排松树前,记者发现,矿区靠近马路的一侧修筑了梯地,但仅在每个阶梯的边缘处才能看到几排向外倾斜的松树苗,路边看不到的地方几乎没有绿化的痕迹。
然而,在当地政府销号验收的公示材料中,这一区域已完成绿化660亩。2020年9月关于这一违法采矿案的一份处理情况则显示,早在2019年12月,当地政府就对该生态修复项目进行过验收,并于2020年7月30日再次组织验收,“认定生态修复工作已达到整改目标”。
2013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要求,非干旱地区露天采场边坡应恢复植被。对照相关标准,结合实地采访,很难得出达到整改目标的结论。
遇到“硬骨头”绕着走
一些基层干部向记者坦言,环保督察整改任务大都是“硬骨头”,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干部心态较为复杂。记者梳理发现,“形式主义”的环保整改大体存在以下3个类型:
一是拈轻怕重不愿担当,有时“一刀切”,有时“切一刀”。如湖南省衡南县车江镇下发开展砂石土矿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时间,与督察组进驻时间很接近。当地整治方案要求,对相关矿山企业“一律停业整顿”,是典型的平时不作为,急时“一刀切”。与“一刀切”对应的还有“切一刀”的现象。比如,督察反馈提到,山上有3处非法采石场,那么,整改任务就限于这3处,未提及的和后续新开的就不属于整改任务。
二是口头重视不落地,纸面推进走过场。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在未完成皂河上游截污工程的情况下,通过给1.21公里黑臭河道加装“遮羞盖”的方式掩饰问题;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对近20万立方米混有危险废物的垃圾简单覆土掩埋后,便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整改到位;湖北省武汉市城管委发布黄陂区前川社区借用科技手段对8张需要整改的点位图片“P图整改”,作为成效上传,应付整改。
三是心存侥幸,蒙混过关。多年前,北部某县在违法围填海问题整改中阳奉阴违,一面编造假文件,谎称违法项目已停建,一面顶风作案,召开专题会议,加快推进违法项目建设。
堵住“纸面销号”漏洞
“纸面销号”既与一些干部不敢动真碰硬、环保整改走形式等因素相关,也暴露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销号环节存在管理漏洞。尤其是整改销号程序不明确、标准不统一等,为个别地方弄虚作假、敷衍整改提供了可乘之机。
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往往涉及多个行业、多个主管部门。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坦言,市县政府和部门既是环保整改的责任主体,也是整改销号的责任主体,对于整改任务的完成情况自行验收,并在政府网站公示。上级部门对相关问题销号的核查,大多限于资料审查。
杜绝敷衍整改、“纸面销号”,关键在于完善制度。一直以来,整改标准问题是困扰地方整改責任单位的难点。同一个问题,依据不同标准,现场给出的结论可能差别很大。
记者检索公开信息发现,尽管各地大多要求对环保督察反馈的整改任务实行“销号管理”,但截至目前,只有湖南、四川、安徽、海南等省份单独制定了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验收销号的标准和办法。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