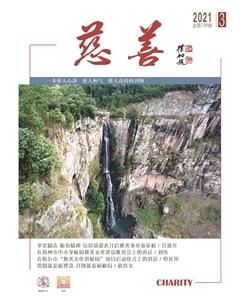母亲,我心中的海
刘维隆
母亲有我,已经四十。幼年时,我眼中的母亲,已不年轻。在哥哥和我之前,母亲已有四个儿女,都是到十岁左右染上疾病(在现在只是普通可治的病),在当年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一个个都夭折在母亲的怀抱里。母亲晚年眼睛不好,都是那时候哭坏的。父亲常年在外,又是家中单传,母亲一人生活在家乡那个大家族中,苦情可想而知。经历十多年抗战烽火,父亲从旧军队失意回到西安时,并未告知母亲,是母亲闻讯后迈着小脚托人相引来到西安,才重新团聚成家。之后才有了我们哥俩。
母亲是个文盲,是个“睁眼瞎”(母亲自语),又缠着小脚,是父亲同事圈里那一群太太中最土气的一个,也是最随和、大家最亲近的一个。街坊邻居都叫她刘嫂子,院子里的孩子常高一声低一声地喊她刘妈。记事时,我看着母亲洗脚,裹缠脚布,心疼地说:“妈,你咋把脚弄成这样?不痛吗?”母亲讲:“好娃呀,你不懂,那时候万事不由人,哪比得新社会。”母亲一心想学文化、有个职业,过得有尊严一些,1958年那阵,她入了扫盲识字班,并决意进了帽子组劳动,一度还糊过火柴盒,为此将我打发到学校食堂吃饭,但是最终还是因两个孩子的拖累没有继续在外工作。所以她常讲:“妈这一辈子最苦就是没有文化啊”——这句话她反复说,我记忆犹新。
母亲晚年得子,更是疼爱有加。她本来想在哥哥之后有个女儿,不料又生了个二小子。哥哥小时淘气,常惹她烦心,母亲对我自然多一点顾爱。父亲常年在校,放假才回家,我们日常就生活学习在母亲的身边,这让我从小就在母爱的海洋中畅游。就是年长之后,我在睡梦中惊醒,听妻子化聪讲,我的嘴中呼唤的还是:“妈,妈!”
自小母亲就教我做个好娃,当个好学生,长大做个好人,不要好吃懒做,不要嫌贫爱富,不要与人攀比,不要吝惜自己。上学后,我一直穿着母亲做的粗布衣服和纳底鞋,到了高一还是那样。小学五年级,我要参加全市小学生普通话观摩演出,要求穿蓝裤子,我没有,母亲无奈,把姑姑(和我们一起生活)的裤子让我穿。不料在学校沙坑里疯跳,新裤子上落下难洗的污痕。我至今记得第一次买的运动服,我都舍不得穿,我的第一件毛衣也是姑姑传给我的。
生活是如此简单,精神的自由却是空间无限。母亲对我是放手的,很少絮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能玩上的类项我都玩过,弹球、洋片、踢毽子、乒乓球、足球、打篮球、滑旱冰、水庫游泳、上城墙偷野桃,有时候心野跑到灞河泸河,一整天不见人影。记得只有一次,回来太晚,母亲恼怒了,要打我,我跑出院门,一直待到晚上九十点。在昏暗的电灯杆前,死死地盯着院门,看母亲怎样来叫我。咯吱一声,大门开了,还是母亲的那张笑脸和她引我回家的五分钱(可买一根冰棍)。
我还算争气,上学后一直要当好学生,我知道妈妈一生的最苦就是对我一生的要求。上学的第一天,我把手背在身后,挺直腰杆一动不动地听讲——内容听不进去,精力全在绷紧的动作上了,只为落得老师的一声表扬和全班同学的目光。以后当上了中队长,又由少先队推荐,再用小黑板画“正”字计票,选上了大队长。那时母亲参加家长会,总是打扮得一身新,笑呵呵地听老师讲:“你娃多好。”回来又比照着训我那调皮捣蛋的哥哥。
我爱读书,常常拿当时能找到的《烈火金刚》一类书,放学后就蹲在大门口阅读,直到黄昏日下才被母亲叫回去吃饭,回想起那些书中的故事、人物,对我年幼的心灵是多么大的滋养和升华啊。由此知道了世间的真善美,母亲就是它的化身。至今我还深深地记着:二年级时我的第一篇作文就是“我的妈妈”,开头第一句便是“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如何教我、为我、让我当一个好学生。”听着众人的叫好,念着我的文章,她那慈爱的目光和笑容,现在还闪烁在我的眼前。
母亲一辈子都崇尚“公家”的事,把那看作男儿的正途与大事。自小对我的“公务活动”满心高兴,牵肠挂肚,全力支持。她老说:“娃呀,大家和老师相信你,咱就要实心去做,做就做好,不要让人有意见。”那个年代的少先队活动真多,拾废铜烂铁、捡骨头炼钾肥、办小银行、搞小球藻、捐“红领巾号”拖拉机,全校学生的捐款由我保管,母亲将它放到柜子的最下边用衣服压着,我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要翻箱倒柜看看它还在不在,弄得她哭笑不得。后来终于如数上缴了,她笑了,我也轻松了。记得有一年暑假,老师让我负责浇灌校园的小菜地、喂猪,每天到北大街捡西瓜皮,拉水管浇地,弄得水一身泥一身,她心疼地摸着我的头,洗刷一番,第二天早早地又让我去干了。
母亲喜欢我干活踏实、卖劲。鼓励我假期到外边勤工俭学,自己找活挣钱。有两件事至今让我记忆深刻。初二的暑假,我去北郊人民面粉厂前的“长坂坡”挂套拉车,就是将套在自己肩上的大绳挂在架子车的辕上,助车上坡。小小年纪,下死力气,手都够上了地,肩膀拉红了印。驾车师傅心疼我,往往付钱要比别人多出一毛钱,一天挣得一块五,回家交到母亲手上,她那欣慰怜爱的目光让我暖意荡漾。还有一次,为莲湖路小学修房子,需要和泥小工。我自告奋勇地去了,现场一看,有点傻眼了。一大摊土还有麦秸,我一个人要担水和泥,踏踩到位,供上用料。一整天累得晕头转向,腰都直不起来,对面楼上小姑娘悠扬的歌声和着咸咸的汗水一同浸在我身上。下午拖着泥脚回家,妈妈为我炒米饭。端着香喷喷的小盘子,那个香啊,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口念想。
母亲虽然叫我们做事不要吝惜自己,可她心里最珍惜的却是膝下的这两个儿子。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哥俩都上了中学,那个饥荒年代,每天想的盼的就是吃上饭,母亲喝稀的,人已浮肿,我们吃干的,也饥饿难忍,一个馒头,要在手中攥成细长的麻花,在街上兜一圈,一截一口地细细咽下,延长时间欺哄肚子。母亲破天荒地做了一件骗人的事,多年以后,她告诉我的时候,眼中还含着泪花。那时姑姑的粮食关系在青海姑父工作的兵站,每月寄粮票来,有一次,母亲坚称邮件没有收到,请求再三,部队又寄了一月的来,这一切似乎家人都不知底里,她是用这点活命粮喂养了面带饥色的儿子,却让自己背负了长年的不安和愧疚。
“文革”来了,父亲痛不欲生,儿子在外受整,家庭顿失平衡。风雨飘摇之中,母亲,一个身患重病(高血压)的小脚老太太,成为我们心中的最疼。她又如何来支撑?母亲的伟大,她的坚持、智慧和乐观,更使我感动。就在那个父亲和我谈话,我从城墙上哭看回来的夜晚,母亲对我讲:“娃呀,你说得对,不管怎样,咱们都是一家人。你爸前几日就说不想活了,我劝他:‘不成!不管你有啥事,后边的日子还长着呢,山不转水转。你不活了,人家还会说你是背叛,你跟儿子脱离了关系,也脱离不了干系,咋都会影响到他们。当年(土改前),你心烦了,还想着回家种地,我劝住了你,不然现在咱娃都真成了那个破落户的地富子女。娃呀,只要你和你哥好,对你爸好,咱这个家到了也一定会好!”母亲的一番话点燃我心中的一盏灯,直到现在,它还在我心中闪亮涌动。
其实,那些日子,我最担心的是被抄家,是我那虚弱可怜的母亲。街坊中不时有叫骂抄打之声传来,街道上穿行的是那些耀武扬威、腰扎皮带、手挥棍棒的打手。我的一位女同学的家,一夜之间被认定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全家罚跪受打,抄得底朝天,那位女同学第二天便在学校贬到了我的座位旁边,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她那脖颈上留下的红伤印和脸上倔强不屈的神情。人们啊,怎么一夜间都失去了良知和同情?杨老师被挂了黑牌,剪了头,进入“牛鬼蛇神”之列,批斗会上,有同学居然在她跪着的腿脖上挂上钢丝系着的石头!母亲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母亲却淡然冷静地安慰我:“不用怕,没有啥,咱家本来就没有啥。我个孤老太太,能把我咋?你们好好的稳稳的就行!”她把早已准备好的棉衣——我平生第一件毛领棉衣——和几十元钱一并塞给我:“带上它,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要照料自己。”——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大勇无惧、外柔内强的母亲。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她竟成了全家的主心骨。
“文革”的第二年,我们便被“解放”了——学校进入了“逍遥”时期,我却跑到了学校,跑到了外边,组织小兵团,自己搞军训,编辑新四中报,塑毛主席像,又集体自费到北关农展馆参加“收租院”泥塑工程,从那里,自己组织联系,第一个奔赴农村,到汉中南郑县插队劳动。我真恨自己,年少不知慈母心,那时母亲血压已高到200mmHg往上,整天头昏,一半时间在床上,父兄不在身旁,与我相依为命,我一天忙忙活活在外,给那么多同学家长做劝慰工作,要大家一起下乡,怎么就没有多多安慰我的母亲呢?是母亲的大量、宽怀和理解支撑了我,母亲已经把我看成了“公家人”,也就是大家的人,她就是再苦,也不让儿子为自己分心。
离别的那天,母亲不顾身子虚弱,坚持要下床送我到屋外,当我扭头看见她扶着门框,饱经风霜的脸上流出浑浊的眼泪时,心像针扎一样的疼。我这苦命的老母啊,你一个人在家里怎么过?离难别苦你经过多少回,这一次却是风烛残年的病老时刻。你就是我们的家呀,没有你,我就是树上无根的枝丫,我真真地舍不得离开你呀!
那年春节,上級向我们发出了春节不回家的倡议,我心中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梓潼岭上,我吟写着自己心中的小诗:“妈妈,我不回家啦,不是儿不想家,只因为孩儿已经长大,你说过,咱有小家,国有大家……”泪水终究使我诗不成篇。一过完年,我就在公社街上买了“益寿宁”,一溜烟地回到了你的身边——进门时,你还躺在床上,头上敷着毛巾。见我归家下床就要给我擀面——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面,同学中凡是吃过的无不赞不绝口。你吃了我带来的药,逢人便说:“娃带的这药真好,头一下子不昏了。”母亲治病没有吃过什么好药,但我心中明白,能治她病的最好的药,就是对儿子绵绵无际的思盼之后,见到儿子茁壮成长的那一刻。
我在钢厂的时候,母亲去住过一次,一个多月,那时她已过75岁,背驼腰弯,拄着拐杖,移步已显得艰难。我带她到武侯祠去转,走几步就要歇一下,冠心病、白内障、十二指肠溃疡诸多疾病折磨着她,可她平时对我们仍是一脸彩霞,自己的大小事不让你操心。厂部露天广场上演电影,我背她下楼,安好小椅让她一解寂寞,只这一次,她死活也不让我背了,“我的腔子(胸口)疼,背着难受”,这是她的理由。实际我明白她怕看见众人瞧着书记的眼光和我流下的汗水。平时我厂务繁忙,化聪照顾母亲多,她常对化聪讲:“咱俩吃这剩下的饭菜,做好的让他们父子吃。”化聪逗她:“那为啥?他们就不能吃剩饭?”母亲便说:“我吃点剩的就行了,化聪,你也吃新做的。”她把自己的习惯要搬到我的小家。一次她腿疼,化聪为她拔火罐,有事出去耽搁了一下,回来看到她腿上被烫出了鸡蛋大的水泡,她疼痛难忍,却一边安慰化聪一边不让对我提及,就是医院抓药服用后出现了药物反应,一连便血好些天,她也是自己忍着,与化聪一起,对我封锁消息。
母亲出身很苦,一生磨难。我的祖母去世很早,她是随着母亲改嫁到刘家的。其母做了我的新祖母,她也许配给了我的父亲。祖父去世后,祖母这个外来户受尽了家族的欺侮,又病又疯,死在母亲的身边。晚年每说到此母亲仍泪流不止。母亲没有以怨报怨,却把自己的爱洒向家族的每个成员。听叔父不止一次绘声绘色地讲过,母亲后来成为那个大家庭中众多妯娌、媳妇、女娃们的领袖,她善解人意,明白事理,协调纷争,排忧解难,主持公道,有亲和力。当家的大掌柜四爷脾气不好,众人怵怕,有啥不可开交的时候,只要母亲来了,好言好语劝说一番,一切风平浪静。当年母亲离乡到西安,大家不舍。我的姑姑年龄小,与我那夭折的大姐同岁,父母双亡,又是家中独女,因得父亲的怜爱和母亲的眷顾,一同到了西安,之后两家人就一直生活在一起。
母亲一生,与人为善,与世无争,心胸如海洋般,包容得下世间的一切苦难,向世人奉送着无尽的慈悲。她一生最常说的两个字是“可怜”,谁有难处,谁就可怜,她的同情怜悯可以说是无际无边。早年在家,大门口只要听到乞讨的声音,她都会摸摸索索地搜上点东西,颠着小脚跑到门口,就是那人走出好远,她也要将吃食送到手边。街坊邻居哪家有事有难,她都会去陪着流泪,劝说一番,回来自己还要难受半天。听嫂子讲,那些年她与父母相伴在家,邻居有些照顾,母亲是不谢不安。有点土产都要分送各家,就是吃好的,也要送去。包饺子,她在锅台上边下边舀,母亲拿走了一碗又一碗,到最后剩下一点点还不够孙女打尖。自小,我就没有见过母亲跟谁红过脸,她待人亲切和气,宽厚而又热情,一心向善,助人为乐,是里里外外大家公认的大好人。
母亲的宽容忍让,有时让家人都无法理解。从大房搬到那难以插足的地方,是母亲的自愿,别人难以协调得下,她只有苦了自己,为的是房东儿子娶妻团圆,她说人家也可怜。之后人家三天两头地催我们搬走,两家人最后都翻了脸,只有母亲不愠不火,时时还替人家说话,弄得父亲不快。记得有次回家,父亲让我好好安慰一下母亲,她已有一天多没有吃饭,原来老两口为此闹气,父亲动怒,母亲伤感,这是我平生见到的唯一一次“家中事变”。母亲啊,我们已经可怜到这般境地,你还操念着别人的可怜,这是何等的心肠、何人能有的良善?
如今,每逢家人亲戚相聚,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母亲。回首往事,时过境迁,多少恩怨付之东流。给我们留下最深忆念的却是母亲的慈爱、贤惠、大度、宽容和无人可及的胸怀。她具有弭纷争、趋和谐的天然倾向,又具备将苦难转化为慈悲的神奇力量。她虽不吃斋念佛,佛心佛意却如佛陀一样。她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九,正好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这真是奇妙的因缘,她原本就是人世间少有的菩萨心肠。
母亲的最后几年,平静而安详。本来她体弱多病,亲友们都以为她要走在父亲的前边,结果她比父亲多活了六年。她人慈气清,淡泊心明,与时相适,顺情应势,自己也十分注意起居和保健。其时她最大的痛苦是严重的白内障,直至失明。起先在她的面前晃动五指,她还能影影绰绰地感到,到后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曾背她到省医院看过,希望做个手术,重见光明。医生检查过身体后对我讲:“老太太命真大!冠心病动脉硬化成这个样子还能挺住活着,真不容易,再要做手术,恐怕下不了手术台了。”无奈我只好把母亲背回。自此她便整日足不出屋,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上,在黑暗中凭着自己的慈慧和心智,与外部世界相呼应。
那时,我已到西乡县政府任职,工作更多也更忙。我的家就住在办公小楼隔壁的平房中,庭院内长着一棵高大苍翠的柏树,年代久远,树干挺拔,一枝长藤顺干而上,直达树冠,春天沿藤绽开一溜粉白色的小花,人称爬柏凌霄,说它有情有灵。我每当仰头望着它,就想起我的老母,心里一阵一阵发暖、发酸。清明中秋,我带着儿子夜晚在树下祭奠,追怀老父,思念老母,我真怕她不辞先行,让儿子没有最后相见的机会。这时的母亲不仅是我的日夜牵挂,也成了我心中慈悲的象征。母亲的慈爱善良、悲悯情怀已深深地浸入我的血脉与意识之中。扶贫解困、救灾纾难,我的脑海中常常浮现母亲的面容。1991年春上,西乡横遭冰雹之灾,我驱车赶往现场,菜籽田里狼藉遍地,看到老人孩子在哭泣,我的眼前尽是母亲悲天悯人的神情。一路察灾救灾,一路热泪滚滚。母亲啊,我的心无时无刻不与你一起跳动,你就是我一生的慈恩情天。
1991年8月,我到西安开会,抽空特意去原来的老住处——立新街的2号院看了一趟,也是了结母亲的一桩心愿。房东张家和邻居十分热情,张妈讲:“新中国成立前那县太爷,八抬大轿或高头大马,十分威风,现在这县长跟百姓差不多,也就一个样,没啥稀奇的了。”回来我笑着对母亲学着说。母亲讲:“娃呀!你到这个份上,是公家信任群众拥护,在自家里,那可是祖宗八辈积的阴德,咱要当个穷官,做个好官,好好给老百姓办事,可不敢耍那个八面威风,让人戳后脊梁。”第二天离别前,母亲拉着我的手,聊了半天家常,她讲:“现在世道好了,生活宽裕了,你哥当了区长,你当了县长,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妈能活到这个岁数,看到这个景象,已是个造化。万事不愁人了,只是晓儿(我的侄女)的婚事还没成,将来也会好的。妈只想你和化聪搞好自己的身体,养好刘齐,一家顺顺当当的,妈啥时闭眼,也都放心值得了。”不想,这竟成了我们母子的诀别。
忘不了1991年12月11日,上午9时,我到西安开会,正要迈入丈八沟的大礼堂时,哥哥来了,叫住了我:“母亲病重,赶快回家。”岂不知进到北关哥哥家里,室内摆设了灵堂,母亲在遗照里安静微笑地看着我。我虽有预料,但亦猝不及防,一时万念俱焚,泪不自禁。母亲并无急病大症,前日有点感冒,稍有不适,服药治理,平静休养,不料一夜过去竟已仙逝。她走得十分安详,没有大的苦痛。母亲已大彻大悟,心近神明,她对后事交代已清,不再想打扰我们的安宁,这样静静地离去,正合她的个性。她已奔赴天国,正在我们的头顶,她那大慈大悲的面容永远驻留在我的心中。
那一夜,在母亲的灵前,我千思万想,心泪涟涟,点点滴滴汇成泉涌,回想她对我似海的恩情,思念她辛劳、慈爱的一生。冰心老人讲过,“有爱就有了一切”。从母亲身上我领悟到,只有爱才是一切美好人性和文化的生命:母亲不识字,谦卑又自轻,可她却拥有所有文化中最可宝贵的神圣,她是我人生第一个老师,也是我永生永世不可相离的至親,我为她子,无上荣光。
这一夜,我为母亲写下了一副挽联:“不识字,大爱铸就文化,是儿终生导师;是凡妇,一生慈悲为怀,堪称大写之人。”呜呼!母亲,我与您同归。
母亲是海,爱如海,情似海,慈悲如海。往历60年,我心才明白,情感最实在。人性、人格、人情;慈善、和谐、宽容。这就是母亲的文化,为我书写着大爱的人生。如果说,在我既往的路上还有那么一点点爱心、达观与宽宏,那便是母亲的传承,是母亲的精神流淌在儿子的血液里,日夜奔腾。
母爱是海,无际无涯,既深又广,没有一丝索求,倾注一片汪洋,滋养我的生命,启迪人生智慧,给我无穷力量。挫伤时,我在这大海中寻找抚慰;困顿时,我在这大海里感受坚强;欢乐时,大海与我一起共舞,去追逐那温暖而又明亮的阳光。
母亲,您离开我们已经快20年了,睡梦中最常见的就是您的面容,时间愈久,母爱愈深,思情愈浓。您如今在天国可好?您晚年失明,让儿十分心痛,那都是为儿女熬下的疾病。我真想祈祷上苍,让您重见光明,让儿再背上您一次,去看看家乡,看看亲人,看看哥哥和我一路走过的风景。我想让您知道,您的儿孙都还争气,将您的爱牢记心中,挥洒在各自人生行进的路程,您和父亲的大爱将会世世代代成为我们的家风。
写罢《父亲母亲》,蘸泪赋诗一篇:
抱朴归真为著文,
最念莫过父母恩;
热泪和墨情相催,
心香长燃祭双亲。
低头觅思慈颜在,
举目山海意难尽;
仰天祈我笔底润,
文脉哪抵情脉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