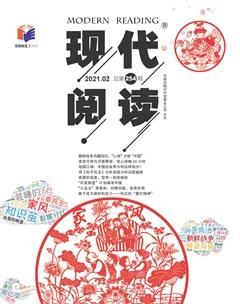当我们谈论孤独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美] 杰茜卡?潘
我人生中最孤独的一段时光估计就是在北京的日子,一只名叫路易斯的聋猫是我那段时间里唯一的朋友,除了我对它的毛过敏,以及我俩其实没那么喜欢对方,一切都还好。路易斯是我室友的猫,但我室友很少在家,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我和路易斯一人一猫相依为命。因为它听不见,所以哪怕我已经在家待了3个小时,只要我一转身,它还是会吓得魂飞魄散,一蹦三尺高,它总这么大惊小怪也会吓到我。
下班后,我独自吃完晚饭然后上床休息。一到半夜两点,路易斯就会在我的门外无情嚎叫,但当我下床去一探究竟时,它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场景,加上时间又是夜半三更,总是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和维多利亚时期的鬼魅住在同一屋檐下。
那段孤独的岁月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回首过往,我也能像讲述一件奇闻趣事那样把它拿出来分享。但实际上,现实比听上去要痛苦得多。我最近找到了曾经的日记本,我的日记上清晰地记录着,当时的孤独和痛苦已经折磨得我几乎丧失了生活的勇气。
这一点都不好玩。
我依旧正常上班、吃饭,熬过一天又一天。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比我那时的状态更糟糕。但我仍然陷在自己的泥淖里无法自拔,从早到晚,从今天到明天,孤独没有尽头。有些日子,我甚至觉得自己成了隐形人,也丧失了感知能力,生活中任何与人交往的互动,都无法让我觉得自己融入社会之中了,我只觉得自己既不能被看见,也不能被理解。有时候,孤独从四处袭来,我能感觉到无边的黑暗就那么静静地笼罩着我。我不知道如何摆脱那种感觉,当它紧紧抓住我的时候,我迫切地想甩开它。我幻想自己能迷迷糊糊地睡去,再也不要醒来,那样就能逃离它了,每每想到这儿,我的心就获得了片刻的安宁。
这种情况最常发生在周六清晨,我一睁眼,一个没有计划、无人可见、没人等我的周末赤裸裸地出现在我眼前。似乎当我漫无目的、没有任何动力和明确的目标时,孤独给我造成的伤害最大。雪上加霜的是,那时我远居海外,身边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
最近,一个可以无所事事的周末是我最梦寐以求的时光。在伦敦的这些周末我特意弃未完成的任务于不顾,忙里偷闲,这让我感受到了莫大的愉悦。但当我处于孤独之中时,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努力在工作中结交朋友,邀请大家共进晚餐,并搬去了新的公寓。和路易斯挥手告别后,我拥有了新的爱尔兰室友。他是一个群居动物,很快将我纳入了他的朋友圈。对抗孤独的斗争很辛苦,就好像在进行一场我永远都不会胜利的战役,但最终,我的努力还是奏效了,我的孤独感不断消减。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相信,孤独是一种随着你生活状态的改变自然而然产生的东西。在新的城市定居,从事新的工作,独自一人旅行,亲人和朋友搬家离开,以上种种都让我们不知道何时才能和这些爱的人重逢,也失去了和朋友的密切联系。孤独就这样产生了,它不是上天因为我们过于可爱而发出的一种谴责,它只是一种自然的情绪而已。
无论你是内向还是外向,羞赧还是活泼,孤独不会因为你的性格而网开一面,它就像一场无差别选择的流行病。因为相关研究显示英国已经有约900万人经常或一直被孤独困扰,英国政府甚至还任命了一名专门负责缓解民众孤独感的部长。遭受这些困扰的并不仅仅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群体——老人,生活在郊区的人们也在孤独感中苦苦挣扎。16岁至24岁的青少年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孤独,手机上的社交媒体、邮件和外賣软件让我们失去了和别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相应地,我们对手机的依赖程度正在逐年增长。每个人都有一段孤独的岁月,或短或长。尽管这个话题早被媒体翻来覆去地提及,已不再是什么禁忌,但和别人面对面探讨它,依旧会让人觉得危险在步步逼近。
(摘自天地出版社《走出内向:给孤独者的治愈之书》 作者:[美] 杰茜卡·潘 译者:郑志远 桔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