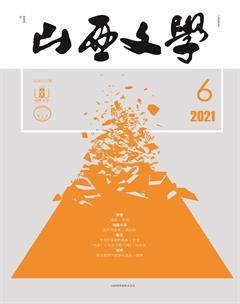我判断优秀只有一个标准
沙丽 周洁茹
一、写作的回归:从出走开始
沙丽:您曾在访谈文章中多次提到,2000年辞去公职,停止写作,远走美国,是因为一种厌倦感,这种厌倦感,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写作动力的戛然而止?就像眼睁睁地看着灵感一点一点地被蒸发掉。
周洁茹:一切动力的戛然而止,不仅仅是写作的。这里只谈写作,因为1999年开始做文联专业作家,那一点最后的火花也被磨灭了。如果你要毁掉一个作家,就让他去做专业作家,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也许不适用于其他人,适用于我。后来要去做编辑,我也一直在想,如果你要毁掉一个作家,就让他去做编辑?有个前作家现编辑就跟我讲,能够毁掉你的只有你自己。我同意他的说法。“灵感一点一点蒸发掉。”这个句子真有意思,能够一点一点蒸发掉的只有爱情,绝对不会是灵感,给了你才华当然也会把灵感一起配备了,才华还在灵感也在。
沙丽:美国的生活对写作带来的影响,或许要到多年以后才会发酵并发挥效应,正如您自己所说,在美国是一个中国字都不能写的。可以谈谈这段海外的生活吗?
周洁茹:那段生活与写作也没有什么关联,确实是什么都没写,而且十年。我尝试重新整理那十年,重新写那十年,很可能是十个短篇,不是长篇是各自独立的短篇,如同我真实的生活,无数碎片,每一片都很锋利。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沙丽 :不断地行走、迁徙,或者说漂泊,哪怕是定居与内地更为接近的香港,也没有获得一种安稳感,家乡及家乡风物、年少时的往事会不断地闪现在作品中,念兹在兹。我读过您回归后的大部分作品,在那些散文随笔中我读到了与北岛散文中一样的“絮叨”,既是一种状态、情绪的反复呈现、陈述,也是一种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感伤、叹喟。我有一种感觉,您是需要在写作中完成一种“诉说”的,那么,与之前的写作相比,搁笔十多年后再重新写作,您的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写作于您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呢?
周洁茹:我不喜欢漂泊这个词,一定要用,那么我们都是来地球漂泊的。谁都不是地球人,我就是这么想的,谁都是从别处迁徙到地球,也就是所有人类永远没有安稳感的缘由。我想我的“诉说”也是如此,无关时光、物是人非,也许只是想要回家,而我认为的回家,也不是那种意义上面的回家,对我来讲,就是回去我来的地方,也许离地球也不是那么远。心态变化这个问题,我刚才还在想,我33岁时,也就是我来到香港的年纪,我是无法想象我的45岁的,就是我现在的年纪。那也太老了吧?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也不敢去想象我的60岁,会比现在更从容一些吗?会写得更好一些了吗?或者就是又不写了?还是不要去想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吧,也许一切都会超出你的想象。写作对我来讲就是日常生活,希望它成为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大家都活得太低落了,希望都能够写一点字,有一点自我思索的机会。
沙丽 :可以就此谈谈内地、香港与美国三地文学写作的环境(氛围)吗?
周洁茹:这个问题对我不适用,我就没有环境这个意识,就好像我从来意识不到我写的就是城市。我可以来讲生活环境的不同,毕竟这三个地方还是很不同的,没有一个地方是相同的。但我这个人,还是在三个不同的生活环境活成了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说,我在哪儿都是一个人,对融入很不刻意。也就是我对整个地球的态度,一种旅行者的态度吧,我想,说到底,我就是来旅游的,到时我就走了。而我这个人又是非常不喜欢旅游的,所以总是时时想着早些结束,也许有一些人可以从旅游中得到更多拓展,我的方式可能还是自己拓展自己,我之前也说过,每一个人的口中都有一个宇宙。写作环境的话,内地是这样的,我也写了一阵子,但再写下去都是一样,写一篇和写一百篇都没有区别了,如果我留在内地,继续写,应该就是这个局面。到了美国,由于我个人的问题,美国是没有给到我一个写作环境或者写作氛围的,按照风水的说法,我的属性可能跟那个地方有些对冲,但又有些人是到了美国才写出来了,只能这么讲,祝贺他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找对自己的地方。香港,其实跟我也不是那么调和,我是流动的、一种风,一个动态,与任何一个固定的地方都形成不了一个固定的关系。我讲了这么多,生活环境,写作环境,到底还就是我一个人的环境,我的写作不与任何其他写作人发生关联。刚才正看到一个编辑发了条朋友圈文章,《做编辑,不要跟同行喝酒,不要看读者脸色》,还挺对的,也适用于作家。做作家,不要跟同行喝酒,不要看读者脸色。
二、香港故事与生活的实感经验
沙丽 :尽管您从未将自己定位为香港作家,回归后的写作也不全然是以香港为背景,但在我的理解中,“香港”在您个人的写作中还是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视角,一方面是与内地、美国经历的回望比照,也意味着不同的人生阶段,另一方面香港这个城市本身的特殊性,在这些您所经历迁徙的岛屿与生活中,香港或许更能够让人感受血缘上更为亲近的一个群体的生活与精神状况。尽管“在香港”不比“在美国”,或在其他地方有一种内心的踏实感。在香港已逾十多年,您对这个城市有怎样的感受?通过写作,是否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这个城市?小说家是否就像一个探密者一样,对一个未知的城市,对人的故事总有一种好奇?
周洁茹:感谢您这么说,我自己不定位我是香港作家,就好像我自己不定位我是七零后作家。我写作的时候是不去想我自己在哪儿的,这个故事写出来了,被认为很香港,我才被植入了一個意识,我果真是在香港。其实有时候我早上醒来也得想一想,我果真是在地球了,那么就安然地,仔细地,度过这一段被安置的时光吧。在香港逾十年,已经超过了居住在美国的时间,要来谈感受和理解的话,我突然想到一种婚姻,一开始是相亲,大家都觉得你俩挺合适,就结婚吧,也挺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有一点点爱情,有一点点确实年龄有些大了,再大下去就真不生孩子了,最重要的部分肯定是刚刚好的一个时间,刚刚好的一个人。婚后一年,两年,三年,直到第七年,有的就不过了,有的还是过下去,还是挺简单的,一点点亲情(是的,爱情成亲情了,爱情这个东西性质就是这么不稳定),一点点确实有孩子了,孩子得有一个完整家庭,看起来完整的也行,最重要的部分是中年了,中年就得做中年要做的事情了。我前些天写了一篇《热酒中年》,说的是我完成了一个小说,非常得意,马上就去朋友圈说了一句,我对我满意。我就是这么说的。当然后面我又看了一遍那个小说,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得意的,但是很多写作人都是这样,就是作品完成的那个时刻,那个高光,那种得意,也许我就是要追求那个瞬间,自己对自己的满意。我的一个朋友圈朋友就来讲,少年饮热酒,中年喝晚茶。什么阶段应该做什么事情,到了中年,也别那么热烈了,酒喝快了伤身,还是喝茶吧,养胃。也许他也不是那个意思,但我就是这么理解的。也是我对香港这个城市的感受,相处了这么久,秘也探得差不多了,偶有惊喜最好,没有也OK,以后好好过。爱情就是会成为亲情。
有人问过我粤语的问题,因为从来没听我讲过粤语。我答的是,任何谁在香港住得久了都会讲粤语,但我已经住了十年,我讲粤语肯定还不如许多新到香港几个月的人。为什么呢?我说过是因为我不去街市买菜?不看TVB?不交本地朋友?实际上我什么台我都不看,我也不交朋友,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买菜的话我只在网上买,我连楼下的超市都不去。刚才看到一个文章说,有一种鱼已经灭绝了,因为这种鱼不会游泳,而且很宅,出生在哪里就待在哪里,完全不动的。不会游泳的鱼。如果我的粤语也是这样,不与任何外界发生联系,那真的永远也讲不好。但我一直都是听得懂的,甚至能够分辨得出来北角跟大围的口音差别,好像也足够了,我在写作的时候会使用地道的粤语,单从文本看来,我的口音绝对是中环的。
沙丽:接下来会继续有意识地书写香港这个城市吗?其实,您现在的不少作品,“香港”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叙述空间。
周洁茹:接下来会有意识地写得长一点,其他地理空间什么的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我可能更在意时间,好吧,我又想了一下,我也不在意时间,有一阵子我很在意人,我总想着要把人写通透了,是挺难的,我自己都还没透。
沙丽 :从您早期的作品一直到现在的,“到哪里去”是一个主题,地理空间有时只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标识,有时也象征着一定的社会及时代背景,但很明显,您突显的主要还是“人”的精神状况。如若要做一个比较,早期作品或许更像是一种人生及精神困境的寓言,如《到南京去》《到常州去》,而近年来的《到深圳去》《到广州去》《到香港去》,还有另一些有地理标识的《旺角》《佐敦》《油麻地》等等,有着更加真切的可以触摸的生活实感经验,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周洁茹:作家作品的前后期变化,这是评论家的事,不是作家的,或者我可以自己评论自己,自己比较自己的作品,我真这么想过,但是理论储备很不够,那我还是暂时先放下吧。我自己能够感受到的一个变化是在语言的方面,极简,就是我目前的状态,早期可能还有一些情节以及细节的追求,现在完全无所谓了。
沙丽 :我极少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中读到一种始终贯穿的不安感、疏离感,这种基调却是您之前与现在的作品中不曾改变的,这种精神意绪,是否是现代人无从逃脱的命运?
周洁茹:只要我还在地球,这种精神意绪就不会更改。我最近的小说《51区》谈的也是这个问题,逃离来逃离去,只要在地球,就永远是身体的囚徒。
沙丽 :女性一直是您作品中的主角、叙述者,讲她们之间的友谊,她们在婚姻与爱情中的处境,她们的成长与人生困境……尽管在看《岛上蔷薇》这部长篇时,我有那么一点遗憾是,没有感受到那么饱满细腻的、内在的女性成长经验及故事。但转念一想,现代人的生活如此匆忙,就像小说中的女性在不断流动的生活与地方中结束青少年时期进入中年,完成了女孩到女人的转换,我们的疼痛与伤感有时只是在停歇的空隙中得以闪现,是零碎的,断续的,甚至来不及抚慰与思索,旋即进入下一段旅程。在这种书写中,包括前面提到的作品,能够感受到您是在丰富的生活、情绪的细节中,揉碎了自己的观念,呈现状态、事实与现实,而不是表达概念、理论与思想。那么,我想问问,您是如何理解当下女性的各种状态?您理想中的现代女性是怎样的呢?那些试图或想要抗争一下的女性,不管是在情爱中与自己的欲望作跳腾的,还是在现实婚姻及家庭生活中带着希望一点点攒起行动勇气的,当然还有那些不断沉沦或沦陷得不可自拔的,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笔下的这些女性,她们的形象越清晰,您笔端的温暖与不忍我想也就更执着吧。
周洁茹:感谢您读《岛上蔷薇》,我一般不大提这部作品,因为觉得没写好,就好像有一阵子我也不愿意提《小妖的网》和《中国娃娃》。但关于这三个作品的创作谈和对谈也挺多的了,我这边的感受是越谈越觉得没写好。全书呈现得不好,虽然每一章节也都有闪光之处。我觉得没写好,是我还可以更好的意思,但如果要拿出去打榜什么的,还是可以打一打的。这些天在看《乘风破浪的姐姐》,有位姐姐说的,有人讲我是谜之自信,但人不就应该有点自信?我同意她的说法,人就应该有点自信,人不自信了,也跟一条咸鱼一样了。但“谜之自信”这四个字,也蛮神奇的,很多男性就是有这个自信,很多,而且超级超级自信,那才是谜之自信。我的希望是女性也要更多自信吧,孙悟空压了五百年放出来,还是非常舒展的,仍然很能打,完全看不出来被压过的痕迹。很多女性被婚姻家庭什么的压个十年二十年,即使放她出来都不能回弹了,就算是送给她一个社会,她也接不住了。这一点我也很遗憾,我想的是,会不会当年压的时候,就已经直接把女性给压死了?放不放的意义也不是很大了。所以我也要看《乘风破浪的姐姐》啊,能翻红的都是真妖精,是所有女性的榜樣。
三、小说的艺术与功能
沙丽 :70后小说家的艺术风格好像很难说是遵从于现代主义或现实主义,也并没有经历过在现代或传统之间那么明显地较量与抉择,对于经典作品的理解或许也会不一样,在您的理解中哪些文学作品可以称之为经典呢?
周洁茹:我想一直都是《西游记》,它教给了我写作的第一课:严肃地胡说八道。补充一句,《西游记》的确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文本,甚至可以讲是残忍,它的特点就是能把情爱都写残忍了,这一点非常吸引我。
沙丽 :在您已经出版的这些作品中绝大多数都是中短篇,虽短小,却写得扎实真切,是能够就此打开一个社会的窗口,读懂一些人、一类人的生活与生存状态,您如何看待小说介入现实的功能或作用?您认为优秀短篇小说的标准有哪些?
周洁茹:我之前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把文学分成两种,一种是文学,一种不是,我自己挺得意的,现在看看,不就是一个病句嘛。但我的意思到了,我就是这样的,黑与白,爱与恨,是与非,没有灰色没有中间地带。我判断优秀也只有一个标准,自由。
【作者简介】 苏沙丽,80后,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惠州学院。著有《思想的乡愁——百年乡土文学与知识者的精神图像》《贾平凹论》。
——粤语·女独·伴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