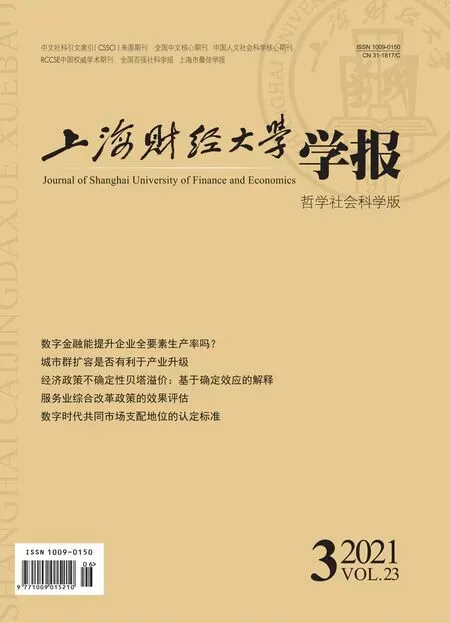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溢价:基于确定效应的解释
邢红卫 , 王汉瑛
(1.山西大学 管理与决策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2.山西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一、 引 言
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近年来,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推动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我国积极发挥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然而在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效能的同时,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在持续加剧。据Huang和Luk(2020)发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2014年后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几何级增加①2000–2014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平均为118,2015–2016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平均为273,2017–2018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平均为412。。根据Merton(1973)的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当投资和消费机会集中受到市场状态的随机冲击时,投资者有动机进行对冲。因此,经济政策作为能够从多种渠道影响市场状态的重要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产价格的决定作用愈来愈强。由于经济政策与时俱进,不可重复,因而经济政策的变化不存在先验信息,无法以概率分布来衡量。大多数研究通过映射资产收益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暴露,进而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暴露对资产预期收益的影响。
依据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投资者的风险厌恶是内生和恒定的,承担暴露高的资产风险会要求高的预期收益,因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暴露应当有正的风险溢价(Kelly等,2016;陈国进等,2017)。然而,前景理论表明投资者的风险态度是外生和条件依赖的,当获利时倾向于规避风险,卖出资产而获得确定收益;当亏损时则倾向于追求风险,继续持有资产。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暴露为正的资产价格也呈上涨趋势,因此投资者基于不确定性规避会在未来卖出或减持此类资产,从而在市场出清条件下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暴露有负的风险溢价。已有研究也表明,由于投资行为不可逆,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时,投资者出于审慎会减少或推迟投资,从而导致资产预期收益下降(Gulen和Ion,2016;Bali等,2017)。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可观测,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资产价格的理论分析(Pástor和Veronesi,2012;Drechsler,2013;陈国进等,2017),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溢价的实证检验较少,更鲜有文献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负向溢价的内在机理。
本文以中国股票市场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以每个月股票日收益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作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会产生稳定的负向溢价。以股票月收益判断投资者获得的是确定的收益还是亏损,发现当月内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加剧趋势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较高的股票月收益为正,并且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与下个月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较低的股票月收益为负,但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与下个月收益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因此,“确定效应”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产生负向溢价的主要原因。尽管实际中投资者总是利用经济政策实现套利交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使依赖于经济政策的套利交易产生风险,然而控制套利风险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负向溢价依然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构建定价因子,发现包含FF3因子、盈利因子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的五因子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具有更好的定价效率。
本文的主要贡献为:第一,以往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主要从理论方面或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微观层面的实证检验,揭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会产生负向溢价,弥补了当前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研究的经验证据。第二,与以往研究局限于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相比,本文进一步剖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产生负向溢价的内在机理,有助于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内涵。第三,与对成熟发达市场进行研究相比,本文选择投资者非理性交易特征依然明显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现加剧趋势的中国股票市场,在更为理想的环境下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负向溢价来自于投资者的“确定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面对后疫情时代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的挑战,在宏观审慎框架下加强宏观政策的连贯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以及考虑经济转型过程中各产业政策之间的统筹协调,有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二、 文献综述
市场参与者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基本面的不确定性、参与者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及难以用概率分布描述的奈特式不确定性,如政治冲突、贸易争端等。经济不确定性无法直接观察,针对经济不确定性这四方面的特点,当前主要有四类测量方法:第一类是基于宏观经济指标在横截面上的差异性。以横截面上股票月度收益的标准差、企业季度利润增长率的标准差、不同分析师预测的未来一年GDP增长率的标准差、不同行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标准差的加权和度量经济不确定(Bloom,2009)。第二类是基于宏观经济和金融财务信息的不可预期性。估计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自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以残差波动率的加权和第一主成分作为经济不确定性(Schwert,1989;Bali等,2014);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宏观经济和金融财务指标的共同因子,然后以自回归模型估计每个因子的残差序列,以残差波动率的加权和作为经济不确定性(Jurado等,2015;黄卓等,2018)。还有一些文献以期权已实现收益波动率与期权隐含波动率之差(Bali和Zhou,2016),以企业债券与国债的收益率之差作为经济不确定性(Bachmann等,2013)。第三类是基于新闻媒体对经济政策的报道。利用文本分析法搜索报刊中包含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出现的频次,依据文章频次计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Baker等,2016;Huang和Luk,2020)。第四类是基于市场参与者对经济不确定性反馈的调查。由于市场参与者对偶发性事件的感知具有主观性,因而通过企业或金融机构对于宏观经济预期的调查数据,计算预期误差作为经济不确定性(Bachmann等,2013;Ozturk和Sheng,2018;Bloom等,2018)。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多个渠道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比如投资者的财富、风险偏好、交易成本、通货膨胀和利率等,因此属于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维度。Wachter(2013)表明时变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可以很好地解释市场风险,邓可斌等(2018)和陈国进等(2018)也表明忽略经济政策的市场模型会显著低估系统性风险,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系统性风险。Pástor和Veronesi(2013)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使股票市场的波动率增加,而且会使股票波动率之间的相关性增强,这种效果在经济环境恶劣的时候更加明显。因而Liu和Zhang(2015)、雷立坤等(2018)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入市场波动率预测模型,表明能显著提高模型的预测效果。依据资产定价理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暴露应该有正的风险溢价。Kelly等(2016)发现如果期权的合约期内有政治事件冲击,那么为了对冲政治不确定性产生的风险,该期权的价格会显著提高,尤其在经济不景气和政治不确定性高的时候更明显。陈国进等(2017)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同时影响股票价格和随机贴现因子,且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股票预期收益也会提高。
然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提高投资者的损失厌恶,从而影响投资决策(Kahneman和Tversky,1979)。Pástor和Veronesi(2012)通过建立一个包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股票价格在政策改变时会下降,而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股价下降幅度越大。Aramonte(2014)以期权隐含波动率在宏观政策颁布前后的变化度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发现经济不确定性会产生负向风险溢价。在实证研究方面,Gulen和Ion(2016)表明由于投资行为的不可逆性,当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时,投资者出于审慎会倾向于减少或推迟投资,从而使资产预期收益下降。Bali等(2017)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股票收益具有负向预测能力,Tan和Ma(2017)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大宗商品价格也有负向预测作用。关于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量指标较少,大多使用Baker等(2016)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析其对公司投资决策和财务状况的影响,如李凤羽和史永东(2016)、王朝阳等(2018)。李凤羽和史永东(2016)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会放弃投资机会而持有更多的现金,王朝阳等(2018)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溢价的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而且受限于针对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量指标出现较晚、相应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缺乏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个股横截面收益中的定价能力。因此,本文以个股收益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贝塔作为股票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暴露,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风险溢价及其产生机理,为拓展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理论提供丰富的经验证据。
三、 变量与样本选择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
由于经济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一般都会以新闻媒体作为传达手段,新闻的时效性也要求媒体实时跟踪和报道经济政策的最新动态,因而对新闻媒体进行挖掘成为提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尽管Baker等(2016)基于中国香港《南华早报》文本分析得到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然而基于单份报刊分析的文本可能会受到记者或编辑主观选择性偏差的影响,而忽略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Ozturk和Sheng,2018)。因此,本文选择Huang和Luk(2020)依据新闻报刊得到的日度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他们参照Baker等(2016)的方法,选取中国内地《北京青年报》《广州日报》等10份报纸,利用文本分析法搜索文章中包含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出现的频次,然后计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且采用另外114份中国报纸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受媒体选择性偏差的影响很小。与以往的测量指标相比,本文选择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基于更全面的调查范围,研究结论具有更好的稳健性。
在每个月,以股票日收益与无风险收益的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进行回归,并且以市场风险因子(MKT)、市值因子(SMB)、账面市值比因子(HML)、动量因子(UMD)、盈利因子(RMW)和投资因子(CMA)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Ri,t是 股票日收益,rf,t是无风险收益, αi,t是 回归常数项,分别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市场风险因子、市值因子、账面市值比因子、动量因子、盈利因子和投资因子的回归系数, εi,t是 回归残差项。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作为股票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暴露,风险暴露高的股票应该要求高的回报,反之风险暴露低的股票应该要求低的回报。
(二)其他变量
以股票当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作为当月价格,以交易金额的自然对数值作为股票的交易量,以流通市值的自然对数值作为股票的规模。以月内日数据回归CAPM模型得到股票的市场贝塔,以月内日数据回归FF5模型,将回归残差序列的标准差作为股票的特质波动率。为了保证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剔除股票月内交易日少于10天的当月数据。以上一个月的收益衡量收益短期反转的程度,以股票t-6至t-2的累积收益作为股票t月的动量指标,以Amihud(2002)的测度作为流动性指标,以机构持股比例(IO)衡量股票被非理性交易的程度。
(三)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中国沪深两市除创业板之外的所有A股作为研究对象,个股和市场因子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由于Huang和Luk(2020)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从2000年1月才开始测量,因此本文的样本期选择从2000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在我们的样本期内,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加剧(如图1所示)。在2015年6月之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平均值为90.6。在2015年7月我国股票市场第二次“股灾”爆发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平均值达到192.4。在相同样本期内,上证综指波动剧烈,然而并没有呈现出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而上升的趋势,而且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系数仅有−0.017,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市场波动反馈不同的信息①在相同样本期内,上证综指波动率分别在2001年“股市大辩论”、2008年“股灾”和2015年“股灾”期间出现三次波峰。2001年“股市大辩论”是指 “海归派”认为中国股市应该挤泡沫,或推倒重来,重建完美股市;“本土派”则对前者的观点予以严厉反驳,这次大辩论对市场走势和监管政策出台都影响巨大。尽管股票市场被认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然而由于中国股票市场尚未发展到强式有效阶段,因而股票市场波动并不能完全反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信息。反过来,经济政策的出台和颁布针对财政收支、通货膨胀、产业调整以及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而不仅仅为了应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因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并不完全由股市波动所引发。。此外,中国股票市场非理性投资特征依然明显,有助于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溢价究竟是来自理性定价框架下的风险补偿,还是来自非理性框架下的确定效应。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的《2018年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50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占比为80.0%,交易频繁,一周内交易若干次的投资者占比为46.4%,并且45.3%的投资者在亏损时不及时采用止损策略。

图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上证综指收益波动率
四、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风险溢价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组合分析
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组合,分析组合的预期收益,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是否能够产生风险溢价。将所有股票按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构建5分位组合,以流通市值加权计算组合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并分别以流通市值加权和算术平均加权持有组合1个月,检验组合预期收益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为了剔除系统性风险溢价对组合预期收益的影响,以同期的系统性风险因子对组合预期收益进行回归,分析5个组合的回归截距项alpha之间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并进行Newey-West-t统计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组合分析
组合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和不同的方向,正的贝塔表明组合收益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正向的风险暴露,反之表明组合收益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负向的风险暴露。低 βEPU组合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为−3.54,高 βEPU组合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为3.50。以流通市值加权计算每个组合的预期收益,低 βEPU组合的预期收益为1.00%,高 βEPU组合的预期收益为0.67%,低 βEPU组合与高 βEPU组合之间存在−0.32%的预期收益之差,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为−4.53,即低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具有高的风险溢价,而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具有低的风险溢价。以Fama和French(1993)的市场因子、规模因子和账面市值比因子过滤组合预期收益中的系统性风险溢价,低 βEPU组合的截距项为0.38%,而高βEPU组合的截距项为−0.01%,高、低 βEPU组合之间依然存在−0.39%的差异,且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为−4.90。如果以FF三因子和Carhart(1997)的动量因子过滤组合预期收益中的系统性风险溢价,高、低 βEPU组合的截距项之差为−0.45%,且统计检验显著。进而以包含盈利因子和投资因子的Fama和French(2015)五因子模型,以及加入动量因子的六因子模型过滤组合预期收益中的系统性风险溢价,高、低 βEPU组合的截距项之差依然显著为负。以算术平均计算每个组合的预期收益,低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同样具有高的风险溢价,而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具有低的风险溢价。以系统性风险因子过滤组合的预期收益,等权计算的高、低βEPU组合截距项同样显著为负。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期股票收益。由于FF三因子、FF和Carhart四因子、FF五因子、FF和Carhart六因子模型对组合预期收益回归后的截距项结果相类似,因此本文此后以FF五因子作为基准模型。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横截面回归分析
股票收益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暴露程度可能受到股票其他特征的影响,因此首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和股票其他特征进行横截面相关性检验。在每个横截面计算股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βEPU)和股票其他特征的相关系数,并且在时间序列上检验其显著性,结果如表2所示,括号内为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Newey和West,1987)。价格(PRICE)、交易量(VOLU)与βEPU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036和−0.010,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分别为−8.880和−2.285。βEPU与规模(SIZE)、贝塔(BETA)、短期反转(REV)、动量(MOM)、换手率(TUR)、非流动性(ILLIQ)和机构持股比例(IO)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表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与股票其他特征的横截面相关性分析
二维投资组合无法同时控制多个特征对股票预期收益的影响,因此以βEPU及其他控制变量对股票预期收益进行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并进行时间序列上的Newey-West-t统计检验。

其中,Ri,t+1表 示股票在t+1期的收益,表示股票在t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Controlsi,t表示股票在t期的控制变量,包括价格(PRICE)、交易量(VOLU)、规模(SIZE)、贝塔(BETA)、短期反转(REV)、动量(MOM)、换手率(TUR)、非流动性(ILLIQ)和机构持股比例(IO)。 γ0,t是横截面回归的常数项, γ1,t是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回归系数, γ2,t是 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εi,t+1是横截面回归的残差项。
根据控制变量的选取,设计了11个回归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1,首先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βEPU对股票预期收益进行回归,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系数为−0.007,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见括号内)为−2.969,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股票收益。在模型2至模型10,分别以价格(PRICE)、交易量(VOLU)、规模(SIZE)、贝塔(BETA)、短期反转(REV)、动量(MOM)、换手率(TUR)、非流动性(ILLIQ)和机构持股比例(IO)作为横截面回归的控制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对股票收益的负向预测能力具有稳健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投资者可能对高βEPU的股票产生过度反应,从而使得t+1期的收益发生反转,导致βEPU与股票预期收益之间的负向关系。然而在控制t期收益后,βEPU的负向溢价依然存在,则意味着βEPU与股票预期收益之间的负向关系并不是由投资者过度反应所致。对于模型11,将所有控制变量加入横截面回归模型,βEPU的系数为−0.005,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为−2.304,结果依然稳健。由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与股票预期收益之间存在稳定的负向关系。

表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对股票预期收益的横截面回归分析
(三)基于行业与股权性质的稳健性检验
首先,我国发布和实施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旨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因而在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按照证监会于2012年发布的行业分类标准,剔除样本太少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与教育业,本文样本共包括17个行业。其次,由于股权性质不同,当国家政策制定部门发布和实施经济政策时,上市公司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如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民营经济扶持政策、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等会对股权性质不同的股票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按照股权性质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及其他企业三类。
接下来,我们控制股票的行业属性和股权性质,重复表3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与股票预期收益的横截面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在模型1中,控制股票的行业属性,发现βEPU的系数为−0.007,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见括号内)为−3.028。在模型2中,在控制股票行业属性的基础上,加入价格(PRICE)、交易量(VOLU)、规模(SIZE)、贝塔(BETA)、短期反转(REV)、动量(MOM)、换手率(TUR)、非流动性(ILLIQ)和机构持股比例(IO)作为横截面回归的控制变量,βEPU的系数为−0.004,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为−2.283。结果表明,控制股票的行业属性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与股票预期收益之间的负向关系依然稳定,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负向溢价并不具有行业聚集性。在模型3中,控制公司的股权性质,βEPU的系数为−0.007,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为−3.005。模型4加入股票的其他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与股票预期收益之间的负向关系依然稳定。

表4 行业属性和股权性质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溢价的影响
五、 负向溢价的机理分析
(一)基于确定效应的分析
前景理论表明投资者的风险态度是条件依赖的。面对获利时倾向于规避风险,并且卖出资产,获得确定收益,称之为“确定效应”;而面对亏损时倾向于追求风险,并且继续持有以待其变,称之为“反射效应”。(1)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是股票收益对当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当月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加剧趋势时,正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意味着当月股票收益上涨。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使得研判信息的难度和风险预期的干扰增加,持有该股票的投资者倾向于“落袋为安”,因而在下个月卖出股票以获得确定的收益,从而使股票预期收益降低,并且贝塔系数越为正,预期收益越低,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负向预测股票收益。相反,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意味着当月股票收益下跌,卖出该股票会获得确定的损失,持有该股票的投资者在确定的损失和继续持有之间倾向于继续持有。(2)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减弱时,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意味着这一时期内的股票收益为正。依据“确定效应”,持有该股票的投资者倾向于卖出股票以获得确定的收益,从而使得股票预期收益降低,并且贝塔系数越为负,预期收益越低,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正向预测股票收益。相反,正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意味着股票在这一时期内的收益为负,依据“反射效应”,持有该股票的投资者面对确定的损失倾向于继续持有。
本文按照月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趋势,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划分为加剧和减弱两个情形,并且以月收益区分持有该股票的投资者是获利还是亏损,检验当月股票盈亏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与股票预期收益的关系,结果如表5所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时( ΔEPUt>0) ,获利股票(Ri,t>0)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与预期收益的横截面回归系数为−0.013,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为−3.473,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时,获利的投资者会卖出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暴露的股票,从而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负向溢价。同时,亏损股票(Ri,t<0)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与预期收益的横截面回归系数为0.004,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为1.14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负向溢价统计不显著。
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减弱时( ΔEPUt<0),无论是对于获利的股票还是亏损的股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均不存在显著的负向溢价。对于获利的股票(Ri,t>0),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与预期收益横截面回归的系数为0.006,且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减弱时,获利的投资者会卖出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暴露的股票,使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与预期收益之间呈现正向关系。对于亏损的股票(Ri,t<0),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与预期收益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综上,获利的投资者为了规避不确定性风险,卖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较高的股票,即“确定效应”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产生负向溢价的原因。

表5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盈亏维度下βEPU的收益预测能力
(二)基于套利风险的分析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能够预期股票收益,而且具有稳定的负向溢价,这显然不符合资产定价理论“高风险具有高收益”的风险补偿逻辑。投资者往往利用经济政策利好或利空进行套利交易,进而获得较高的回报。然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对套利机会的评价和判断,从而给依赖经济政策的套利交易带来风险,因此假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是套利风险之一。
Stambaugh等(2015)、Cao和Han(2016)表明,特质波动率作为资产定价模型无法解释的异常收益的波动率,表示投资者利用异常收益进行套利交易的风险。因此,本文以特质波动率作为套利风险的代理指标,解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负向溢价。参考Ang等(2006,2009)的方法,以股票月内日收益中FF五因子模型无法解释的收益残差的标准差来度量股票的特质波动率。以特质波动率和βEPU构建5×5投资组合,分别以流通市值加权和等权持有组合1个月。控制特质波动率对βEPU组合预期收益的影响,检验高、低βEPU组合在持有期的收益是否存在负向差异,以及FF5模型回归组合预期收益后常数项是否存在显著的负向差异,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控制特质波动率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组合分析
以流通市值加权计算组合的预期收益,并且控制特质波动率对组合预期收益的影响,高、低βEPU组合预期收益的差为−0.368,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为−5.008,差异依然显著为负。以FF5因子模型过滤组合收益中的系统性风险溢价,高、低βEPU组合预期收益的常数项之差为−0.280,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为−4.614,负向差异同样显著。以等权计算组合的预期收益,并且控制特质波动率对组合预期收益的影响,高、低βEPU组合预期收益的差为−0.3133,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为−5.741,差异依然显著为负。以FF5因子模型过滤组合收益中的系统性风险溢价,高、低βEPU组合预期收益的常数项之差为−0.084,相应的Newey-West-t统计量为−5.687,结果都显著为负,因此套利风险并不能解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与股票预期收益的负向关系。
六、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定价能力
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对股票收益具有稳定的负向预测能力,因此按照Fama和French(1993,2015)的方法,买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低的组合,同时卖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高的组合,以买多—卖空获得的套利收益定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robust minus sensitive,RMS)。参照邢红卫等(2017),我们按照过去一个月以模型(1)估计的βEPU,以三种划分方式形成股票组合,并且持有组合一个月来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1)将股票分为βEPU较低的20%股票、βEPU居中的60%股票和βEPU较高的20%股票,买多βEPU较低的20%股票组合的同时卖空βEPU较高的20%股票组合(RMS20-20);(2)将股票分为βEPU较低的30%股票、βEPU居中的40%股票和βEPU较高的30%股票,买多βEPU较低的30%股票组合的同时卖空βEPU较高的30%股票组合(RMS30-30);(3)将股票分为βEPU较低的40%股票、βEPU居中的20%股票和βEPU较高的40%股票,买多βEPU较低的40%股票组合的同时卖空βEPU较高的40%股票组合(RMS40-40)。
首先,分析三种方式定义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与市场风险因子(MKT)、市值因子(SMB)、账面市值比因子(HML)、动量因子(UMD)、盈利因子(RMW)、投资因子(CMA)的基本统计量,结果如表7的Panel A所示。三种方式定义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的均值分别为0.003,0.004,0.003,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具有正的风险价格,且高于账面市值比因子、动量因子、盈利因子和投资因子。三种方式定义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有基本相同的均值,标准差也小于其他六个因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的风险价格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其次,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与其他六个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如Panel B所示,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与其他六个因子有较低的相关性。由于三种方式定义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具有相似的统计特征,后文使用RMS30-30定义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且省去下标。

表7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与其他定价因子的基本统计分析
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RMS)和其他六个因子互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检验定价因子的冗余性,结果如表8所示。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作为因变量,回归的截距项为0.003,且统计检验(括号内)显著,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并不能被其他六个因子完全解释。以市场风险因子作为因变量,回归的截距项为0.005,且统计检验不显著,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为1.080,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对市场风险因子不具有解释作用,而其他五个因子能够解释市场风险因子。以市值因子作为因变量,回归的截距项为0.008,且统计检验显著,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回归系数的统计量为0.700,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也不能解释市值因子。以账面市值比因子作为因变量,截距项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的系数都显著,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与其他因子不能完全解释账面市值比因子。分别以动量因子和投资因子作为因变量,回归的截距项不显著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和其他因子的系数都显著,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与其他因子能够完全解释动量因子和投资因子。以盈利因子作为因变量,回归的截距项为0.005,且统计检验显著,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回归系数的统计量为0.485,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也不能解释盈利因子。因此,在我们考虑的六个因子基础上加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后,动量因子和投资因子都成为了冗余因子。

表8 定价因子轮流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续表8 定价因子轮流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为了比较不同因子的定价能力,在每个月分别按照规模(SIZE)和动量(MOM)、规模和非流动性(ILLIQ)、动量和非流动性构建独立5×5组合,以包含不同因子的定价模型对组合收益进行时间序列回归。依据Fama和French(2015)评价模型定价效率的方法,选择GRS联合检验统计量(Gibbons等,1989)、组合收益回归截距项绝对值的平均值 |ad|、 截距项绝对值的平均值 |ad|与组合收益偏离平均收益的偏差 |τd|之 比(其中是组合d收益的时间序列平均值,是的算术平均值)、模型拟合的均方误差(mean square error,MSE)和调整R2为标准检验模型的定价效率,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的定价效率
在Panel A,对于5×5规模和动量组合(SIZE-MOM),包含FF3因子、盈利因子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的定价模型的GRS统计量为1.885, |ad|为 0.002, |ad|/|τd|为0.554,MSE为0.001,调整R2为0.943,与其他模型相比,有更小的定价误差和更好的拟合程度,表明有更好的定价效率。在Panel B和Panel C,对于5×5规模和非流动性组合(SIZE-ILLIQ)、5×5动量和非流动性组合(MOM-ILLIQ),无论是反映收益未被解释程度的GPS统计量、 |ad|和 |ad|/|τd|,还是反映模型拟合优度的MSE和R2,包含FF3因子、盈利因子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的定价模型都表现出更好的定价效率。
七、 结论与启示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和稳定发展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既要发挥经济政策在化资源配置、刺激市场信心等方面的宏观调控功效,更要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本文选择我国股票市场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将股票收益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回归的系数贝塔作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暴露。依据资产定价理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应该要求正的风险补偿,然而实证结果却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会产生显著的负向溢价,并且这一结果不能够被股票的其他特征、行业和股权性质所解释,所以投资者并不能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暴露中获得风险补偿。
我们发现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时,获利的投资者为了规避不确定性,会减少投资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暴露的股票,从而使其产生低的预期收益,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负向溢价是由投资者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时的“确定效应”所致。我国股票市场常被视为“政策市”,投资者也往往利用经济政策进行套利交易,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给这种套利交易带来风险,因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属于套利风险的某个维度。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控制套利风险也不能消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的负向溢价,可见投资者并不轻易选择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敏感的股票作为套利交易对象。进一步,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贝塔构建定价因子,发现包含FF3因子、盈利因子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子的五因子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具有更好的定价效率,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资产横截面收益中的定价能力。
我们的研究表明经济政策具有“双刃剑”作用。长久以来,积极的经济政策已经在优化资源配置、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加快经济体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展现出显著成效。然而在国际经济环境大变革的背景下,更应关注经济政策的二阶矩层面。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产生负面的经济后果,不利于引导投资者恢复信心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面对全球防疫形势严峻、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国际贸易争端升级等诸多挑战,有必要在宏观审慎框架下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经济政策在颁布上要适时适度,在操作上要精准有效,在持续加大支持力度的同时保证投资者群体的信心和活力,为维护金融市场流动性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