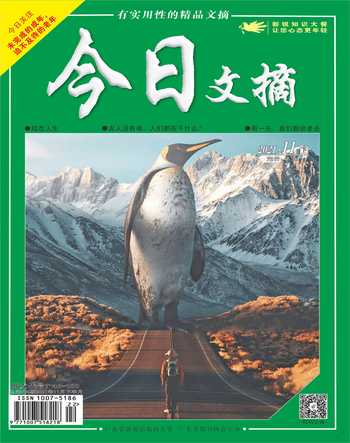变与没变
孙道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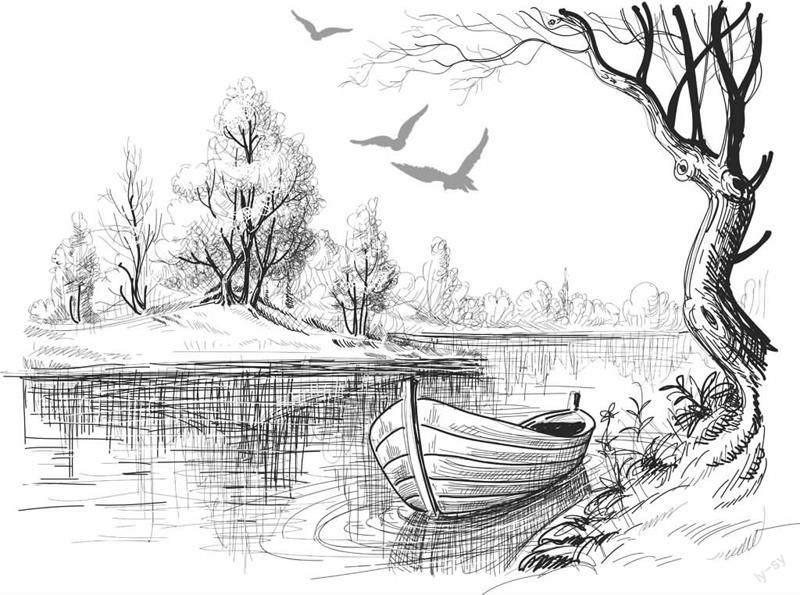
大塘是村里最大的一口池塘。还有两个池塘,一个在南,叫南塘,一个在北,叫北塘。大塘离村最近,又最大,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我们的夏天,都是泡在里面的。最厉害的小黑子憋一口气,一个猛子,能从大塘的这头钻到那头。若干年后,我回乡,路过大塘,惊讶地发现,大塘怎么变小了?问村里的老人,老人说,变了吗?没变啊,一直都是这样的。
老人在村里生活了八十多年,天天在这个水塘边,洗衣,淘米,挖藕,捉鱼,他说没变,肯定是没变吧。我感觉它变小了,可能是我很多年没有见到过它了,以一个孩童的眼光来看,它是大的,当你离开它,在外浪迹了几十年后,再回头看它,它就似乎变小了。随着年龄渐长,每次回乡,這种变与没变,感受日深。
小时候,看到村里全是小孩,邻居家的虎子和狗子兄弟,村西头的大平和小平,村北头的小黑子和他两个妹妹……这都是我的小伙伴,村里奔跑的,全是他们的影子和他们的哭笑声。村里没有大人吗?大人都下地干活了,再说,你是去找小伙伴玩的,看到大人有什么用,他会放下锄头蹲下来陪你玩石子吗?看到了跟没看到一个样,遇到了跟没遇到一个样。现在回村,看不到几个小孩了,小孩子在学校上课,或者跟着他们打工的父母进城去了,我看到的,都是拿把椅子,坐在自己家墙根晒太阳的老人。也只有他们看到我,认出我小时候是这个村里的人,他们会拿把椅子,让我坐一坐。
村口有棵老榆树,小时候觉得它很大,很老,现在回村,看到它,它还活着,还是很大很老。村里其他的树,都是我离开村庄后栽种的,我不认得它们,就像它们也不认得我。而我小时候在村里看到的其他的树,有的被锯了,做成了家具,或者当柴火烧了,肯定也有那么一两棵,我小的时候,它还是小树苗,现在,它长大了,我已经认不出它了,它也压根儿记不得那个调皮的男孩,对着它的根撒过尿了。
小时候,村里的狗,都是土狗,名字也差不多,不是叫小黑,就是叫大黄,就像我们这些孩子,我们的名字,也不是叫黑蛋,就是叫狗头。我们和狗,都常常吃不饱肚子,瘦骨嶙峋,谁也不会笑话谁。现在回村,我几乎看不到土狗了,很多人家,也早就不养狗了。但村里的狗还是有的,我就看到两只小的京巴,还有一只大的金毛,老邻居老刘告诉我,这是那些在城里上班或者打工的年轻人,寄养在老家的,它们都有洋气的名字,家里的老人记不得它们的名字,就想给它们改个名,叫小黄或者大黄,但那些从城里来的狗不答应,也不知道它们习惯了叫吉吉、托尼,还是嫌小黄和大黄土气。到了长假,城里养他们的人,就会来看他们的狗,还有年迈的父母。
孩童时代,夏天的夜晚,大人们扎堆,聊收成,家长里短,我们也跟着扎堆,玩石子,玩泥巴,听大人讲鬼故事。现在回乡,我看不到扎堆的人了,坐在高板凳上的大人在玩手机,坐在矮板凳上的小孩,也在埋头玩手机,他们和城里人一样,各在各的家,各玩各的。玩累了,大人去做饭,小孩去做作业,偶尔听到一声狗叫,不是土狗汪汪的叫声,而是那种捏着嗓子一样的小狗的尖锐叫声。
我离开村庄已经很多年了,每次回乡,我从村口走进,又从村口走出,路过那棵老榆树,路过那口大塘,有时候感觉跟几十年前一样,很多东西没变,它还是我的村庄;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像个迷路的人,这里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我能轻车熟路走进我的村庄,却再也走不回我的童年。
(吴兴发荐自《思维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