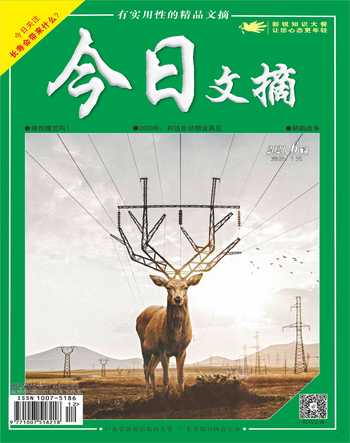长寿会带来什么
梁静怡

美国记者约翰·兰莱德有一份6人的采访名单,每当打电话无人接听时,他开始担心——这意味着可能又有一人去世了。
从2015年开始,这份名单像是一个黑洞,截至2020年年底,仅剩一人。原因无他,名单上都是超过85岁的老人。
一开始,约翰对这群人感兴趣,只是因为“踏入85岁后,这群人在社会上似乎就销声匿迹了,他们的生活是不被看见的”。可这一群体正迅速增长着,世界卫生组织预测,80岁或80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将在2000至2050年期间达到3.95亿人。就连约翰自己的母亲,在2015年时也跨过了86岁,他们有了自己的名字——“最老的老人”。
约翰不知道这群人的真实生活,也不知道该如何和母亲相处。“我们都没有为我们即将携手闯入的人生阶段做好准备。86岁高龄的她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所在,而我则不知道该如何施以援手,但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困境。”约翰写道。
采访前,他庆幸自己年轻,和他们相比,“我想,至少我还不老”。他自嘲,一开始自己像讨厌的新闻记者那样,总想着表现苦难,只想展现人到老年的悲惨和艰难,“有没有这样一道门槛,跨过去之后,人生的价值就逐一丧失?”
然而,在和这六位老人共处一年后,约翰颠覆了自己的想法,并把经历写成书《长寿的代价——我和六位老人共处的一年》,让这些“最老的老人”去回答那些关于失去、爱与死亡的困惑。
失去:从记忆到身体
约翰第一次见到黄萍就印象深刻,这位89岁的老太太来自香港,照片中的她齐耳短发,戴着耳环,微微发福,她每月付200美元租金,住在公园附近的福利房里。
和约翰聊天时,黄萍有着固定的对话模式,总是简短地介绍生活经历,加一段人生建议,最后以麻将作为结尾。她的一天用麻将来填满,约翰发现,黄萍和楼里的女人们打麻将时几乎一声不吭,她解释:“麻将靠打不靠说。我们没有精力顾别的,只能打。”
这位老人到美国生活三十年了,丈夫和姐妹早已去世,没有储蓄,靠每月的保障福利生活,唯一的儿子在广东意外去世。说到儿子时,她流泪了,告诉约翰,自己曾经有两年整夜难过得睡不着觉。
这一年,约翰见证了黄萍逐步失去记忆,不管是讲英语还是粤语,愈发地颠三倒四,有时急匆匆地把约翰叫到面前,却忘记自己要说什么。“她缓缓站起身,环顾房间,好像在为自己失去思路而感到惊讶。它跑哪里去了?”约翰写道,这是否意味着她明天会忘记更多东西,忘掉更多的人生碎片?
可黄萍却似乎对现有生活很满足,她还想要学英语,觉得新换上的油毡很好看,她的熟人圈子很小,但每个人都很重要,打麻将就是重要的事。
有研究显示,老人比年轻人更快乐。对此,约翰充满了困惑,像黄萍这样的老人,“为什么比似乎拥有全世界的年轻人更热爱生活?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千疮百孔了吗?”
他尝试去找原因,在一项研究中,老人和年轻人被提供同样多的画面,然后回忆复述,老人记住的正面画面是负面画面的两倍,而年轻人则是正面与负面一样多。另一项研究发现,老人更善于记住令人愉快的信息。虽然老人关于新近发生的事情记忆会消失,但童年那些快乐小事却愈发清晰。
约翰认为,黄萍们都采取了对生活的选择性记忆,只记住那些美好快乐的事。“你45岁时,记住婚姻或事业中犯过的所有错误是有好处的,这样你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但到了90岁,更好、更明智的做法是遗忘。”约翰写道。当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时,不再需要这些教训,只需要记住美好的事情,“失忆,成了一种优势”。
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黄萍能渐渐从丧子悲痛和前半生的艰辛记忆中走出来。每当约翰问起遗憾时,她总是摇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像大多数老人一样,黄萍不仅仅失去了记忆,也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和自由。2015年,她计划和女儿去大西洋城旅行,可是对于患有风湿的她,3小时的车程太长了,只能放弃。她一度感到绝望,面对日益孱弱的身体,她说:“有时候想死,90岁了,活得够长了。”可和约翰聊了一会儿,她似乎又变得积极向上了。
对于黄萍这些超过85岁的老人而言,他们看待事情的方式与年轻人不同。他们早已意识到,生活永远不会十全十美。年轻人常常用的句式是“只有……才会快乐”,也许会因失去一次旅行沮丧很久,但对老年人,他们习惯了,更倾向于采用“尽管……还是快乐”的句式——尽管没能去旅行,但黄萍觉得自己能够打麻将,还是很快乐。
黄萍失去了儿子、亲人、记忆,甚至控制自我身体的自由,但她“教会我的是,从未用失去来定义自己的人生”。
忙于去爱,仿佛没有明天
拜访老人们时,约翰正处于一场中年危机中,将近30年的婚姻解体,他还记得当妻子若无其事地提議离婚时,自己站在厨房的水池边,甚至没有停下手中洗碗的动作。
他形容自己的婚姻是一辆没油的汽车,在路上开了很久很久,所以到处是伤。“抬脚走开是个轻而易举的决定。”约翰写道,“我意识到,该失去的多年前就失去了。”后来尽管他新交了女朋友,却不知该如何维持一段关系。他是带着困惑找到海伦·摩西的。
这位90岁的老太太不顾女儿的反对,在养老院找到了比自己小21岁的挚爱豪伊,谈了一场6年的黄昏恋。
在这段关系中,豪伊是依赖仰慕的那方。海伦虽然大了21岁,但活跃、外向,每天涂口红。而豪伊没有亲人,不善言辞,需要别人照顾,海伦于是拉着他的手看电视,每次她一转身,豪伊一定在身边。
6年恋爱里,他们从未吵过架,海伦总是照顾着他,努力成为豪伊的一切。关系看似是不对等的,在生命燃烧将尽之年,重新发展一段关系,意味着把新的义务和责任重新加在两位老人身上。但这段关系,让海伦的生活重新有了方向和目标。“她在重新扮演使她人生具有意义的角色,”约翰写道,“而不是没有用的老人。”
在约翰看来,海伦和豪伊摆脱了那些婚姻关系中的固定思维——不断去质疑所谓的是否给予太多或回报太少。“在一段关系中,有时索取也是一种给予。”此时,对于海伦和豪伊来说,“快乐就是养老院里的老妇人有个坐轮椅的伴侣,第19遍为她讲同样的故事”。
当然,并不是所有老人都能拥有海伦豪伊似的美好恋情,残酷的现实是,年过85岁后,只有27%的人有伴侣,剩下的人伴侣去世或者独居,一个人度过余生。
90岁的迈克便是其中之一,伴侣离去后,迈克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他会感觉对方还在。约翰认为,伴侣活着的时候是老人,中年人或年轻人,但去世后,是所有身份的合体,在迈克的记忆里活着,他永远记住的是对方美好的一面。“活着的时候,一个人的伴侣往往是乏味或者平凡的,但在记忆中,绝对不是。”
不管对方是否有不足和缺点,他们都曾经或正在拥有着对方。
“也许只有年轻人才有资格认为最佳伴侣是下一个,一个你尚未见到的陌生人,或者是现有伴侣的升级版。年轻人更看重未来和幻想。”约翰写道,“老人们没有时间去妄想,包括妄想自己还有更多时间。他们忙于去爱,仿佛已经没有明天。其实,对我们任何人来说,可能都没有明天。”从养老院返回时,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中,约翰反思自己的婚姻。
现在的他,会打电话给女友,告诉她“我爱你”。他会在早晨亲吻她,“不是因为她完美,而是感恩她是她,出现在我身边”。
只有年轻人以为自己不会死
2011年,约翰的母亲因为一次脊椎手术差点离开人世,又老又弱的她在感染暴发时,身体毫无抵抗能力,她要求“放弃抢救”,离开这个世界。当弟弟通过嘈杂不清的信号连线正在伊拉克做报道的约翰时,他们需要抉择母亲的生死,可说到一半就听不见了。最终,为了救下母亲,弟弟同意插管。可后来,母亲一直责怪弟弟没有让她离去。
每次聊起这个话题,老人们对死亡的態度总是很淡然。约翰解释说:“目睹了伴侣的死亡,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知道发生在伴侣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他们没有任何幻想。”
一开始,迈克也曾提出想要早点离世,约翰总是说,自己希望他不要走,如果没有他,世界会更加乏味。可是不过一年,看着迈克日益衰老和疾病缠身,付出越来越多的代价才能享受得之不易的一丁点回报时,约翰不再对他说希望他别死了。“到了冬天,我已经不再想这件事,”约翰写道,“让那些根本不想永生的人勉强得到一种打折扣的永生,这并不是善意。”
没等这本书写完,电话簿里的黑洞就出现了,迈克、黄萍、一个又一个老人离开了人世,截至去年年底,仅剩下一位了。就在一个多月前,约翰91岁的母亲也去世了。
当时因新冠肺炎全城封锁,约翰的兄弟不能赶到母亲身边,只有约翰陪着她。在最后时刻,约翰不再恳求她留下,而是在母亲身边耳语,告诉她:“离开是可以的,我们会永远爱你,妈妈。”
约翰平静地接受了他们的离开,因为他意识到:“死亡并不需要去打败,并不是运行的系统出现了问题,而是这就是运行系统的一部分。我们皆凡人。”
与六位老人相处的这一年让他接受死亡,并庆祝生命。约翰说:“我每天醒来,更感激生活,感激可以再次看到树上美丽的树叶,可以和从未见过的人交谈。因为,它们都不会重来。”
“这是心灵鸡汤吗?”我问约翰。
“我知道年轻人可能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以为自己年轻,带着年轻人的傲慢。”约翰说,“只有年轻人认为自己不会死,或者变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如果有机会给自己写一段讣告,约翰想写:“在这疯狂的世界里,我希望能找到一种生活在其中的方法,并尽了最大的努力与人分享。在这过程中,我收获很多,有的来自我所写的六位老人,而有的,来自我一直与之相处的人。”
约翰今年61岁了,他不再害怕变老、失去,他重新认识相爱和死亡。六位老人和母亲教会他——年龄,仅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
他没有想过自己85岁时的样子。“我仍然在探索,会成长,会学习,”约翰说,“我以同样的方式期待明天,像期待25岁时那样。”
(郑文斌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