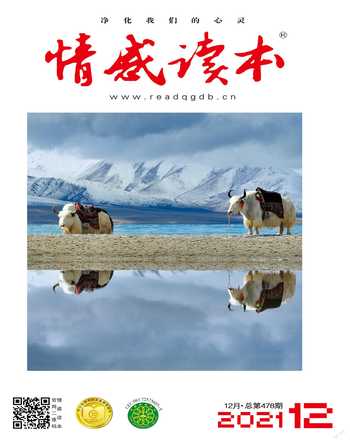母亲知道的事
约翰·达纳卡斯

我没细问母亲,但从她眼中的光芒来看,母亲对我持肯定态度,我感觉喉咙有些哽咽。
2020年春天,温尼伯市第一次开始封城,每天照顾老母亲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因为我是独身生活,又已退休,可以踏实地呆在家里陪她,确保她的安全。弟弟和弟媳负责每星期给我们买些日用品,送来后放在门口就得回去,他们还负责每个月给母亲理一次发。
母亲88岁了,自己在家生活,父亲12年前就已去世。母亲晚年生活是幸福的,她有我和弟弟这两个儿子,还有三个孙子和孙女,住的地方离她不远,我和弟弟也偶尔就来看她。尽管如此,我不敢说陪她就会顺利。我和母亲一直性格不合,如今我已50多歲,和母亲相处仍然令我憷头。母亲讲究规矩礼节,我喜欢随心所欲。我们俩都挺能说,但是两个人经常话不投机。
母亲喜欢看一个希腊综艺节目,开始陪母亲的几天,我每天选择她下午看电视的时间去看她,看着电视没话找话。如果想知道节目里某个歌唱家的详细信息,我就拿着智能手机查,每次都能查到。母亲惊奇地说:“那个小东西怎么啥都知道?”
不过等到关掉电视,我发现有些事母亲知道,网络上没有。不久我就放下了手机,有事宁愿问母亲。比如母亲说,二战时德国占领她的家乡希腊斯巴达时,德军士兵们每天下午都会晒日光浴;母亲还知道怎样烹调蒲公英,既让它的刺不扎嘴,又不会因为熟过头而失去鲜味。母亲还给我讲了她小时候家里的一些事,比如她小时喜欢爬树扔石子、她的两个叔叔死于流感病毒、她嫁到加拿大之前只看过一次下雪,还有就是,我的父亲曾经诚恳地给他的岳母买了副假牙,这件事让母亲一生欣赏。
我听得入了迷,从此我每天两次看望母亲。
封城第12天,母亲房子里的电话线路不通了。我向电话公司报了修,得到的回复是至少要等一个星期才能修复。电话公司的人很惊讶妈妈连手机都没有,他们建议我给母亲买一部手机。
我和母亲开玩笑:“电视台会教80岁以上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母亲没觉得好笑,我们放弃了买手机的想法。但是万一她自己在家时需要帮助,怎么和外界联系成了问题。我们商量了一下,最好的办法是我先搬来和母亲同住几天。
没想到,这几天非常顺利。我不怎么会干活,但还是笨手笨脚地给母亲的房子换了个灯泡,给她的眼镜安上一个螺丝,好让她戴眼镜刷假牙。
我们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挺紧,我每天陪母亲到门外街上溜达一趟,回来做那一堆家务,然后就是继续陪母亲聊天。
一天晚上9点,到了关电视睡觉的时间,母亲忽然转过身对我说:“现在我看到你的孝心了。”
我没细问母亲,但从她眼中的光芒来看,母亲对我持肯定态度,我感觉喉咙有些哽咽。
陪母亲住进入第二月,母亲的电话修好了,一天下午,我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我马上过去。电话没人接。我感觉不妙,又马上告诉自己不要胡思乱想。我开车到了母亲家门口,敲门没人答应。这下我可真慌了,我给弟弟和住在后面那条街上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疫情发生前,母亲常去那条街散步。我在车上找到了钥匙,回来开了房门。我检查了楼上的屋子、地下室、洗手间,都没看到母亲。
我出门上车,沿街道开着车往前找,希望有警察正在帮母亲回家,可是没有。
我把车拐进一座商场的停车场时,忽然看到母亲正在旁边的一条便道上溜达,只见她戴着一副太阳镜,手里提着一个购物袋。
我长出了一口气。“我带你回家。”我对母亲说。
“谢谢,我能走,我只是想自己做些事。”母亲说。
我笑着说:“我都要报警了。”
“不用担心,以后我就不自己上街了。我不喜欢新规矩,我拿出钱包,收银员说他们现在不收现金。”
如今一年过去了,疫情还未结束,去年加拿大冬天那几个月对母亲来说是最难熬的,她不得不一直憋在家里。在那个寒冬,母亲的几个老朋友相继去世了。母亲有时会念诵几句伤感的诗,也许对于一个90岁的人来说,生命的终点会感觉很近。
母亲盼望着疫情结束,她想着和以前一样享受儿孙绕膝前的快乐。母亲的冰箱里存放着蛋糕粉,那是她留着给我们做希腊馅饼用的。
我们这代人习惯了,等到父亲住进医院甚至即将走到生命尽头,我们才去看他们。现在我知道,在父母活着的时候陪他们才是最有意义。疫情尚未结束,陪伴母亲这些日子成了我一生中最感荣耀的时光。
我也相信,陪伴母亲还会给我的“孝心”加分,每想至此,我都会很开心。
夏熙志摘自《生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