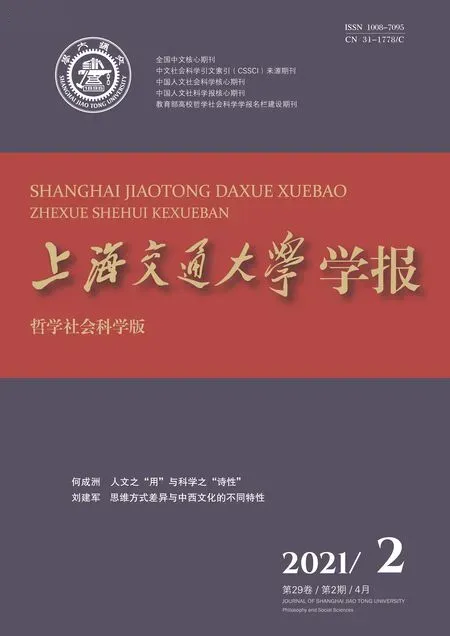科技人文与中国的新文科建设
——从比较文学学科领地的拓展谈起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科技人文(techno-humanities)应该说是当今学界为人们讨论得颇为热烈的一个新话题,至少在人文学科诸领域内是如此,即使在英语世界这一概念也和数字人文一样依然方兴未艾。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人们热烈地讨论新文科建设时难免不提及这一话题,也即一般认为,新文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跨越传统的人文学科的界限,但至于跨越到何种地步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这至少让人们难以否认,面对全球化时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商业大潮的冲击,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地越来越呈萎缩的状况,它确实应该经历一种革命性的转折,尤其是应该注入一些科学技术的成分。这样看来,科技人文这个话题就被人们提到学术研究的议事日程上了。那么人们也许会问这样一些问题: 究竟科技人文指的是什么呢?难道它只是科学技术加上人文吗?显然不是如此简单的一种相加。但是如果不是如此简单地等同于这种相加模式的话,那么它又意味着什么?再者,科技人文是否可以算作一种研究范式,还是一种方法?在笔者看来,科技人文作为一个全新的理念,它的出现完全是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高科技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给我们人文学者提出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命题: 我们的学科将如何得以幸存?它应该朝着何种方向发展?所谓“十年磨一剑”式的“坐冷板凳”从事研究的传统的人文学科应该成为历史了。具有转折和范式意义的新文科已诞生,在这一过程中,科技人文所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因此,科技人文命题的提出绝不只是科学技术加上人文,而是可以同时含括这二者,并达到其自身的超越。新文科理念的诞生就是这种超越的一个直接成果。因此,它更具有范式的意义和引领作用。
我首先要加以界定的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科技人文意味着什么。如果说,美国当代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1922—1996)于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1962)标志着一种科学研究范式的确立的话,那么当前我们所要讨论的科技人文则可以算作是新时代中国学界的又一种科学研究的范式。如果说前者的作用主要之于科学研究的话,那么后者的作用则主要之于人文学术研究。关于何谓“范式”,人们有着不同的说法。在库恩看来,一方面,所谓范式就是对人们习惯认为的“常规科学”的突破和超越,也即它应当能够引领新的科技革命,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去践行,以便不断地在实践中取得新的突破和超越。另一方面,它又有足够的能力为后来的践行者提出问题,使他们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即,诚如库恩所坦陈的,“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第4版[M].金吾伦,胡新和,译.2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序4.由此可见,一方面,范式是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成功的和切实可行的经验之总结。一种范式一旦确立,就在一定的时期内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另一方面,范式的确立也可以为一个学科奠定长久的发展路径,并为之指明新的发展方向。这在西方学界是如此,在中国学界也基本得到人们的认可。针对该书出版后所引起的广泛讨论甚至辩论,库恩在1969年的修订版中对范式又作了进一步修正和发展:
“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第4版[M].金吾伦,胡新和,译.2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47.
担任该书第4版“导读”的学者伊安·哈金也对之作了说明,“库恩认为,科学革命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具备某种结构。这种结构在书中被库恩小心翼翼地展开,结构中的每一个节点都被库恩赋予了一个有用的名字”。(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第4版[M].金吾伦,胡新和,译.2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序4.我认为这是对该书核心观点十分中肯的概括。
作为一位研究兴趣较为广泛的人文学者,我从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之日起,就经常不满足既定的学科规范,试图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尝试一些突破和超越。我深深地知道,不要说我所进入的人文学科的诸多分支学科领域壁垒森严,就是我所安身立命的学科文学研究也是理论思潮纷呈,学派林立,要想在某一个分支学科领域内取得一点突破绝非易事。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我深有体会。因此在讨论新文科与科技人文之前,我不妨将我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的探索和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与广大读者分享。
熟悉我学术生涯的人大多知道,我本人所从事的学科专业主要是比较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因此我的“跨学科”尝试主要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通过多年来的探索和实践,我深深地感到,要想在一个壁垒森严的学科领域进行哪怕是那么一丁点的突破都是十分艰难的。我清楚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还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三个月。其间我接触到了港台和海外的一些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意识的学者,在与他们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我不禁萌发出一个不成熟的“跨学科”想法: 既然国内外的比较文学学者都十分熟悉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曾经为比较文学所下的一个十分宽泛的具有跨学科特征的定义,也即雷马克首次将比较文学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其他艺术表现领域的比较研究,(4)关于雷马克的宽泛并引来广泛争议的比较文学定义,参见: Newton Stallknecht and Horst Frenz, e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 and Perspective[M].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1: 3.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某种狭义的研究范式的转向呢?就其吸引了整整一代东西方比较文学学者潜心践行这一点而言,雷马克的定义所起到的作用无疑具有研究范式的意义。那么我们为何不能据此出发,并结合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对之作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描述呢?于是我在大量阅读了港台和国外学者的著述后,参照中国的人文学科研究传统,写下了一篇题为《比较文学: 走向超学科研究》的论文,投给了上海的一个专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刊物。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篇文章还比较稚嫩,主要涉及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科学以及文学与(处于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的比较,并没有斗胆涉足科学技术,而且受篇幅所限对前面所提出的几种跨越学科界限的比较文学方法也未作深入的阐发。但是至少在那篇文章中,我率先在中国的语境中提出了比较文学的超学科研究,并得到了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杨周翰等人的首肯。(5)乐黛云,王宁.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此外,我提出的超学科研究也不同于美国学者那种漫无边际的跨越学科界限的比较文学研究。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就在于,比较文学必须突破当时的接受—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雄并立的模式,超越影响/平行之二元对立,达到超学科的境地。但是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无论跨越什么界限,都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最后的结论还是要落实到文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上,这样才能算得上是一部比较文学的论著。(6)王宁.比较文学: 走向超学科研究[J].文艺研究,1988(5): 143-148.这一点同样可以适用于今天的科技人文研究,也即科技人文无论跨越何种边界,最后的落脚点仍应当是人文,它提出的结论一定要有助于人文学科的建设和人文学术的发展。若非如此,这样的科技人文就是失败的。
但是文章投出去之后,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并且有一种预感,由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三十岁出头的青年学者提出这样一种文学研究的范式是否会有人响应或跟从,或者进一步推论,那个档次很高的刊物是否会将其发表?所谓“人微言轻”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果不其然,文章很快就被退稿了,理由就是这样一种大的宏观论述比较空泛,不应该由一个小人物来做,对于一个刚步入比较文学领域不久的青年学者,应该首先写出有着扎实研究基础的论文,这样的宏观理论描述应该由本学科的权威性学者来提出。我想,今天不少致力于宏大叙事和新理论概念建构的中青年学者都会碰到同样的遭遇,并且有着同样的切身体会。
好在人文学科既然有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主观性判断之特征,那么我始终坚信,在当今时代,一种有着深入思考和研究基础及理论依据的建构完全有可能觅见知音并得以发表。一篇文章被一家档次较高的刊物拒绝,完全有可能被另一家更具权威性的刊物接受。就在我回到北京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和另一家更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刊物《文艺研究》的副主编吴方的交谈中,我顺带提及了这篇文章。素来具有理论敏感性和前瞻性的吴方立即敏锐地感觉到,我的这篇文章将开辟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于是要我将文章寄给他。后来他和另一位副主编张潇华审读后一致看好这篇文章,并推荐给了主编。该文作为《文艺研究》文学栏目的首篇文章发表后我确实多方受益: 首先是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社的《文艺理论》卷将其作为那一期的首篇全文转载,我提议编辑的一本专题研究文集《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与乐黛云合作主编)也很快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白烨的青睐,被迅速列入选题计划,并于1989年我获得博士学位的那年出版。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比较文学史和比较文学教材的编写者在提到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向时,都免不了要提到我的那篇并不太成熟的文章和那本专题研究文集。

相比之下,美国学派在注重文学的平行研究的同时,从一开始就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和跨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面对全球化时代精英文学及其研究领地的日益萎缩,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苏源熙(Haun Saussy)依然坚定地认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赢得了战斗,它从未在美国学界得到更好的认可”。(8)Haun Saussy,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M].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3.照他的看法,比较文学在与各种文化理论思潮的博弈中最终还是幸存了下来并得到长足的发展,“争论已经结束,比较文学具有合法性,而过去则不太具有合法性,此时我们的学科扮演的是为乐团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我们的结论已经成为其他人的假设”。(9)Haun Saussy,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M].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3.不难看出,苏源熙在说这话时确实充满了自信和底气。
如果确实按照苏源熙的看法,比较文学在美国的人文学科研究中起着领军(第一小提琴)的角色的话,那么我们从比较文学学科领地在中、美、法三个重镇的拓展及其在当今时代的发展状况中不难发现,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下强调新文科建设,并呼吁传统的人文学科注入科学技术的因素也并非空穴来风,它也有着一定的国际和国内背景,符合人文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始终注重总结经验和提出问题,他们每隔十年都要邀请一位该学科领域内的著名学者为本学科的现状及未来发展编写一个十年报告,从而起到为本学科研究“导航”的引领作用。最近的一个十年报告由专事生态和环境研究的学者乌苏拉·海斯(Ursula K. Heise)主持,她是美国学界有名的先锋理论家和跨学科学者。她在报告中回顾了比较文学最近十年来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学界的发展现状及态势,并预测了在未来的发展走向。但是面对近十年来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在跨越人文与科技界限所取得的微不足道的进展,她在导论中不无遗憾地指出:
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比较文学在把各种理论介绍给文学和文化研究时所扮演的开拓性角色相比——那时它几乎与文学研究的理论分支领域相等同——它近期在一般的人文学科和特定的文学研究领域的创新中却未能扮演主要的角色。甚至在对之产生了主要影响的那些研究领域,例如生态批评,比较文学也姗姗来迟,而在诸如医学人文学科这样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者则刚开始涉猎。(10)Ursula K. Heise.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Humanities[M]// Ursula K. Heise ed. Futur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LA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Repor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6.
显然,较之前一个十年报告的主持者苏源熙,海斯对当今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现状并不十分看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与美国的其他人文学科领域相比,曾经率先提出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和范式的比较文学学者的跨学科意识虽然很强,但是在满足于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跨界比较研究的同时,却在科技人文这个新的领域内姗姗来迟,并且著述不多。这显然与长期以来人文学者所受到的多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的训练不足不无关系。这应该是当今的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介入科技人文时所暴露出的一个先天性的不足,值得我们今天在中国的新文科建设中倡导科技人文时加以借鉴。
以上我之所以花了这些篇幅描述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只是想说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新文科的跨学科模式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扎实的研究基础和理论依据的。关于新文科之于中国的外语学科建设之意义,我在另一场合已经作过专论,(11)王宁.新文科视野下的外语学科建设[J].中国外语,2020(3): 4-10.此处毋庸赘言。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温库恩的那本曾在学界产生振聋发聩之影响的著作的核心概念——范式之于我们今天确立科技人文之新范式的意义。正如库恩在讨论范式的优先性时所指出的,一种范式的确立就如同一个新理论的提出那样:
一个新理论总是与它在自然现象的某种具体范围的应用一道被宣告的;没有应用,理论甚至不可能被接受: 在理论被接受以后,这些应用或其他的应用就会伴随着理论写入教科书,未来的从业者就会从教科书中学习他的专业。这些应用在教科书中并非纯粹作为点缀品或历史文献而已。正相反,学习理论的过程依赖于对应用的研究,包括用铅笔与纸和在实验室中用仪器来解决实际问题。(1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第4版[M].金吾伦,胡新和,译.2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9.
科技人文也是如此,它作为一种范式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被应用于人文学科的一些分支学科,(13)关于科学技术之于比较文学的作用,见Wang Ning. Introducti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Literary Studies[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20, 57(4): 585-594.而它也应当能引领未来总体的人文学科研究,使之摆脱传统、单一的“人文性”或“主观性”,加入一些科学的因素。此外,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科技手段的引入也可以使得传统的人文研究更加具有规范性和可效法性,(14)这一点尤其可在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运用大数据的手段对世界小说的研究中见出端倪。这方面可参见冯丽蕙.莫瑞提的远读策略及世界文学研究[J].文学理论前沿,2021(1).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既具有科学特征同时又保留人文情怀和属性的学科门类。关于这两点我在结束本文之前略加阐述。
首先,科技人文提醒人文学者注意,如果我们不否认我们所驻足并得以从事学术研究的领域是一个学科的话,那么这个学科的存在价值和发展前景就必须经得起学术同行以及相关学科的学者的评估,也即我们的研究成果既要对同行学者有着引领作用,同时也可以为相关学科的学者提供方法论和学术范式方面的启迪,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担当得起一流的称号。那种认为人文学科不需要进行评估的说法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在对具体的人文学者及其成果的评价方面,除了主要依赖同行专家的定性评价外,也应该引入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客观地评估一位学者及其成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如果局限于国内就得测评其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和所得到的同行关注度;若这种影响力具有广泛的国际前沿性,那就得依赖其在国际范围内的客观影响和所得到的国际同行的关注度。
总之,科技人文理念的提出必将对我们的新文科建设有着巨大的帮助和推进。我对此充满了信心,并将一如既往地砥砺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