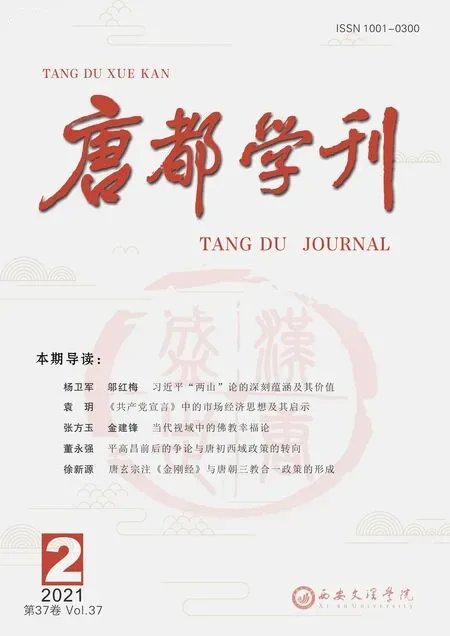唐玄宗注《金刚经》与唐朝三教合一政策的形成
徐新源
(京都大学 人间·环境学研究科,日本 京都 606-8316)
儒、道、佛三教合一是中国宗教史上的重要命题,事实上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曾像唐朝那样在政策上强调三教合一。唐玄宗时期,为了平衡知识界、宗教界的势力,稳固统治,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以注三教经典的方式,完成了对三教政策的确认。《御注金刚经》在开元二十三年(735)最后颁布,标志着三教合一政策的最终成形。
一、唐玄宗注《金刚经》史事考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六月三日,时任都释门威仪的僧人思有上奏一表,请唐玄宗注《金刚经》(1)房山石经本《御注金刚经》第一面底部题记云:“开(元)二十三乙亥之岁六月三日,都释门威仪僧思有表请。至九月十五日经出,合城具法仪,于通洛门奉迎。其日表贺,便请颁示天下,写本入藏,宣付史官。……天宝元年八月十五日立。”中国佛教协会《房山石经》隋唐刻经第三册,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337页。。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译名),是初期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之一,也是般若类佛经的纲要书。尽管不如禅宗极盛期时那么流行,但公元735年的中国,《金刚经》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2)《金刚经》的六个汉译本此时已全部问世,译者分别是姚秦鸠摩罗什、元魏菩提流支、南朝陈真谛、隋达摩笈多、唐玄奘和唐义净。其中最晚的义净的《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译成于702年。唐玄宗所注为鸠摩罗什译本。而唐玄宗以前就有慧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并注》、窥基《金刚般若经赞述》《金刚般若论会释》等多个注疏。。其实在这之前不久,有志于文治的玄宗已经分别在开元十年(722)和开元二十年至二十一年(732—733)颁布了御注的《孝经》和《道德经》(3)御注《道德经》成书年代,据柳存仁《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之得失》,《和风堂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页。,而且在他的《御注道德经》中,还参入了佛教思想(4)龙晦认为:玄宗在注《道德经》时已受了唯识、天台的影响, 不惜把自己认的老祖宗老子, 用佛教去附会。这固然与他个性夸诞、好显示自己的博通有关, 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与他的宗教思想及宗教政策有关。见于《敦煌文献所见唐玄宗的宗教活动》,载于《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31页。。
《御注金刚经》现存最完整的版本是北京房山云居寺藏经洞第八洞的石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御注并序》,为天宝元年(742)顺义郡市令李大师合家捐刻,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吴梦麟先生最早发表录文[1]。另有现藏大英图书馆的敦煌写本(S.2068),首尾残缺,约保存了房山石经本的80%。日本花园大学教授衣川贤次在吴梦麟校录的基础上,重新以房山石经本为底本,以敦煌遗书本和吐鲁番出土残片三片参校,做出了迄今最好的整理本[2]。
为了完成这项艰难的“使命”,唐玄宗请教过道高望重的僧侣道氤。《唐长安青龙寺道氤传》:“(道氤)撰《御注金刚经疏》六卷。初,玄宗注经,至‘若有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乃至罪业则为消灭’,虽提兔翰,颇见狐疑,虑贻谬解之愆,或作余师之义。遂诏氤决择经之功力,剖判是非。奏曰‘佛力经力,十圣三贤,亦不可测。陛下曩于般若会中,闻熏不一,更沈注想,自发现行’,帝于是豁然若忆畴昔,下笔不休,终无滞碍也。”[3]98
开元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一部由当朝皇帝御注的《金刚经》终于颁行于世(5)关于颁布时间,有不同记载。据前引房山石经本《御注金刚经》题记为“开(元)二十三乙亥之岁……九月十五日经出。”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録》卷14《总集群经录上之十四》载:“圣上万枢之暇,注金刚经,至(开元)二十三年著述功毕。”(大正藏55册878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51《帝王部·崇释氏》载:“开元二十三年九月,(玄宗)亲注《金刚经》及修义诀。”(中华书局影印明本1960年版,第575页)与以上三者不同,[明]觉岸《释氏稽古略》卷3引《大藏流行众经目录》:“开元十九年,御注金刚经颁行天下。” (大正藏49册825下)从年代来看,前三个史料无疑可信度较高,且房山石经本《御注金刚经》序云: “昔岁,述《孝经》以为百行之首,故深覃要旨,冀阐微言,不唯先王至德,实谓君子务本。近又赞《道德》……凡有以理天下之二经,故不可阙也。今之此注,则顺乎来请。”可知其注《道德经》在《金刚经》之前。另外,玄宗注三经,实有儒、道、佛的先后次序,以表明他的个人好恶及宗教政策,详见下文。故今取开元二十三年说。。不过这部象征着皇朝正统思想的“宝书”,颁布的过程似乎并不顺利。
《御注金刚经》完成后,以时任中书令张九龄为首的群臣适时地连上两封状。第一封当作于张九龄等人初次见到御注之时,《曲江张先生文集》(下称《曲江集》)题作《贺御注金刚经状》(下称《贺状》),状中群臣称玄宗的新注好像“日月既出,天下普照”:
右:内侍尹凤祥宣敕,垂示臣等《御注金刚经》。但佛法宗旨,撮在此经,人间习传,多所未悟,陛下曲垂圣意,敷演微言,幽关妙键,豁然洞达。虽臣愚昧,本自难晓,伏览睿旨,亦即发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诚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术,道已广其宗,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臣等忝奉天文,不胜荷戴无任庆跃之至。(6)参见张九龄《曲江集》卷15《状》,四部丛刊景明成化九年韶州刊本3a及《全唐文》卷289,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35页。
文中“平分儒术,道已广其宗,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等句,提示出《御注金刚经》在平衡儒、道、佛三教以实现统治这一层面上的意义。此时玄宗御注的《孝经》《道德经》已经行世,而一旦《御注金刚经》颁行,则“三教并列”的最后一块拼图就将就位。
果然,群臣很快就毕恭毕敬地阅读了御注,并上第二状,《曲江集》题作《请御注经内外传授状》(下称《请状》),恳请玄宗公开他的伟大作品,使天下人得以“朝闻夕死”:

所谓“前件”很可能就是指《贺状》。从《请状》看,张九龄似乎也参与了注疏讨论,即所谓“九龄说”“九龄此传”,但其详细今已不可确知。状中再次出现了“三教同归”。显然,在张九龄等看来,对这一理由的强调,能使玄宗更快下定决心。
但是,玄宗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我们从御批中看出了他的顾虑:
此经宗旨,先离诸相,解说者众,证以真空。僧徒固请,欲以宏教,心有所得,辄复疏之。今请颁行,虑无所益。(8)参见张九龄《曲江集》卷13《表状》,四部丛刊景明成化九年韶州刊本13b及《全唐文》卷37,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2页。
这则御批《曲江集》无题,《全唐文》题作《答张九龄请御注经内外传授批》,为编《全唐文》的清人所加。从文意上看,谦虚的玄宗正在犹豫,要不要把他普普通通的“心有所得”公布于世。
关于张九龄等人与玄宗的状、批往来,《册府元龟》和《曲江集》的记载有出入。《曲江集》在第一封《贺状》后附御批(《全唐文》题作《答张九龄贺御注金刚经批》),显示玄宗接受了张九龄等人的建议,“竟依群请”颁布《御注金刚经》:
不坏之法,真常之性,实在此经,众为难说。且用稽合同异,疏决源流。朕位在国王,远有传法,竟依群请,以道元元。与夫《孝经》《道经》,三教无阙,岂兹秘藏,能有探详。所贺知。(9)参见张九龄《曲江集》卷15《状》,四部丛刊景明成化九年韶州刊本3b及《全唐文》卷37,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5页。
若然,则无法解释为何会出现第二封《请状》。《册府元龟》的记载与《曲江集》呈现出微妙的差异,书中关于《御注金刚经》的对话如下:
(开元)二十三年九月,亲注《金刚经》及修《义诀》。中书令张九龄等上言:“臣等伏见御注前件经及《义诀》。佛法宗旨,撮在此经,人间传习,多所未悟。陛下曲垂圣意,敷演微言,幽阐妙键,豁然洞达。虽臣等愚昧,本自难晓,伏览睿旨,亦既发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诚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道,已广度其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伏望降出御文,内外传授。”
帝手诏报曰:“僧徒固请,欲以兴教。心有所得,辄复疏之。今请颁行,仍虑未惬。”
检校释门威仪僧思有奏曰:“自像教西流,贝文东译,学传师口,凡今则多。注诀圣情,前古未有。臣请具幡花,奉迎于敬爱寺,设斋庆贺其御注经。伏乞示天下,宜(宣)付史官。”许之。[4]
为便于对比两部文献的差异,笔者针对“张九龄等上言”和“帝手诏”内容制作了对照表,涉及文意理解的异文加着重符号(见表1)。
比较可知,《册府元龟》“张九龄等上言”文本,第一段、最后一段与《曲江集》卷13的《请状》也就是第二状基本重合。《册府元龟》编者在第一段相同位置把“墨敕批答,兼九龄说”改作“及《义诀》”,则《义诀》可能为张九龄所作的《御注金刚经》修改意见。中间一大段与卷15的《贺状》也就是第一状基本重合,其中《册府元龟》“平分儒道,已广度其僧,又不违其愿”,《曲江集》作“平分儒术,道已广其宗,僧又不违其愿”,这例异文的出现应该是传抄致误。若依前者,则更强调玄宗注《金刚经》是对佛教徒愿望的满足,但“广度”即普度众生,称皇帝“广度其僧”似乎不妥;若依后者,则强调玄宗对三教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于文意似更优。

表1 《册府元龟》“张九龄等上言”和“帝手诏”对照表
其后“帝手诏”的回复内容与《曲江集》卷13《请状》的御批重合,不载《贺状》御批。也就是说,根据《册府元龟》的记录,唐玄宗用《请状》御批拒绝了张九龄等人的颁行请求,直到当初名义上请他注经的思有出面奏请,玄宗才“许之”。思有的奏《全唐文》卷922题作《请宣示御注金刚经奏》(下称《请奏》)。
衣川贤次曾对此做过解释[2]。他认为《册府元龟》的叙事逻辑是把《曲江集》中所收的《贺状》与《请状》两文合二为一称为“张九龄等上言”,且《贺状》在《请状》前成文(这一点笔者同意)。他把时间顺序考订为:开元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前,玄宗便已“完成初稿”,因此张九龄等献《贺状》,玄宗御批表明《金刚经》的思想意义,并且说明注释是受僧人的恳请而作的(这是衣川氏对《贺状》御批内容的解释)。此后张九龄等又上《请状》,玄宗御批表示犹豫(对《请状》御批内容的解释),于是询问思有。到了六月三日,思有仍表请颁行。玄宗因得到思有的称赞,决定颁行,但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修改,九月十五日才允许颁行天下。换句话说,衣川贤次认为房山石经本所谓“开(元)二十三乙亥之岁六月三日,都释门威仪僧思有表请”中的“表请”指的是思有《请奏》一文,其时玄宗“初稿”已成,思有请求颁行此稿。而上文提到的张九龄、唐玄宗的往来状、批全都成文于六月三日以前。
笔者对衣川氏的考证有一点不同意见,《册府元龟》所记事件不应发生在六月三日及以前。现存《曲江集》的编订者并没有按成文顺序排列篇次,这一点从韩理洲对全唐文诏敕的编年可知(10)韩理洲主编《全唐文诏敕考辨》(三秦出版社2017年版)对《全唐文》诏敕部分做了编年。清编《全唐文》卷37的唐玄宗答张九龄批部分的文本,便来自于《曲江集》卷13至卷15表状后附的御批。,所以我们只能从文意判断成文先后。细味文意,笔者认为并无证据证明存在一个六月三日前完成的《御注金刚经》初稿,若有,则房山石经本的题记不应该不述玄宗作注的起始时间,而从初稿完成后思有表请颁行说起。一来不符合常人的叙事习惯,二来《御注金刚经》本就不是一部无人请求就不颁行的著作,它和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是继御注《孝经》《道德经》之后“三教合一”的最后一环,所以哪位臣子何时请求君王颁行,这件事并不那么值得一书。而且据《册府元龟》所述,“(开元)二十三年九月……中书令张九龄等上言”,文意连贯,似无倒叙至六月的必要。最后的“许之”干脆直接,看不到再行“修改三个月”的痕迹。另一方面,我们再回顾房山石经本题记:“开(元)二十三乙亥之岁六月三日,都释门威仪僧思有表请。至九月十五日经出,合城具法仪,于通洛门奉迎。其日表贺,便请颁示天下,写本入藏,宣付史官。”可以肯定 “表请”和“表贺”是两件事,“表请”显然发生于六月三日。那么“其日表贺”的“其日”当指九月十五日,“表贺”的主语很有可能就是前一句的主语都释门威仪僧思有,“便请颁示天下,写本入藏,宣付史官”一语恰与《册府元龟》所载《请奏》的“伏乞示天下,宜(宣)付史官”同义。在现有史料的条件下,似乎认为《请奏》等同于九月十五日的“表贺”才是更合理的意见。
除此之外,细味《曲江集》中的两篇玄宗御批的行文,《贺状》御批相比于《请状》御批更乐观自信,在心态上更接近颁布前的状态,也更符合“群臣力劝,皇帝谦虚”的模式。“岂兹秘藏,能有探详”一句表示愿意把作品公之于众,所以笔者不同意衣川氏指出《贺状》御批只是说明注经原因,而认为此句的写作,似乎应定在注经已完成且距正式颁布不远的这段时间。考虑到《册府元龟》不载《贺状》御批,笔者想提出一种假设,即《曲江集》卷15的《贺状》御批为误植,这篇诏书为玄宗答思有《请奏》而作,而《册府元龟》最后的“许之”,或即指涉此批。至于房山石经本题记所谓思有在六月三日“表请”玄宗注经,其具文今已不存。玄宗对《贺状》如何回应?有两种可能,其一,玄宗未批复《贺状》,或者用《请状》御批一次性拒绝了《贺状》《请状》,因此《册府元龟》把两状概括为“张九龄等上言”;其二,玄宗确实批复了《贺状》,但原文已佚。要之,玄宗拒绝了张九龄,同意了思有,这点《册府元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表2 《御注金刚经》成书过程本文作者与依川贤次考证对照表
因为唐玄宗御批中多次强调“僧徒固请”“竟依群请”云云,有学者就此以为玄宗是应僧人的请求而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的。而他之所以选择此经,主要是因为此经最能体现“佛法宗旨”,最能“稽合同异,疏决源流”[5]。虽然唐玄宗注《金刚经》的起始确实是思有的“表请”,但这么说还是没有看透玄宗注经的本质,如果皇帝想要颁布御注,那么没有人能拦得住;反之,如果皇帝本来就没有注经的打算,那么也没有人能劝得动。所谓“竟依群请”不过是玄宗自导自演的戏,使他颁行御注之事更加顺理成章。他对张九龄等请求颁布时的谦虚犹豫也是同理,实际上,以皇帝的九五之尊,无论其作品怎么偏离所谓“宗旨”,天下人也会跪拜着接受它。这样的戏码,在中国古代宫廷中绝不鲜见。在这一幕中,宰相张九龄自然总是出演那个御用配角。他集子里另一篇《请御注道德经及疏施行状》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右:臣等伏以至道无名,常善救物,所以镇彼浇竞,登诸福寿,而古今殊论,穿凿多门,徒广津梁,何阶阃阈。伏奉恩敕,赐臣等于集贤院与诸学士奉观《御注道经》及疏本。天旨玄远,圣义发明,词约而理丰,文省而事惬,上足以播玄元之至化,下足以阐来代之宗门。非陛下道极帝先,勤宣祖业,何能迴日月之晷度,凿乾坤之户牖。使盲者反视,聋者耸听,蒙蔽顿祛,沉迷有适。凡在率土,实多庆赉,无任忻戴忭跃之至,请宣付所司施行。(11)参见张九龄《曲江集》卷13《表状》,四部丛刊景明成化九年韶州刊本11a及《全唐文》卷288,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27页。
可见,就在一两年前,张九龄就已经代表群臣恳请玄宗施行他据说能“使盲者反视,聋者耸听,蒙蔽顿祛,沉迷有适”的《御注道德经》。那一次,玄宗一次性地答应了:
先圣说经,激时立教,文理一贯,悟之不远。后来注解,歧路增多,既失本真,动生疑误。朕恭承余烈,思有发明,推挍诸家,因之详释。庶童蒙是训,亦委曲其词,虑有未周,故遍示积学。竟无损益,便请宣行。朕之不才,甘失旨于先帝。卿等虚美,岂不畏于后生。循环此情,未知所適。可广示朝廷,有能正朕之失者,具为条件,录姓名以闻,当别加重赏。(12)参见张九龄《曲江集》卷13《表状》,四部丛刊景明成化九年韶州刊本11b及《全唐文》卷37,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3页。
不过仔细品味御批,玄宗答应得倒也没那么爽快。似乎在说“朕之不才,甘失旨于先帝。卿等虚美,岂不畏于后生”的时候,他显得有些愤愤不平,而在说“循环此情,未知所适”的时候,他又显得颇为无奈。
无论如何,我们明显看得出,这一来一去、半推半就之间,玄宗作为一个谨守谦逊美德而又难掩才华的明君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了。恐怕很难把这解释为皇帝应臣子之委托注《道德经》吧?
二、唐玄宗注《金刚经》与三教合一
8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随着宗族的逐渐瓦解,社会流动的愈发频繁,思想文化的自由宽松,信仰的边界开始模糊起来。这个时代开放昂扬的风气,孕育了文学的繁荣,而在思想领域,南北朝以来的儒、道、佛三教合流成了民间的主流思潮和官方的宗教政策。
在民间,以礼法为基础的传统儒家生化模式和观念系统濒临崩溃,宗教对超验世界的美好许诺,吸引着富裕士人[6]。在官方,经历了唐初三帝(高祖、太宗、高宗)时期的“三教共存、道先佛后”政策;武则天与唐中宗时期的“三教共存、佛先道后”政策;唐睿宗时期的“三教并行、不分先后”政策。三教并行格局已经形成[7][8][9]。
李唐皇室自认为是老子李耳后人。出于发自内心对道教的特殊情感,终其一朝,唐玄宗先后追封老子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甚至追封农民起义的理论指导者张陵为“太师”;他命令士庶家藏《道德经》并增加其在科举中的比重;他优待道士、女冠,广兴道观,仅长安就造了九座[1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粗检《全唐文》,由卷26《禁坊市铸佛写经诏》(开元二年)、卷28《禁士女施钱佛寺诏》(开元九年)、卷30《禁僧徒敛财诏》(开元十九年)、卷30《澄清佛寺诏》(开元十九年)等一系列诏书可知,玄宗打压佛教势力可谓不厌其烦。从早期的宗教政策来看,他因致力于扫清武则天崇佛政策留下的遗产,抑制过于狂热的佛教势力,实行了遣散伪滥僧尼、禁止建寺写经等政策,可以说仍然延续了几位先皇极力打压某教而推崇另一教的传统:唐前期那些生活在战争之动荡或政变之不安的阴霾下的皇帝,无论选择崇道抑佛还是崇佛抑道,究其根源,都是在设法制衡各方势力以为己之统治服务。
但随着执政深入,唐玄宗逐渐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的其实是空前和谐的局面。儒学随着意识形态的垄断和应试的教条化,沦为辞藻与韵律的附庸;道、佛经历了东汉末年以来的发展,已在社会各阶层站稳脚跟,谁也不能盖过谁。曾几何时争论不休、剑拔弩张的三教议论,已然偃旗息鼓,甚至在不久的将来沦为皇帝生日宴会上的娱乐活动[11]。那么,像他这样头脑清醒的君主当然不会不知道,现如今保住既成的和谐局面才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权延续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玄宗的佛教政策明显呈现出从抑制到推崇的转变。
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到东都,命菩提流志、善无畏随驾。十三年(725),玄宗又命义福随驾。几年下来,他到东都还带过道氤、良秀、法修。十五年(727),一行圆寂,帝为辍朝三日,并亲制塔铭。二十六年(738),命天下各州郡立龙兴、开元二寺。二十九年(741),河南采访史汴州刺史徐浣奏请道士僧尼女冠有犯,望准道格处分,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违者处罪。玄宗准奏。天宝三载(744),玄宗敕令州郡政府铸金铜天尊和佛像各一躯,分送开元观、开元寺。天宝五载(746),不空为玄宗进行了灌顶仪式,皈依佛门,成了“菩萨戒弟子”[12]。要知道,二十五年前的开元九年(721)他已经受司马承祯之法箓皈依道教[13]。
特别应注意的是,不能对玄宗执政后期崇佛的虔诚性抱有太多期待。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玄宗强制执行僧尼拜君亲政策。佛教教义规定佛教徒只能跪拜佛祖释迦摩尼,对世俗的一切人,即使是父母或君主,也不能跪拜。因为这一规定与儒家忠孝原则抵牾,历来频遭儒家官僚指责为违背纲常,自东晋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以来,佛教势力从未停止过抗争,可谓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大尖锐冲突。唐朝僧尼拜君亲与否,政策上多有反复。据砺波护先生的细致考证,玄宗朝以前唐朝政府有过两次推行僧尼拜君亲政策的尝试。唐太宗贞观五年(631)诏令“僧尼、道士,致拜父母”[14],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僧尼、道士反而“坐受父母之拜”,但可能因为阻力太大,仅两年后便废止。随后高宗龙朔二年(662)诏令研讨“欲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13)道宣《广弘明集》卷25《僧行篇第五之三·今上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一首》(大正藏52册284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3《胜朝议不拜篇第二·今上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一首》(大正藏52册455中)及《全唐文》卷14《命有司议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5页。相关事宜,寻求扩大致拜范围,引发宗教界强烈反抗,从结果来看可能没实行就被撤销。直到玄宗开元二年,诏令“自今已后,道士、女冠、僧尼等,并令拜父母”(14)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13《令僧尼道士女冠拜父母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88页,及《全唐文》卷254《令道士女冠僧尼拜父母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71页。,这是玄宗朝初期打击佛教的诸多举措之一,当时已然无力招架的佛教徒似乎没有做出成气候的反抗就接受了。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尽管如前所述玄宗已经有了“崇佛”举措,还是诏令僧尼和道士、女冠一样,对君主“称臣子之礼”并“兼拜其父母”(15)《全唐文》卷30(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1页)采用通行明刊本《册府元龟》卷60《帝王部·立制度》(中华书局影印明本1960年版,第672页)作“无拜其父母”,并题作《令僧尼无拜父母诏》。因《全唐文》影响较大,造成了道端良秀、镰田茂雄等学者误读。砺波护据《唐大诏令集》卷113《僧尼拜父母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89页)及静嘉堂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内藤湖南旧藏两部明抄本校正,文见砺波护:《唐代における僧尼拝君親の断行と撤回》,《東洋史研究》1981(02):237,中译见《隋唐佛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而此时的宗教势力也没有留下丝毫抵制的痕迹。这一政策,到了肃宗上元二年(761)才撤销。玄宗表现出“崇佛”行为的同时却终其一朝不改僧尼拜君亲的政策,这是此前唐朝历代皇帝没做成的事,直到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才废除,足以说明他虽皈依佛门,却并不把信仰看得比政治权力更重。砺波护称此时的玄宗在三教调和的口号下,推动的是“培养镇护国家的佛教”[15]。
“三教”作为宗教政策在唐代的出镜率非常高。历代正史中,“三教”一词共出现69次,仅《旧唐书》中就出现了24次(16)《南齐书》1次,《周书》5次,《隋书》2次,《北史》6次,《旧唐书》24次,《新唐书》13次,《宋史》7次,《辽史》2次,《金史》2次,《明史》7次。。《全唐文》出现“三教”一词竟高达74次,如“三教归一”(卷160)、“惟此三教,并自心修”(卷130)、“三教俱设”(卷176)、“三教同归”(卷240、卷531)、“六德六行六艺三教备而人道毕矣”(卷236)、“圣策以三教立言”(卷295)、“周流三教”(卷490)、“三教并行,殊途一致”(卷860)、“兼闲三教”(卷930)、“三教皆可遵行”(卷922)。无论是士大夫、道士还是佛弟子都有述及,也难怪宰相张九龄的状要频繁提及“三教并列”“三教同归”,玄宗要强调“三教无阙”了,“三教”已经成了这个时代最突出的命题,同时也成了几乎不经大脑的口号套话。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把视线转回开元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的宫廷,时任释门威仪的僧人思有也许在这幕剧中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我们姑妄猜测,为什么玄宗在颁布《御注道德经》时一次性答应下张九龄等人的请求,而在颁布《御注金刚经》时拒绝了群臣,直到思有请求后才同意颁行?
释门威仪一职,史籍中仅此一例。但是唐代有道门威仪一职,负责“统摄”“监领”等道教内部事务,开元二十一年在史籍中首次出现。担任道门威仪使的既是道官,也是道门中的领袖(17)周奇认为唐代道门威仪是介于中朝管理机构(有鸿护寺、宗正寺、司封等),和三纲(观主、上座、监斋)二者之间的道官。具有一般使职的特性,有利于中央控制道教。见周奇《唐代宗教管理研究》,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0-64页。。思有的形象尽管模糊,但是不难想象,一个可以奏请皇帝的佛教领袖,一定有着令人艳羡的地位与权力。有意思的是,除了地位与权力,他还得到了一样特殊的恩惠——唐玄宗给的面子。
就像之前提到的,皇帝既然已经决定颁布《御注金刚经》,那么他要做的只不过是找个合适的时机接受臣子的恳求罢了。唐玄宗知道,他的“三教并行”政策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御注金刚经》。面前的释思有,代表了整个国家的佛教徒,这些信仰者可能在御注《孝经》《道德经》问世之时,就开始苦苦等待了,等待着正统思想与秩序的象征者——皇帝,兑现这最后的、久违的拼图。这时候,“御用配角”张九龄就成了一个绝佳的衬托者:利用他的被拒,衬托思有的一言千钧。
当然,无论这个猜测成不成立,它都不过是玄宗努力拉拢佛教势力的诸多举措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而已。
三、余论
《金刚经》注成之后,在唐代影响很大(18)关于《御注金刚经》对后世影响,前揭衣川贤次《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的复元与研究》一文已详,请参阅。。玄宗曾经请教过的道氤被要求为之作疏《御注金刚波罗蜜宣演》,后者也凭借在西明寺、崇福寺讲此疏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唐长安青龙寺道氤传》:“续宣氤造《疏》矣。四海向风,学徒鳞萃,于青龙寺执新《疏》,听者数盈千计,至于西明、崇福二寺。”[3]
从都城到地方,宣讲活动频繁。开元二十三年(735),为庆祝玄宗“著述功毕,释门请立般若经台,二十七年其功终竟。僧等建百座道场。七月上陈墨制,依许八月十日安国寺开经。九日暮开西明齐集。十日,迎赴安国道场,讲御注经及《仁王般若》”[17]。位于都城长安的大安国寺由皇室供养,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如此快地跟进朝廷的宗教政策并不奇怪。开元二十九年(741),大安国寺还任命僧侣释道建,到沙洲主持授戒仪式,宣讲《御注金刚经》及《法华经》《梵网经》等(19)俄藏敦煌文书《开元廿九年授戒牒》(Дx.02881+Дx.02882)记载了此事,荣新江在衣川贤次录文的基础上做了文字修改和分析。见荣新江《盛唐长安与敦煌——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后收入氏著《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从沙洲的情况,完全可以推测宣讲《御注金刚经》这一政治宣传行为,由中央政府推动,从长安辐射到了全国。房山石经《御注金刚经》的捐刻者,来自顺义郡的市令(管理市场的小官员)李大师可能就是在当地接受了宣讲。另外,长安的兴唐寺里甚至有以《御注金刚经》命名的寺院(20)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神品上一人·吴道玄》引《两京耆旧传》:“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间。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上都唐兴寺御注金刚经院,妙迹为多,兼自题经文。慈恩寺塔前文殊、普贤,西面庑下降魔、盘龙等壁,及景公寺地狱壁、帝释、梵王、龙神,永寿寺中三门两神及诸道观寺院,不可胜纪,皆妙绝一时。”(四库全书本3a)又见于李昉《太平广记》卷212《画三·吴道玄》引《唐书断》,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23页。。
以《金刚经》为题材的变文俗讲的涌现,说明该经在唐代下层人民中越来越受欢迎[18]。唐代中后期,禅宗在中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御注金刚经》挟帝王之力行世,与唐代禅宗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本文蒙京都大学李弘喆博士指教,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