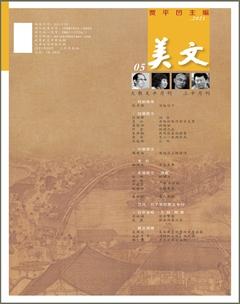深爱与沉迷(三)

张炜
鱼之趣
苏东坡一生嗜鱼。他可以为一条刚刚捕获的好鱼到处找酒,携着它们去找好友,然后去一个配得上这美味的地方享用。有名的月下赤壁之夜就因了这样的缘由。他喜河豚,制鱼羹,就因为有鱼,所以惠州和儋州这样的边远苦地也让他得到了口福。即便是南海,诗人也不以腥膻为苦,而当年的韩愈在岭南因为食物难以下咽。诗人关于鱼的文字太多了,一生与水结缘,鱼水情分深重。
在他这儿冒死吃河豚已成常事。记录中有一个朋友的妻子是烹饪河豚的能手,她曾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东坡怎样吃自己烹的河豚。到最后,只顾低头猛啖的诗人不发一言,这让她大为失望:期待中的那场热情赞誉竟然没有发生;但过了一会儿诗人从案前站起,说了“死也值”三字。这让她大获快慰。
诗人生在眉山内陆,对淡水鱼更加喜欢。他一生的苦难之地有三处,其中的惠儋都为临海之州。除了短短的登州任职的经历,可以说海鱼往往与大风大湿和大跌宕连在一起,实在是共度苦日。眉山少年的口味不是海鲜,所以后来渐得海鱼之趣,可能是惠州和儋州。登州是让其心情明媚的日子,那时对于鲜美海鱼的感受并不为怪。
“终南太白横翠微,自我不见心南飞。行穿古县并山麓,野水清滑溪鱼肥。”(《二月十六日,与张、李二君游南溪,醉后,相与解衣濯足,因咏韩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乐而忘其在数百年之外也。次其韵》)山溪之中的获取最为迷人,这些文字千年之后读来令人倾心,口角生鲜。如“芽姜紫醋炙鲥鱼,雪碗擎来二尺余”,有人认为是苏东坡在镇江焦山品鲥鱼而作,虽存疑,却也实在传神。“紫醋”和“雪碗”,二尺余长的名贵大鱼,这些皆为大美之物,想象中香味穿越时空扑鼻而来。而今天漫漫长江都很难找到一条鲥鱼。古人之有幸,也表现在“芽姜”“紫醋”“雪碗”都有更好的用处。
诗人前后留下了二十多首关于鱼的佳作,几乎每首都是令人流涎的美章。“烂烝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春菜》)“青浮卵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早岁尝为荆渚客,黄鱼屡食沙头店。”(《渼陂鱼》)“三年京国厌藜蒿,长羡淮鱼压楚糟。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赠孙莘老七绝·五》)说的是自己在京都汴梁待了三年,远离溪水長河,只能享用久吃生厌的藜蒿,而今天来到了水畔桥下,眼看网中窜跳的大鱼,简直高兴坏了。“紫蟹鲈鱼贱如土,得钱相付何曾数。”(《泛舟城南,会者五人,分韵赋诗,得“人皆苦炎”字四首·三》)“若信万殊归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鱼。”(《濠州七绝·观鱼台》)“举网惊呼得巨鱼,馋涎不易忍流酥。”(《次韵关令送鱼》)这些诗句活画出一个人迷入美食的情态,急促和兴奋状跃然纸上。就此我们也会明白他为何倾心江边的“鱼蛮子”,对他们的苦难遭际洒一掬同情泪,同时也对这种奇特的生活方式极为好奇。他交往许多水上朋友,经常出入他们狭窄阴暗的船屋:“异哉鱼蛮子,本非左衽徒。连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庐。”(《鱼蛮子》)
文字记载中既有大名鼎鼎的“东坡肉”,也有令人垂涎的“东坡鱼”。他在此领域的发明,除了以其盛名高位易得记载之故,也实在是因为专注和勤于尝试。他有一篇《煮鱼法》写道:“子瞻在黄州,好自煮鱼。其法,以鲜鲫鱼或鲤治斫冷水下入盐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浑葱白数茎,不得搅。半熟,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三物相等,调匀乃下。临熟,入橘皮线,乃食之。其珍食者自知,不尽谈也。”鱼汤细事,记录何等周详。多少人津津乐道于所谓的“中华美食”“饮食文化”,但从源头溯起,这里面的确洋溢着诗意和想象,远不是一个粗人可为。如果诗人东坡将此法稍作省略,比如把“不得搅”或“橘皮线”几个字去掉,又该如何?相信做出来的食物当不会有什么差异,但失去的是分寸和精微,是程序上的美不可言,实在大有不同。粗精之别竟在几个字的删减之间,人生也是如此。
我们观古今之画,经常看到的是鲈与鳜这种形体夸张的鱼,当然还要看到水与石。它们代表了内陆的山水雅趣,实际上隐去的则是临水观鱼的高士。二者相映成趣,意境高古。这一切就像梦一样逝去,再不见这样的水流和鱼趣,也没有了高士的身影。那是一个时代的情怀,它必须远离数字传播的喧嚣和大面积的工业化养殖。人工饲养的鲈鳜不再稀罕,可它与诗有什么关系?水塘里密集的鱼如同东部沿海繁华街区密集的人流一样,离开了活泉,已经没有了天地滋养,而统统化为一个时代的养殖品。
草木饮食
苏东坡记下了太多的草木饮食,这其中大多是一生实践所得,与自小接受的道家修养和兴趣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好奇探究和创造的天性。他详细地记录了这方面的一些尝试,记下了心得,只为了备而待考以便进一步探寻,同时也留下了奇文共析之妙。草木无尽,尝试也就没有穷期。草木饮食本为大要,用以支持生命,就此来看,所有这些方面的实践都有重要意义。一笔一笔记下品类、效用和滋味,从头回味一番,既可重温逝去的时光,也可与他人分享互鉴。在漫长的历史上,类似的民间经验或因为记载而留下来,或因为其他种种原因而湮灭。苏东坡真是一个有心有趣的人。
“我梦羽人,颀而长兮。惠而告我,药之良兮,乔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龟蛇藏兮。得而食之,寿莫量兮。于此有草,众所尝兮。状如狗虱,其茎方兮。夜炊昼曝,久乃藏兮。茯苓为君,此其相兮。”(《服胡麻赋》)这样的饮食基本上是玄人才能有,是我们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一种特异见识,所谓的不食人间烟火也不过如此。在诗人来说,这与那些金石丹丸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成“外丹”。而传统的“外丹”冶炼,草木远不如金石的作用,于是后者更为珍贵。当年的杜甫感叹诗友李白迷于炼丹,苦于自己不能跟随,原因就是没有“大药资”,可见干这种事需要很大的本钱。硫汞一类在古代十分难得,而草木也不可或缺。在我们沿用至今的中医药宝库中,占绝对数量的还是草木一类,可见它们的确具有重要作用。
苏东坡曾经记下了一种棕笋,说它的样子就像鱼,剖开来里面竟然有鱼籽一样的东西,味道像苦笋,但又多了一种甜香滋味。这种奇物只在二月间可以剥取,过了这一特定时刻就变得苦涩不可食。他特别在记录中指出:将这种棕笋剥取是无害于树木生长的,做法与做笋相同,须用蜜煮醋泡,对人的好处简直大极了。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赠君木鱼三百尾,中有鹅黄子鱼子。夜叉剖瘿欲分甘,箨龙藏头敢言美。愿随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问君何事食木鱼,烹不能鸣固其理。”(《棕笋并叙》)他寻找菌类,栽种薏米,深得药食同源之妙,认为这些美好的草木作用之大,不仅能够解毒医病,还有其他神妙功效,不无幽默地写道:“能除五溪毒,不救谗言伤。谗言风雨过,瘴疠久已亡。两俱不足治,但爱草木长。”(《小圃五咏·薏苡》)还记道:“竹有雌雄,雌者多笋,故种竹当种雌。自根而上至梢一节二发者为雄。物无逃于阴阳,可不信哉?(《记竹雌雄》)“北方之稻不足于阴,南方之麦不足于阳,故南方无嘉酒者,以曲麦杂阴气也,又况如南海无麦而用米作曲耶?”(《黍麦说》)
如此用心缜密地记录,感悟之深和妙想之奇,实在令人惊讶。南北阴阳之别、食物之异,阴阳之气与酒的关系,只有他这样细密的心思才可以解说。怎样煮蔓菁、芦菔、苦荠,怎样用水,诗人不仅细细地记下和辨析,而且还为之做赋,写出了有趣的《菜羹赋》。他竟然为那些用尽心思到处搜寻吃物、巧妙烹调、不顾一切、全力以赴的怪人,写出一首《老饕赋》。类似的文字还有《接果说》《荔枝似江瑶柱说》《记汝南桧柏》《记岭南竹》等。
他写茶叶的诗有近八十首,诗中关于茶的各种煎法、煮法,无不周备。茶、水、火三者相会之情状,百般比喻流泻而出:“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试院煎茶》)烹茶一事,如何奇异,也只有从这些微妙的汉字组合里去品味和想象了。“岩垂匹练千丝落,雷起双龙万物春。此水此茶俱第一,共成三绝景中人。”(《元翰少卿宠惠谷帘水一器、龙团二枚,仍以新诗为贶,叹味不已,次韵奉和》)类似的妙作还有许多,真是令人眼界大开,击节叹服,几乎所有篇什都透着异彩奇趣:因兴奋而夸张,因有闲而自傲。
对茶如此,对生活中的诸多物事也是如此,它们全都来自生命的活力与专注。这样的传达实际上是一种共享,是即时共享,也是留在时光里的共享。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在这扑面而来的水汽中嗅到浓烈的茶香,一睹诗人兴味盎然之状。可以想象,古往今来关于茶的著述數不胜数,但像苏东坡这样拆解奥妙、将无法言说的精微诉诸想象和猜度的人,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他最有名的一首茶诗为《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文字用到如此地步,心绪与记忆,经验与思悟、快活与心得,一切既来自实践之精细、品味和想象。这真是生命之杰作、享受之杰作、大快之杰作。活水与活火、钓石之水与其他水,这一切会有什么区别?一般来说生活中人全都忽略不计,也只有追随诗人的深悟和想象了。舀一大瓢水,其中映出了一轮明月,把它倒入春天的瓮中,再用小勺装到瓶里。云脚乱翻,雪浪飞旋,松风忽来伴奏,无论是怎样的枯肠,只消喝上三碗,也就兴致大发。这大概是一个无眠之夜,任凭畅想,荒城短更。
民间俗语中,形容一个平凡的人为“草木之人”,但如果在生活中真的能够获得草木真味,却是难而又难的。真正的“草木之人”是与大自然同生共长之人,是与之同享一片灿烂阳光,迎朝霞沐晨露,融入大自然怀抱之人。
医药与修炼
在苏东坡看来,医药和修炼的路径虽有不同,但目的却也相似。人做到身体无疾,其实是追求长生的最低要求。道家一般不问年龄,因为他们认为压根就没有什么死亡的问题;而佛家认为生命本来就是轮回超度的,既无开始也无结束。苏东坡的修炼既着眼于长远也考虑到近前,可以说是从基础抓起:医病防疾。就因为这个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需求,他一生实践多多,并留下了大量药方。
有一个《梦溪笔谈》的作者叫沈括,一度是苏东坡的敌人,此人一生最不堪的记录,就是收集苏东坡的诗与文构陷告密。这样一个人在其他方面同样用心周密,竟能成为历史上的不朽者:世上流传一册他与苏东坡的《苏沈良方》,已属后代医家必读之书。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苏东坡对于医术研究之深、施用之广,既为自己也为他人。他知杭州期间曾经遇到瘟疫流行,于是急急搜寻良方,并自费购买大量药材,配成秘方“圣散子”,用大锅煎煮,广布街巷,救人无数。
医药益于大众,还需多多问诊临床;修炼却要独行,这其中不乏晦涩的个人领悟。这种完全个体化的体悟和实行可能比炼丹更难。苏东坡是一个积极尝试丹丸的人,当时主要还是苦炼“外丹”,而且自年轻时就喜好寻找丹药妙方。他在凤翔为官时,曾发现居所旁的古柳处每到下雪都有一片泥土从不积雪,天晴后即凸起数寸,疑心为古人埋丹之所,准备挖掘,结果被妻子王弗拦下:“如果婆母在,必定不会发掘。”东坡这才惭愧地打消此念。此事记于《记先夫人不发宿藏》。
因为“内丹”之说在北宋并未普及深入,苏东坡虽有一些体会,也未作更多研习。他在海南预防断炊而苦苦练习的“龟息法”,实际上就属于“内丹”学的范畴。他的《枳枸汤》《服生姜法》《服茯苓法》《艾人着炙法》《治内障眼》《苍耳录》等,都是由实验而得来的宝贵方剂。至于那些接近于“内丹”的试验,是日后才渐渐多起来,为玄妙所吸引,诗人开始更多地参见道人,寻访异术,还学习了一种舌舔上腭以取华池之水法:感到舌下筋微微急痛,所谓的“向上一路,千金不传”。此法名曰“洪炉上一点雪”,且是秘不传人之方,他特意嘱咐弟弟不可以示人。(《龙虎铅汞说寄子由》)有趣的是,东坡常常这样郑重地叮嘱,自己却不能遵守,忍不住就要与人共享。他记下的《大还丹诀》《龙虎铅汞说》《养生诀》《寄子由三法·胎息法》等,都已经属于“内丹”范畴了,在当时可以说诗人已经是至为先锋和深奥的一个大养生家了。
我们有时不禁疑问:巨量的劳动和耗损,以及官场的跌宕、频繁的磨难、一生南北跋涉,这当中还会余下多少时光间隙,让他能够如此专注用心,践行并涉猎这么多的学问和方法?除了儒家经典,无数的治世方略,还有各种方术及其他不可尽言的杂趣,对他而言需要多大的精力和活力来处理;另一方面,也极有可能是在草药学、“内丹”“外丹”的身體力行方面,他获得了真正的生命援助,这才能够承受如此沉重的劳动及其他磨损。总之对诗人来说,那些洞察幽微、神妙难测的古怪方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了正面帮助,我们一时还难以分析量化;这方面,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受害者和受益者,我们也同样费解。受限于当时的科学认知,就健康而言必有妨害的一面;但更多的,可能还是他以超人的悟想和智慧,得到了一些心与身的滋养。
他一再地拓展认识和实验的边界,以至于包容无限、泥沙俱下,就像他海洋一般远阔和深邃的文字一样。这真是一个生命的奇观,一个天地之间的大悟者,一个人生的高蹈派,一个事无巨细的亲历者。我们经常会想到:苏东坡如果不是一个深入儒家堂奥、在家学传统中大步向前,最终踏上为仕之途不可回返,那么一定是一个寺庙或道观中的非凡人物,而最后,极有可能是一位游历四方的神秘隐士。只有类似的角色,才能够满足这个特殊生命的好奇心和无所不在的探究力。他对待无形的心神使用了修炼,他对待有形的躯体使用了医药,一生都想在这二者之间寻一个准确的答案。不过像古往今来所有的智者一样,在这些方面,他好像一生都没有实现自己预想的目标。
“内丹”“外丹”,更有酒,都是苏东坡一生不能忘怀之物,也是他时常依赖之物。没有丹丸的向往,就少了许多想象和希望;没有酒的慰藉,日常生活就苦涩而单调,也更难解脱。“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渔父》)苏东坡是出于嗜好、出于对恍惚之境的神往和迷恋,还是以酒浇愁,大概二者皆有。
醉与梦,这是神志上的两种特别境界,对现实生存中的人总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醉后的舒畅和放肆,梦中的奇幻见闻,与具体而切近的眼前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样的一种情境和际遇,等于生命屏风之后的另一片景色,几乎令所有人难以忘怀。人们把类似经历藏在心头,有时候言说,有时候只留下来个人品咂。历史上的豪饮者比比皆是,能够即时留下神奇文字者也不少见。大饮者并非时时沉醉,沉醉即超越了酒量。苏东坡不能胜酒,动辄醉卧,就有更多进入醉境的机会。他喜欢自己醉酒,更喜欢看别人醉倒的样子。人生没有如此频繁的入醉,在他来说该是多大的缺憾。
关于丹和酒的实验,既繁多又深入,文字中有过很多。它们对他来讲究竟是单纯的慰藉还是一种更实际的需要,一时无法确认。我们只知道在这些具体实践中,苏东坡都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可言。对他来说不是因为不用心,而是因为这两项事业实在太难,即便付出毕生的精力,也未必可成。
他痴迷于造酒,但因为急于求成的性格,常常不能安下心来好好酿造。记录中他发明了一种“真一酒”,原料十分简单,不过是用米麦和水三样。对这种酒,他多少有点夸张地说,喝过三杯以后“俨如侍君王”。这里透露出一点秘密,就是“侍君王”会有一种特异的满足和欣喜感,这里没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想必在贬谪之地,他记取的多是宫廷美好的一面。在炼丹方面没有成功的记录,医药则是成功的,有留传后世的苏氏药方为证。
酒是享用,丹是修持,它们的功用其实是大为不同的。炼丹可以视为酿酒的基础,因为没有长生和健康也就没有享用。饮酒可以在成丹之后,因为尽情享用要在生命的一些大问题解决或正在解决的时刻,才能充分地进行下去。诗人少年的修炼志向一直潜在生命深处,后来一有机会就会萌发。从古到今,有一部分读书人都将修炼作为隐隐的大志向,因为通常是用它们来解决人生至大问题的。或许从根本上来看,这种修炼远比科举功名之事大得多也重要得多。科举从理论上看是先顾天下,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走向科举,实际上是舍弃自身之利益服从于国家的需要,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献身的行为。而修炼首先是解决自身肉体和灵魂的问题,不可不谓之大事业。苏东坡在后来的仕途上,仍然要时不时地停顿一下,回头遥望原来的那份大事业。
炼丹这种事情说来玄妙,其实一直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它从来都没有退出我们的生活,许多时候不过是改变了一下形貌而已,比如化为各种各样的现代滋养品和补充剂,正得到广泛使用。今天能够彻底拒绝“丹丸”,特别是“外丹”的人,实际上是很少的。最新的医学研究认为,酒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但这里并不包括酒的其他功用,比如说助兴和一展豪放,比如与之相关的诗意弥漫。而“丹丸”作为一种生命的辅助剂,却是无法否定的,尽管对它们的功用偶尔也有争执,但总的来说还是认为大有益处的。看来现代人的“丹丸”还要继续炼下去,这里指的是“外丹”。“内丹”在大多数人那里已经废止,因为它过于晦涩,而且需要更多的闲暇;即便在山东半岛东部,那个素有长生修炼传统的地方,今天也很难在大众中兴盛起来。
杂记异事
诗人记下了那么多奇闻逸事,这些听闻或亲历都是特别有趣的文字。它们有时候仅仅是存异备考,其意义却是多方面的。许多时候他对这些怪异之事深信不疑;作为一个求真者不可能对这些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客观存在或真实发生的。他是一个忠诚的儒家子弟,却对“不语怪力乱神”之训不以为然。再者孔子也并未否定“怪力乱神”的存在,只是“不言”而已。情趣旺盛如苏东坡,对这一类事物的探求是自然而然的,其求证也必定贯穿始终。
我们可以由他的“记录在案”扩大自己的眼界,展开自己的想象,增长许多见识。它们构成了苏东坡游记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废弃。他亲手书下的《记神清洞事》《空冢小儿》《太白山神》《华阴老妪》《猪母佛》《广利王召》《广州女仙》《鬼附语》《陈太初尸解》《书桃黄事》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仅看作耸人听闻的记异还远远不够,在当年有的属于存异待解,有的因为惊讶难弃,总之必须写下来。这些记叙大多详细,而且有论有证,不可轻易视为荒诞妄语。
人生也短,个人见闻总是有限。生活中的人常常由于实践的浅陋而对许多费解事物斥为迷信,特别是对源于古代的这类文字,只作为小说传闻而已。这样的笼统认识未免肤浅,而且叠加了新的谬误。许多时候并不是苏东坡轻浮和草率,而是我们自己过于孤陋寡闻。打开一部苏东坡全集,这个部分也有可观,它同样表达了生命的丰沛和宽裕,除去这些,苏东坡将是不完整和不真实的。我们由此可以推开去看,发现生活中和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几乎大都有广大兴趣和非同一般的专注心。他们在真理和真相的求索方面不愿放过一个细节、一次论证,每遇怪异必寻其踪而求其实。也许仅仅是一个趣闻、一个异端,却会蕴藏深广的理路。我们追寻下去或有新的发现,它足以推翻我们惯常遵守的一些通论和常识,发现偶然中的必然。
我们的错误在于过分地听信已有的成见,视野里只有粗枝大叶。世界如果是一棵树,不能去掉繁茂的枝丫,只留下光秃的躯干。它要有茁旺的舒展和吐纳,要伸出叶芽迎接露水,在风中哗哗作响,招来群鸟喧哗,洒下一片绿阴,伸出根脉在深壤中汲取。我们应该寻找和认定一棵真实的、正在生长的树。
诗人关于杂异的一些记录或幽默有趣,或存以警示,或另有深意。这里可见苏东坡的真性情,可以看到他的理性与率直。许多事物有异有常,在他看来都值得一记,我们自然要极其重视。“异”因偏执和偏僻而存,因此与常态不同。一些人物和事件,从着衣吃饭到梁上君子,从钱塘杀鹅到徐州屠狗,他都一一写出,可谓其闻也广,其记也详。
他在《书罗浮五色雀诗》中曾记下这样一件怪事:惠州的罗浮山上有一种五色雀,以绛红羽毛者为头鸟,带领群鸟盘旋飞翔。当地俗语说只有贵人入山它们才会出现。有个叫余安道的人诗云:“多谢珍禽不随俗,谪官犹作贵人看。”苏东坡过南华寺时遇见过这种鸟,自然欣喜。海南人称五色雀为凤凰,说旱天见到它们就会下雨,涝天见到则会免除涝灾。当苏东坡贬谪到海南之后,五色雀曾翔集于城南所居之处,他正在一位朋友的庭院中游玩,这群彩鸟又翩然而至,并且“铿然和鸣,回翔久之”,他举起酒杯对它们说:“汝若为余来者,当再集也。”后来果然如此。
苏东坡在《事不能两立》一文中,记录了诗人白居易的一件奇事:当年白居易在庐山盖起了一个草堂,筑炉炼丹,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炉鼎突然垮掉,第二天“忠州刺史除书到”。此处喻为入世和出世两事对立,不能同时兼得,既讲了天意,也讲了人不能有过多奢望:如果一个人想“鱼与熊掌”兼得,那是不会成功的。他的《禄有重轻》《德有厚薄》《仙不可力求》《螺蚌相语》等,都是这一类记叙。
如果一个人不求真实,闻过而已,只会视为戏言,是不会诉诸文字的。我们在现实中未尝没有这样的亲历和听闻,但像诗人一样深入探究,并将整个过程细细记下来,是不太可能的。这需要极认真的生活态度,需要纯粹的心情,更是一种人生境界。
纵观诗人的行迹,给我们的感觉是,苏东坡总在寻找“别一境界”。这里不仅指意境和精神,还包括客观环境。官场、人流、日常、物事,所有这一切日日重复,反而容易将其深处的意义和真实包裹起来。就为了突破眼障,他不得不寻访一些偏僻清寂之地,将搜寻的范围一再地扩大,接近极美的山水、风物、特异的自然环境和人士等。在《游金山寺》这首诗里,苏东坡记下了奇异的天象,后来的读者竟说他当年看到的也许是外星人的飞船。诗中写道:“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就这样留下来,千年存疑。
他常常留连之地有寺庙、道观,接触了很多和尚、道士和隐士,因为这一部分所谓的边缘人物离开了世俗物欲,不仅有着特别的人生视角,而且还由于身处偏远冷寂之地,有更多的生存感悟。心境与能力的不同,决定了不可取代的价值,而这些恰是苏东坡所需要的。他们之间的对话何等精彩,俗见在这里暂时被隔离和屏蔽,交谈者已非俗人。这种时刻对于苏东坡来讲,是何等快慰和难得。
如果说一个人最大的收获是特别的心智和见识,那么它往往存在于生活的褶缝之中,只有伸理开来才会显现。这在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时代是很少见到的情形,因为我们已经很难找到独处之人,所有人都在熙熙攘攘之中,就连寺庙也在不停地奏响摇滚,传来智能手机的铃声。纵横交织的现代科技挟来各种消息,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丝空间。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和所谓的知识,把深层的生命感悟全部覆盖和淹没。
苏东坡一生都在探求,并且记下整个过程用以回顾。也就是这样的一些场景,把他时而拉进一场幽思之中,找回自我的真谛。匆忙的人生会遗漏很多,忽略最重要的景致,所以有心人才会尽力做出弥补。一些特别的时刻和经历滋养了诗人,让他每每发出惊叹,为自己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感叹不已。苏东坡作为一个名声巨隆的人物,生活于官场与文场,那些大热闹却实在难以让其满足。他有更开放的视野,更旷远的心灵。梦中留连之地、似曾相识之地,他都要设法进入。他热衷的一些物事可谓生僻,却因此而更加不能放过。
月夜
在静夜,在月光下感受一个世界,它是大不同于白天的另一个世界。苏东坡之爱月,如同李白。轮换交替的夜与昼是最大的神奇和昭示,人们却有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关于月亮,现代人出于深刻的好奇,发明了探月器,结果却陷入了技术主义的圈套,收获了一轮破败的月球。自古以来天穹中那么美好的一个存在,一个心灵的存在,就这样无意间毁掉了。这可以视为现代进步所犯下的一个极大的、不可饶恕的审美错误。
从兴味盎然到兴味索然,原来不过是一步之遥和一念之差。人类耗去几千年的时间才踏上月宫之路,发现的却是无比的荒凉和粗粝,是无可挽回的失望。由此反观古代那些绝妙的人物,比如苏东坡和李白,他們对于月亮并没有愚昧和自欺,而是极尽奢华地享受了自己的心灵之月。那一轮姣美,那一个婵娟,供他们享用无尽。比起白天,月夜是阴性的美,它私密、含蓄、柔弱,这样的属性当然更多地适于一个诗人,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多情的人。我们在现实的阳光下暴晒太多,活动太久,实在需要像他们一样进入自己的月阴之中。一种温和的照抚会使我们获得另一种满足,甚至滋生出无可比拟的力量和信心。我们可以挥发想象,在这里思念和遐想,进入无边无际的昨天和今天,在旷邈的空间里低垂双目,抚摸银光闪闪的大地。
苏东坡他们最舍不得这月光,吟唱,寻觅,记忆,与友人爱人一同陶醉和欣赏。古往今来有多少月光之章,它们真的不朽。“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记承天寺夜游》)怎样的情怀才能如此拥有?绝美的山水景致,有时候不是缺少,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那样的情怀。这里的苏东坡就因为楚楚动人的月色而欣然起行。他不仅是自己享受,而像得到了一条美鱼和一壶好酒那样,一定要与人共享,这个人叫张怀民。
“新月生魄迹未安,才破五六渐盘桓。今夜吐艳如半璧,游人得向三更看。”(《夜泛西湖五绝·一》)“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前赤壁赋》)“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在西湖,在赤壁,在大江,在南海,无不伴有明月。苏东坡好像一定要将月亮的世界和太阳的世界,做一对比和平衡。这两个世界一个都不能舍弃,因为各有妙处。月夜似乎更温柔,更惬意,也更迷恋,像母亲的温厚和慈爱。中国有一首不朽的名曲叫《二泉映月》,是一位盲人写下的心灵之月,一生的悲苦与无边的欣悦,都在这场倾诉之中。他已经无缘见到空中的那一轮皎洁了,可是在它的照抚下,他的心灵开始了一次漫长的诉说。所有隐秘尽含其中,最低沉和最激越的生命之章在月光下流淌。
这样的一场倾诉,只有黄州之后的苏东坡才有可能与之相通;至于荒芜险峻的海南之夜,这样的一轮月亮会垂得更低、逼得更近。
(责任编辑:马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