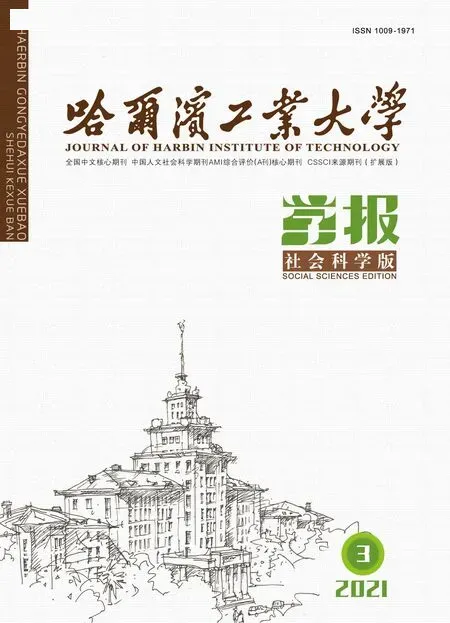避免疫灾的环境治理之道
唐代兴
(四川师范大学 伦理学研究所,成都610066)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提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命题,历来被视为一条自然律。但进入21世纪以来,诸如H1N1、H1N9、埃博拉病毒以及新冠状病毒等跨地域流行的疫病似乎证伪了这条自然律:这种“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奇迹,到底是天灾还是人为?直面这一问题,或可对环境治理有其更新的认识和更好的行动方案。
一、流行性疫病:从天灾到人灾的环境巨变
人类的伟大,并不是因为他创造出了什么,而在于他能反思和自我修正。社会的文明,国家的强大,不仅仅是物质的富有、科技和军事的领先,更重要的是理性精神和节制能力。面对世界大流行的新冠状病毒开启的后世界风险社会进程,人类唯有自觉地提升理性精神和节制能力,严正反思和自我修正,方可去除许多的无知而担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指出,当前正在经历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是文明社会对自己的伤害,它不是上帝、众神或大自然的责任,而是人类决策和工业胜利造成的结果,是出于发展和控制文明社会的需求。”[1]英国史学家阿诺·汤因比更是痛心疾首地说道:“在现代,灭绝人类生存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灾,这已经是昭然的事实。不,毋宁说科学能够发挥的力量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不可能有不包含人灾因素的天灾。”[2]我们可以不赞同两位思想家的断言,毕竟人类是“吃五谷”的物种,“生百病”亦是自然现象,“疾病在人的一生中不可避免,应对疾病也是人类的普遍经历,遭受疾病的痛苦就像人终将会死亡一样无法摆脱”[3]。疾病伴随人类,“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传染病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更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打击了他们的心灵。”[4]但是,伴随人类的疾病,可能是自然生成,也可能是非自然生成:就前者言,遭受疾病折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命,不可避免;仅后者论,疾病与人类之间只构成或然关联,因为有许多疾病伴随人类文明而来。人类所承受的疾病苦难,到底根源于前者还是以后者为主,可大致以农牧社会为分水岭: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一路向前发展至于今天,越来越多的疾病是人类不经意培育的成果,它成为一个反面镜子,照出两个方面的伤害:一是照出人类为造福自己的过程对自然环境的伤害程度,更具体地讲是对生物和微生物世界的伤害程度;二是照出人类在实现自我造福的过程中对自己及其未来的伤害程度[5]。
从根本讲,文明是人类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创造存在和生活事务的呈现。但是,人类自我设计、自我创造和自我经营的过程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维度,即世界本身的存在,包括构成世界存在的其他存在者的存在[6]vii,由此形成人类为谋求更安全存在和更优裕生活所做的生生不息的跨界行为本身就在制造疾病,并且这一制造疾病的行为相对地球生物世界和微生物世界而言,人类却成为“病毒”本身,这是来自生物世界的病毒能够“人传人”的生物基础。
完全可以把人类在与其他生命关系的生态角色视为某种疾病。自从语言的发展使人类的文化进化冲击到由来已久的生物进化以来,人类已经能够颠覆此前的自然平衡,一如疾病颠覆宿主体内的自然平衡。当人类一次又一次蹂躏别的生命到达自然极限时,往往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稳定的新关系。然而,或早或晚,而且以生物进化的尺度衡量还总是在极短的时间以后,人类又掌握了新的手段,把此前无法利用的资源纳入可利用的范畴,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其他生命形态的摧残。故而,从别的生物体的角度看来,人类颇像一种急性传染病,即使偶尔表现出较少具有“毒性”的行为方式,也不足以建立真正稳定的慢性病关系[6]15。
人类的病毒性来源于人类的进化方式,这一特有的进化方式使疾病成为人的社会和历史的产物。“自然界,就他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不仅如此,“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8]马克思告诫我们:正是我们能够认知、发现和运用自然规律,才容易产生狂妄自信和贪婪无度,形成与自己的“无机的身体”的矛盾和对立。表面看,这种矛盾与对立只是体现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或对立,但实际上却是人与生物以及人与微生物之间的脆弱的共生平衡的破坏:“一个人若因身体机能紊乱而无法完成预期的任务,这就将被同类视为‘有病’,而在这类生理机能紊乱中,又有许多源自与寄生物的接触。”[6]6从根本讲,“疾病是一个生物过程。人体组织以正常的生理反应对正常刺激作出回应。它对千变万化的环境有着高度的适应性。……当刺激的数量或质量超出了生物体的适应能力时,生物体的反应也就不再是正常的,而是反常的,或病态的。它们是疾病、受损器官功能或防御机能(它总是极力战胜损害)的征兆。疾病只不过是生物(或它的某些部分)对异常刺激所作出的异常反应的总和”[9]。因为当一种以生理机能紊乱为实质的疾病群体性出现并产生跨区域传播时,人类与微生物之间脆弱的共生平衡体系被打破;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肆无忌惮地侵入人的身体,人类成为微生物的受害者。但就人类与微生物世界的关系论,人类成为微生物的受害者,仅是其结果呈现,溯其根源,首先是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成为人类的受害者。从存在的本原性结构看,人类存在与生物世界构成一种因果链条,这一因果链条得以构建的实质是食物链:人类与生物、人类与微生物之间建立起来的食物链,构成本原性存在的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维持的是一种松散的、不断变动的平衡,这种平衡尽管可能偶尔或暂时在时空上有一定的变化,但却能有效地抵制剧烈的、大的变动。人类狩猎者虽然登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他们以其他动物为食,又不致为别的大型动物所食,不过,这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变这些恒久的生态关系,人类虽以胜利者的姿态取得新的生态地位,但其总体来说并没有改变生态系统本身”[6]16-17。原因何在?宇宙创化之初所设计的生物与微生物以及物种之间的食物生态链,既是不易改变的,也是不能改变的;并且微生物与微生物之间、微生物与生物之间、物种与物种之间所形成多层级食物链具有各自的边界和限度,这个边界和限度构成了生物与微生物、生物与生物、物种与物种动态的共生平衡;一旦生物与微生物、生物与生物、物种与物种之间的边界被突破,限度被消解,整个生物和微生物世界的共生平衡的生态秩序就会变乱,微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生物、物种与物种之间就会相互伤害,并且互为病毒源。人类原本是生物世界之一普通物种,只因在流浪生存的进程中因为许多偶然因素会聚其身而形成层累性改变,这种改变被生物学命名为物种进化,被人类文化学名之为文明。高度进化的人类物种一旦忘记他本身的出身和忽视自己原本存在于自然世界并与生物、微生物共生存这一事实,就会心生狂妄和自大。一旦人类以狂妄自大之心发动持续扩张的跨界行为逼近这种改变他与自然之共生平衡的临界点时,就会引来整个自然界包括微生物界的反跨界运动,各种形式的气候灾害、环境灾害以及诸如天花、鼠疫、霍乱、疟疾、伤寒、黄热病、艾滋病等等,都是人类持续扩张的跨界行为所结出的恶果;21世纪后期以来所暴发的各种流行性疫病,仍然是自然界、生物界甚至微生物界对人类跨界行动的“报复”。先后发生的SARS、H1N1、H1N9、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和新冠状疫病等,就是微生物界对人类的跨界侵犯作出的反跨界报复,并且微生物界对人类跨界的报复活动,是一次比一次猛烈,人类为此承受的代价一次比一次高昂,这可以从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流行疫病的扩张程度和持续时间的对比中体会到这一趋向。
二、疫病传播的“环境”之维
进入21世纪以来,先后出现SARS、H1NI、H1N9、埃博拉病毒等,这些当代生活世界出现的传染性疫病得以引发的直接病毒源却是野生动物。这恰恰暴露了这类直接源于野生动物的传染性疫病,都与人类的口腹之欲直接关联,即人们满足口福之欲的行动直接指向生物世界,并且,为了源源不断地满足人的口福之欲,人对生物世界实施了无止境的跨界侵犯,并在这种跨界侵犯生物世界的过程中无意地跨界侵犯了微生物世界。所以,21世纪以来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冠状性病毒疫病,大多不是天降其灾于人,而是人自降其灾。
人自降其灾,是如何做到的?
这就涉及人类向自然和环境要存在、要生活的双重现实。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而征服自然、改造地球、掠夺环境资源的无穷进取运动,以不经意的方式持续不断地破坏环境所形成的负面影响力层累性生成,最后以“一根稻草压倒一只骆驼”的方式实现了“自降其灾”。因为在人类向自然和环境要存在和要生活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改变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不断地发明新技术提升生产能力,并不断地发展交通和通讯以求无限度地压缩自然时空等社会化作为所造成的负面力量,都会无声地以会聚方式推动形成对环境的层累性破坏,造成人类修复环境使之达成动态平衡关系能力的削弱,也造成了环境自恢复、自净化、自调节功能的丧失。要言之,人类(无意地)破坏环境的根本性力量主要由如下三大要素会聚其他因素自动整合形成。
其一,生产方式。在生产方式上,人类走了一条舍渔猎而种植,然后开垦土地开辟农业生产方式,进而创造出工业生产模式,并以机械技术推动深耕农业的同时,又以机械技术征服自然、改造地球、掠夺性开发环境资源,直接造成了三个互为影响的生态学后果:一是地球生境全面遭受破坏,物种大量灭绝,生物多样性减少,人与地球生物包括微生物之间的动态共生平衡链条破损甚至部分断裂。二是从地下到地面再到太空污染立体化,地下水和地面水系、大地、江河湖泊海洋和大气层的自净化功能整体性丧失,造成的恶果是酸雨天气和雾霾气候日常化。三是气候丧失周期性变换运动规律,气候变暖,冰川快速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降雨违时,高寒与酷热无序交替。尤其是气候失律,不仅导致了整个地球生境破碎,而且为各种疫病的暴发和恣意传播提供了土壤。从根本讲,地球与宇宙的动态循环,才使世界成为充满生机的活动的世界。但地球与宇宙的动态循环却要通过气候来调节。气候一旦丧失周期性变换运动规律,最终导致整个世界动态循环的宇观生态链条断裂,从而改变整个自然界及其一切存在,人与生物世界及微生物世界之间的动态共生平衡也由此被打破,形成逆生态化运行。
其二,人口生产。人类要使自己持续存在,必须展开两种生产,即人口生产和物质性生产,前一种生产是生物主义的,后一种生产是生存主义的。比较地看,生物主义生产具有双重性:一是,它构成生存主义生产的奠基性生产,因为只有生产出劳动力,才可强有力地展开物质性生产;二是,它也成为生存主义生产的负担,因为物质性生产的起步是解决生存,但目标指向却是实现更好的生活,而生物主义的人口生产一旦超过地球承载力限度和人类物种限度,就会将生存主义的物质性产生创造的财富大部分用来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尤其是用于解决贫困问题,由此实际上降低了发展,也延缓了发展。最好的例子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努力就是解决生活贫困问题。从根本讲,人类不断地改变生产方式加大物质性生产的不可逆努力方向,是为了更安全存在和更好生活,但起步和前提却是能够生存。在人类早年,能够生存的压力主要来自自然界。自从渔猎社会进入农业社会以来,这种压力却越来越多地来自人口生产所形成的人口大增长,它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人口对地球的压力,因为能够为人所利用的土地有绝对限度,有绝对限度的土地之自身生产力也是有绝对限度的;而男女基于生理需要而“必须结合”[10]所产生的生育运动,却始终呈无限度朝向,“人口增殖力与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11]8,其基本方式就是抑制人口生产,因为“人口若无受到抑制,会按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比率增加”[11]9;二是人口生产形成对社会的压力,因为人不仅是需要资源滋养才可存在的存在物,也是具有特别强烈消费欲望的存在物,不断生产出来的人口均是可数的,但被生产出来的人口的欲望却是无限滋生的,所以,逾越地球承载力的人口之无穷欲望构成了社会不堪重负的压力。从整体观,前一种压力导致人类生存不断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展开无止境的跨界运动,人与自然、人与生物以及人与微生物之间那种极为脆弱的动态的共生平衡关系被强行打破,人与自然、环境、生物、微生物之间呈紧张状态,疫病就是这种紧张状态的产物。后一种压力导致人类居住方式的畸形发展,这就是城市化、都市化和居住空间的高楼层化,这“三化”将原本自然地居住的人口高度地密集起来,这种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为疫病的暴发提供了温床。
其三,技术。技术原本因解决生计而产生,也为解决生计问题而开发运用,后来拓展到生计之外的所有生存领域,形成最强大的生存功能:不断开发的技术,不仅强化了竞斗,并成为所有战争的推拉力,或可更准确地讲,为解决生存问题而产生的技术得以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却是或为预防战争或发动战争或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尤其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变革和发明的技术都原发于军工领域。技术向民营领域推广和拓展,不断地改变通讯手段、交通工具和运输方式,大大地缩短了时间并压缩了空间。自然时空的高度压缩,恰恰为疫病的高速传播,开辟了空间渠道,提供了广阔舞台。疫病,就其发生学论,始终是地域性的,但就其生存变化论,它却总是会搭乘技术的便车而获得传播的力量,尤其在城市化、都市化、洲际化交通(高速公路、飞机、高铁)特别发达的今天,疫病的传播更是如鱼得水,比如新冠状病毒,无论它源头何处,都是地域性的,但它迅速蔓延于世界170多个国家,却得益于特别发达的城市化、都市化、洲际化的交通,即航空、高铁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
以上三个因素形成的整合态势恰恰表明,已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的今天,全方位敞开全球生态危机的环境问题,已经不只是一个严重的自然问题,它更是一个严重的人力问题。通过世界大流行的疫病这面镜子,环境生态问题的人为性,是必须正视的事实。因为环境生态问题不仅直接构成了各种环境疫灾暴发的现实场境,也直接构成了各种流行性疫病肆虐的现实场境。检讨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地域性暴发的疫病何以能够世界性流行,自然要追溯到如生产方式、人口生产、技术等方面,是这些因素整合生成无止境地征服自然、改造地球、掠夺环境资源所造成;但同时还不得不正视自然时空被高度压缩之后的交通、通讯、运输和由此交通、通讯、运输所改造形成的生活方式、行动方式。这种高时空压缩的生活方式和行动方式却从整体上体现两个特点,那就是快和灵敏。快和灵敏,既是对空间的要求,更是对时间的要求。一旦其快和灵敏被悬置起来,就会酿成巨大的灾与害。
三、避免疫灾的环境治本之道
世界是由个体组成,但任何个体都是“一个世界性存在者”[12],这是因为社会是由于人与人互借智、力谋求安全存在和可持续生存而共同缔造。人所共同缔造的社会不仅不能脱离自然,而且只能嵌含在自然之中。将社会嵌含于其中的自然世界一旦被人意识地对象化,它就构成环境。
其一,环境作为被意识地对象化的存在世界,它是我们意识到的存在世界:“作为被人们意识到的存在世界,既是整体的,也是开放的。环境的整体性,揭示环境既是一个复杂系统,更是一个开放系统。”[13]它也是我们尚未意识到或意识不到的存在世界,包括人力不及和想象不及的那部分存在世界。但是,不管我们意识到或没意识到,由存在世界本身构成的环境始终存在,而且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相反,人却依赖环境而存在。并且,环境以什么方式存在,是由环境自身决定,与人无关。环境的这一存在事实决定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只是一种外在化的存在关系,从功能角度观,人与环境所形成的这种外在关系,本质上是使用关系,即是人要使用环境,而不是环境要人使用它。人对环境的这种使用关系,也可尊重环境的自存在方式,也可不尊重。如果选择前者,人与环境共生;如果选择后者,人与环境逆生。因为选择后者,人可以按自己的欲望作为环境,造成的实际结果是环境生境破坏,环境灾害和疫病必然丛生。
其二,环境作为我们意识地对象化的存在世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世界,并且这个开放性的世界不仅使人这一物种存在其中,也使其他生命和存在物存在其中:使一切存在于存在世界之中,是一切存在本身存在的需要使然,而不是存在世界使然。
其三,环境作为我们意识地对象化的存在世界,既涉及自然世界,也涉及人的世界,但其所涉及的既不是自然世界的全部,也不是人的世界的全部:我们存在于其中的环境,只是我们的人力(行动力、控制力和想象力)所涉及的世界。人力无论以哪种方式作用于自然,所指涉的只是一部分,因为我们的行动、控制、想象只能涉及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所涉及的那部分自然,才构成我们的环境的一部分,人力所不能涉及的更大的部分,则始终是自然世界;我们所涉及的人的世界,也是如此,比如人的历史世界、人的未来世界、美洲世界和欧洲世界,我们只能部分地涉及。
其四,我们意识到的存在世界虽然只能部分地涉及,未涉及的部分并不截然与我们无关,而是相反,无论自然世界还是人的世界,未被我们涉及的那部分始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我们的存在发生作用。比如,冰川、遥远的太空或无以计数的星球,它们的存在状况始终对我们的存在环境产生影响;冰川的融化,导致海平面升高,我们赖以生存的陆地因此而减少,而且气候变暖,将引发各种环境灾害爆发或瘟疫流行。又比如,无论非洲或欧洲,亚洲或澳洲,其社会的变化或祸福的产生,都对每个人产生当下的或未来的影响。切尔诺贝利核爆炸所释放出来的毒气,可能已经通过空气污染和对地下水层的污染而影响了全球,日本的海底核泄漏排放出来的有毒物质,可能早已进入了那些喜欢吃海鲜和生鲜的人们的身体之中,只是更多的人不知情而已。综上,环境作为我们所意识到的存在世界,由三部分构成(见图1):

图1 构成环境的三维视野及其内涵
我们存在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由周期性变换运动的气候所统摄。美国环境学家麦克基本断言:“我们终结了自然的大气,于是便终结了自然的气候,尔后又改变了森林的边界。”[14]这是因为自然的气候是以周期性变换运动规律的方式敞开降雨有时的运动,人类因为更好地生活而持续不断地征服自然、改造地球、掠夺环境资源造成的最严重的生态学后果,就是终结自然的大气。所谓终结自然的大气,就是使气候丧失周期性变换运动的规律而做失律运动。气候失律推动了大气气温和地表温度的无序改变,这种无序改变导致了温室效应或寒冷效应,即一部分地区气候骤然变暖,另一些地域气候突然变冷,或者同一地区高寒和酷热无序交替,这种失律的气候突变必然改变地球温度,最终改变地球表面性质[15],地球的存在状态由此发生巨大变化,反过来又推动气候失律运动加剧。世界历史学家弗莱德·斯派尔(Fred Spier)指出:地球“板块构造可能在推动生物进化(包括人类进化)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地球陆地物质的位置不断变化导致了洋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影响了全球气候。我旨在举例说明生态和气候体系在影响人类进化方面的主导作用。”[16]从根本讲,地质结构变化与气候失律之间呈互动取向,这一互动取向的实质呈现是气候失律与灾疫频发之间构成互生关系:“一方面,气候失律制造出各种人间灾疫,推动当代灾疫失律;另一方面,当代灾疫失律又加速了气候的恶化。气候失律与灾疫失律的互动,演绎出当代世界风险社会和全球生态危机。”[17]
整体理解我们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的真实构成,是面对频发的疫灾而谋求标本兼治环境的认知前提。从根本讲,要避免疫灾再发生,需要标本兼治环境。所谓标本兼治的环境,首先指自然环境。我们存在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原本就存在宇观、宏观、微观三个维度,所以对环境的表层治理,就是恢复地球生境,这需要通过退耕还草,退耕还湖,退耕还海,禁伐森林,退牧禁游恢复草原,疏通江河,恢复陆地和海洋的自净化功能,进而恢复大气层的自净化功能,然后才可进入根治领域,恢复气候的周期性变换运动规律,使之降雨有时。这是抑制、减少、避免流行疫病频繁暴发的存在土壤。
历史地看,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只有适应自然,并有以自然为师、向自然学习的能力。但这种状态最终被改变,从农牧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再至今天技术化存在的后工业社会,人类早已在自然面前变换了角色,由拜自然为师、向自然学习转化为以自己为师、向历史学习。这一角色转变的根本要义是:人类存在从遵从自然的律法转向了对自造的律法的崇拜。从人类生存发展史观,其从承受天灾到自造疫灾所呈示出来的轨迹,恰恰是抛弃自然律而自崇人造律的狂妄轨迹,所以根治人存在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其根本前提是在认知上彻底改变人类的自我崇拜,这需要重新回到自然,拾起早已抛弃了的自然律法,遵从它[18]。以此为起步,才可真正展开社会环境的治理。因为在人所存在于其中的环境里,自然环境是土壤,社会环境是根基。要真正治理自然环境,使之达于恢复,使地球重获生境,使气候恢复周期性变换运动规律,其施治的根本功夫应用在社会环境方面。
治理社会环境,本质上是治理人欲。人欲既是立体的,也是发散性生成的,没有静止、没有边界、没有最终的满足。在可无限滋生和繁殖的人欲中,最根本者有三,即性欲、物欲和权欲。其中最为坚挺的是权欲,因为权欲的满足可以无限地保障性欲和物欲的满足,反之则不能。所以,在由人组成的世界里,人欲构成社会环境之本,但权欲却成为社会环境之根。治理环境的目标是治理人欲,但重心是治理权欲,其根本方法只能是法治。为此健全法权政体,完善法权制度,构建法权体系,将一切形式的权力关在“一切断于一法”的笼子里。
要能通过法的方式实现对人欲的治理,需要展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整合推进的社会认知治理。所谓社会认知治理,就是治理社会认知。治理社会认知的实质,是对主导社会的认知体系的纠偏。这个需要纠偏的认知系统,由物质主义幸福观、消费主义生产观和享乐主义生活观三者构成,并且此“三观”共谋生成建构起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以它为导向形成了唯经济增长主义的发展观和无边界的竞争主义价值导向。这是古典工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认知土壤,也是人类竞争活动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个领域无休止跨界的动力机制。为避免疫灾再发生的社会认知治理,就是全方位地纠正如上畸形的社会认知体系,其根本的努力如下:
纠正片面发展的认知导向,确立“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认知导向。客观地讲,以单纯的经济高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这一认知导向,体现普遍的可激励性,在发展的起步阶段体现正效应,但是,在发展持续展开的历史性进程中,发展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如何调动发展的积极性和热情,而是如何引导人们理性地遵从规律和法则,有限度地发展的问题。环境生态危机和疫病世界化传播,则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警示人们:更应该理性地认知到生存比发展更根本;并且,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安全存在和更好生活而致力于恢复地球环境生境和防治新老疫病,都是为生存而战。这种为生存而战所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发展付出的代价,所以决不能忽视生存本身去盲目地追求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
以可持续生存式发展为硬道理认知导向,重建社会认知系统,必须确立一个生存准则,建立一种社会机制,重建一种社会结构。
为避免疫灾再发生而重建社会认知系统所需要确立的生存准则,就是“环境优先”[19]。确立“环境优先”的社会生存准则,是对“发展优先”的社会生存准则的动态调整,因为“‘发展优先’思想的落实,就是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实质有二:一是追求唯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唯经济增长模式和‘GDP’政绩评价模式。二是主观主义和唯意志主义:所谓‘跨越式发展’,就是跨越条件、环境、规律、法则的发展,所以,跨越式发展就是无视现实条件,不讲环境,抛弃规律和法则的发展,本质上是一种野性的发展,这种发展所伴随的只能是高浪费和高消费”[20]。其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无休止的跨界活动,形成对地球环境、生物环境、微生物环境的扫荡性破坏,导致疫病频发。化解人类与地球环境、与生物世界和微生物世界的紧张生态危机的根本努力,就是终止这种无底线的跨界运动,但前提是调整发展优先,建立“环境优先”的指导思想和社会生存准则,敬畏环境,尊重自然规律,因为“尽管我们许多人居住在高技术的城市化社会,我们仍然像我们的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的祖先那样依赖于地球的自然的生态系统”[21]。
为避免疫灾再发生而重建社会认知系统所需要建立的社会机制,就是“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这一社会机制不是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动力和目标,而是以国家社会安全存在和可持续生存为动力和目标[22]。
为避免疫灾再发生而重建社会认知系统所需要重构的社会结构,就是“小消耗、大节约”和“限度开源、无限节流”的社会结构[23]。从根本讲,“高消耗、高浪费”和“重视开源、忽视节流”的社会结构,既是造成社会资源和财富高耗费的重要原因,更是层累性催生环境灾害和疫病频发的根本性动力。因为,个人的高消耗和高浪费,并不构成社会结构,只有当社会组织、机构甚至政府高消耗和高浪费的持续展开时,才形成高消耗和高浪费的社会结构,这种高消耗和高浪费的社会结构才推动社会个体形成高耗费和高浪费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所以,当社会结构化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或政府机关倾向于高耗费和高消费,自然形成浪费性消耗财富和资源的社会运作机制,形成社会结构性消耗和浪费有限社会财富和资源就越多,各种形式的垄断力量就呈更加绝对的刚性取向,片面追求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必然推动社会经济活动和消费活动无底线地跨界,最终层累性造成环境灾害和疫病灾难。与此相反,“小消耗、大节约”和“限度开源、无限节流”的社会结构,首先要求政府没有冗员并且机构精简,形成对社会财富消费小,但却能够发挥大功能,产生大功效。所以,“小消耗、大节约”和“限度开源、无限节流”的社会结构,可推动所有的社会组织、团体、机构以及政府,真正做到“禁役止夺”和避免“与民争利”。并且,唯有建立起“小消耗、大节约”和“限度开源、无限节流”的社会结构,社会才大,或者说社会才成为大社会。所谓大社会,就是通过“社会来管理社会”“社会来引导社会”和通过“社会来规范社会”的社会,从根本讲,大社会是通过建立一种机制来推动人人自律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仅追求平等的权利,更是人人具有担当责任的能力。所以,“小消耗、大节约”和“限度开源、无限节流”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人人自觉担当责任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本身就构成一种整体的力量,引导社会走向节约、尊重环境、敬畏生命、维护自然,实现人、社会、自然、环境的共生存在,这是消除环境灾害、避免疫灾的社会土壤。
以上述三者为规范和引导,探索一种生境经济。所谓生境经济,就是尊重市场规律、自然规律和健康规律的经济,即通过经济活动促进社会和人的健康的发展,并在其健康发展过程中实现有限度的经济增长:“在当今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已经认识到重新定义的必要。经济增长无视限制的存在,因此会对生物群落造成破坏,若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代名词,那么发展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就值得怀疑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科技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单纯在数量上的增长给地球所带来的负担已经快接近地球的承受极限了。而其他方面的发展,如经济发展在质量上的提高,生产工艺上的进步,更为有效、创新、节约的资源利用方式的发现,以及道德上更为宽广的包容性,都会起到积极作用。这些领域的发展可以帮助保护而不是摧毁地球生态圈。”[24]就经济本身言,生境经济是一种“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25]的节制经济,它遵循经济对自然的“嵌含”法则和经济对环境的“用废退生”规律,“经济嵌含在环境之中。在这种嵌含规律的控制下,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之间呈相反的矛盾张力取向:经济发展必以环境为代价,经济每向前发展一步,环境就向后倒退一步;经济全速发展,环境就全速后退;经济无止境地发展,环境就遭受全面破坏而死境化。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是‘用废退生’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正面表述是:经济发展越缓慢、越有节制,环境就越具有自生境的恢复功能。反之,必然违背‘用废退生’的规律,其‘竭泽而渔’的发展大跃进,只能加速环境的全面崩溃。”[26]生境经济方式的真正建立,必然形成对社会的健康哺育,最终建立起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这是避免疫灾再发生的真正社会化的和深入人心的防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