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蚕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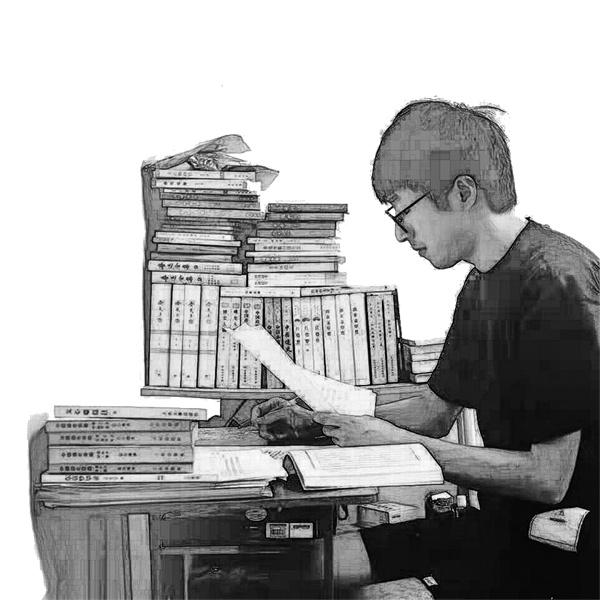
吴灵烽
二年级那年初春,我得了些蚕卵,它们紧密地附着在一小块瓦楞纸板上。待天气回暖后,细黑的幼蟲争相破壳而出,我撕下练习簿上的纸粘成小盒,用作它们的家。幼蚕极小,一夜下来,桑叶只能被啃出几个很小的洞,余下则整片枯去。每天睁大了眼,把它们一条条拨到新鲜的桑叶上去是必修的功课,这个过程持续到蚕身泛白后就好了,而桑叶也在那时开始紧缺起来。母亲得知后,买来一株桑树苗送到教室,引得同学直呼“哇!桑树欸!”当即就来与我约定,“阿烽,以后要给我桑叶啊”,我满口答应。可是迫切的心等不及树苗长大,我依旧去各个村子找桑叶,顾不上回家吃饭。
蚕再大一些后就可以搬进鞋盒里了。去上学前往里面放几片桑叶,到傍晚就只剩摇头晃脑找食物的家伙了;夜静下来,听得见“窸窸窣窣”的啃食声。有一天,母亲带回来一些别的叶子,告诉我这个蚕也可以吃,疑惑的我还是抓了几片放到盒子里,只见饥肠辘辘的家伙们仰起头,在新食物上一圈圈扫食下来。母亲真厉害啊,我心里暗暗地说。后来我在家门前的河边看到一株树上也长了很相像的叶子,便摘了来喂蚕,却不想第二天蚕宝宝全部伸直了身子一动不动了。我以为养蚕的事到此为止了,终日闷闷不已。
没过几天,母亲又带回来一袋桑叶,并把袋子拎到我面前,“看!这是什么?”原来母亲问厂里人要了十几条蚕,听说对方的女儿与我一般大,养了比我更多的蚕。这些新来的白胖子一点也不认生,只埋头在桑叶上横扫。
蚕身越发洁白细腻了,食量更是大增,而在蜕去第四次皮后,却不大吃了,似乎在找什么。我有点急,母亲举起一条蚕放到灯泡下看,“肚子亮光光了,可以上蚕山喽!”然后放下蚕便转身出去了,过不多久拎进来一只篮子,里面折了一大把秸秆。母亲把蚕一条条拎出,对着灯光看,“嚯,这条也锃亮的!”然后把它们轻轻地放在秸秆上,也有因为“不够亮”而放回鞋盒里的。“为什么把它们放在稻杆上啊?”“这样它们不会饿死吗?”母亲没有解释太多,只告诉我它们不吃东西了,要上山做茧了。
果然,上山两天,秸秆丛里长出几个白白黄黄色泽很纯净的东西来,我方知那一个个椭圆体就是蚕茧。也有还正在吐丝织茧的,隐约看得见它们奋力舞动的姿态,比在鞋盒里柔弱乖巧的样子有力量得多。丝层越来越厚,慢慢看不到蚕了,想必它们也累了,该休息了。我把蚕茧一个个从“蚕山”上取下来,依旧放进鞋盒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一切未知在破茧成蝶的那天都清晰了。可是面对素雅大方的飞蛾,我却感到陌生,对它们的感情好像突然就淡了。接着,它们找寻配偶,雄蛾在交尾后死去,雌蛾在产下大片的卵后,也完成了简短的一生。淡黄的卵紧密如麻地附着在鞋盒上,我把盒子剪成一块块不大的纸片,用塑料袋包好,等待着下一次生命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