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玄幻小说进化的叙事与复归的传统
于经纬 张学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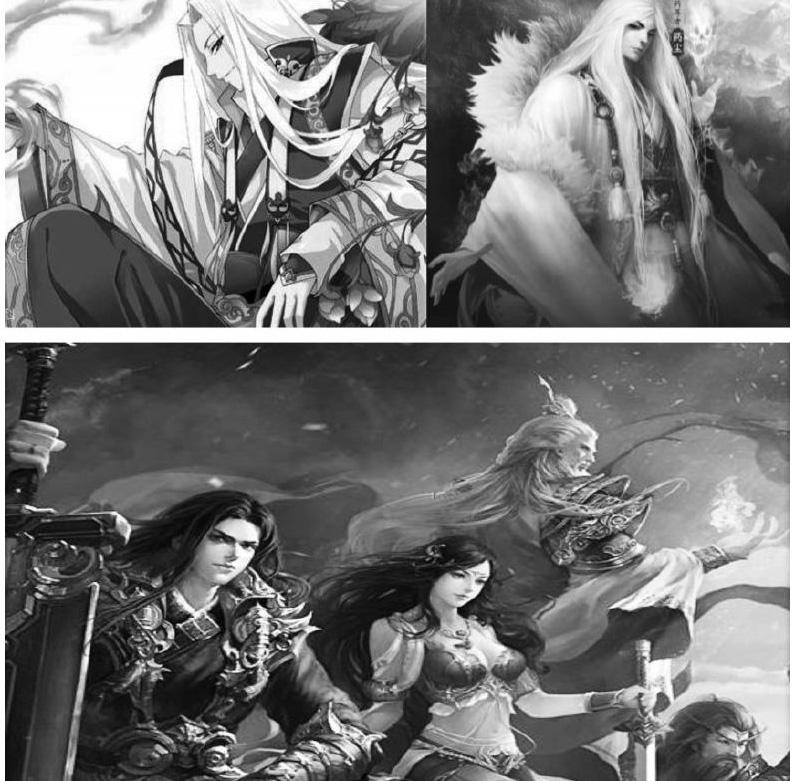
2009年4月,经历了处女作《魔兽剑圣异界纵横》的业绩惨败之后,天蚕土豆(李虎)开始在起点中文网创作他的第二部玄幻小说《斗破苍穹》。令天蚕土豆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小说迅速成为当年起点玄幻小说各种排行的榜首,并且在十年后的今天依然雄踞起点月票榜的前十。或许这种成功对于十年前的李虎来说多少有些偶然,但是从《斗破苍穹》文本本身来说,这种成功又有着某种必然。可以说,《斗破苍穹》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国网络玄幻文学发展的一个拐点,它的成功是当代网络玄幻文学在叙事言语上的一次进化与定型,也是当代网络玄幻文学在“内面”对于通俗小说的某种复归。更重要的是,这种进化与复归凭借着《斗破苍穹》的爆红与持续发酵,实际影响了当代中国网络玄幻小说的创作途径与书写模式。
一、进化:标准叙事言语的形成
2003年,《诛仙》在幻剑书盟网站开始连载并迅速蹿红起来。这无疑是沉潜了四十余年的仙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的复兴。随后的几年,仙侠类小说占据了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然而真正令人犹疑不决的问题是自《诛仙》以来的仙侠小说,比如《搜神记》《凡人修仙传》《缥缈之旅》《星辰变》等其分类是在仙侠与玄幻之间来回摆动。换句话说,欧美的魔幻/奇幻文学(la literature fantastique①)在2000年前后开始大量译介,导致了中国本土的仙侠文学开始出现了所谓“玄幻”的倾向性,但是这种倾向性在2009年之前有影响力的作品上却又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实际上,在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中,直到2009年《斗破苍穹》出现,才意味着中国本土网络小说中玄幻类型的诞生,使玄幻文学能够在概念上彻底与仙侠文学进行区分。②
李虎的《斗破苍穹》能够实现玄幻与仙侠之间的彻底分区,其实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一是叙事类型的复合化;二是描述言语的图像化;三是去象征化的言语系统。
不论是明清通俗白话小说,民国通俗文学,还是网络文学,往往都会根据小说叙述的核心内容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类型都具有相对明显的特征,一如《封神演义》属于魔神小说,《七侠五义》属于侠义公案小说,《江湖奇侠传》属于武侠小说等。即便是网络文学,其本身也有较为清晰的类型划分,以《诛仙》为代表的修真系的仙侠小说,以《步步惊心》为代表的宫斗言情小说等。不过,与2009年之前的火热的仙侠小说相比较,《斗破苍穹》的故事本身很难说属于特定的某种类型,除非用“玄幻”来描述它。总而言之,《斗破苍穹》作为网络玄幻小说,它最大的特征在于叙事类型的复合化。
与较为传统的修真仙侠小说《诛仙》《凡人修仙传》《缥缈之旅》相比较,《斗破苍穹》并没有在中国传统的魔神、仙侠、宗教等话语体系中尋找表达词汇,而是使用完全独创的方式来设立自己的世界观③。用小说自己的话说就是:“这里是属于斗气的世界,没有花哨艳丽的魔法,有的,仅仅是繁衍到巅峰的斗气。”④姑且不论小说“内面”性质的问题,仅从概念本身来讲,这种设计已经完成了对仙侠类型,抑或说对中国传统仙侠文化,至少是概念层面上的脱离。这种脱离就导致了小说在叙事层面摆脱了典型仙侠类型的桎梏——以修真为终极目的叙事言语——转而开始依靠李虎本人独特的想象力开始对各类型的小说进行混合。
单就《斗破苍穹》故事而言,除了包含有贯穿整部小说的“斗气”话语系统下的修真体验,在其具体的叙事中显然可见长篇章“侦探”类故事、“侠义”类故事,甚至于某种程度上的“言情”类故事。贯穿故事“斗气”修真很大程度上只是推动不同模式间故事叙述转型的工具,而非像《缥缈之旅》《凡人修仙传》等小说一样是作为小说的终极目标存在。因此,可以说《斗破苍穹》的叙事是对2009年之前大多数主流仙侠小说叙事模式的逆转,故事不再为目的服务,而衍生出系统下的故事模式复合化。正是这种小说的复合化,使得《斗破苍穹》作为典型的网络“玄幻”小说在阅读体验方面与《诛仙》等小说产生明显的异样感。
除了叙事类型的复合化,《斗破苍穹》另一个重要的叙事特征在于文本言语的图像化。图像化不同于形象化。一般而言,在经典文本中的人物角色的形象化意味着作者力图向读者传达一种特定人物外在或者内面的独特特征,从而使其文本角色与其他人物作出区分。尽管有着“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来意指经典文学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但是哈姆雷特作为一个独特且与众不同的文学形象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不管刻意为之还是无意之举,《斗破苍穹》图像化的描述语言恰恰放弃了经典文学中的这种追求,或者说他用另外一种形式言语替代经典的形象化。
最典型的图像化言语,就是在《斗破苍穹》中对于药尘的描述。实际上,小说根本缺乏对药尘这个主要角色的描述性言语,在相当长的篇章内,唯一具有描述性特征的词汇只有萧炎对药尘的称呼——“老者”。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个“老者”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老人,尤其是对于《斗破苍穹》此类玄幻小说的真正读者而言。实际上,在绝大多数的对《斗破苍穹》二次创作中——漫画、游戏等——都没有将药尘视为我们在经典文学所理解的“老者”形象。
上面三幅图分别是药尘的漫画形象以及游戏形象。如果依照经典文学对于人物形象的理解,这三幅图像所绘制的药尘可以说完全是三个不同的人物,如果仅仅从图像来说甚至于三个人物差异不仅存在于外貌上,而且存在于人物内面之中⑤。然而,不论图像之间的反差多么剧烈,对于小说而言,对于读者而言这些都是药尘。实际上,在《斗破苍穹》中李虎对于各种人物的描述言语都是相对匮乏的,这是小说中真实存在的问题。不过,对于具有故事复合化性质的小说而言,这种描述语音的匮乏恰好实现了小说人物的图像化。这种图像化并不依靠文本描述性言语引导读者,而是在一个一个不同类型故事中,通过人物的差异性行为表现促使读者完成对于人物图像的独立想象。换句话说,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类型的故事获得某种情感共鸣后,便独立地产生具有个体经验偏好的独特想象。比如对于小说“言情”类型故事有偏好的女性读者,往往对于药尘想象更接近图一;而喜欢萧炎、萧薰儿、药尘三人征战四方的“魔神”类型故事的读者则可能更偏爱图三的药尘。
与2009年之前同样具有影响力的仙侠小说相比,无论是《诛仙》《搜神记》之类都还延续着经典文学对于人物塑造的基本要求,努力地使用描述性言语,比如《诛仙》中对碧瑶的颇具特征性的描述几乎使碧瑶的形象完全定型。以叙述性情节替代描述性言语的人物图像化虽然未必是《斗破苍穹》的首创,但是这种文本言语形式却借由《斗破苍穹》的影响力,获得爆发性的推广,很多网络小说,尤其是采取复合型叙事的玄幻小说都采用这种言语策略。实际上后来唐家三少在《斗罗大陆》中也几乎全部继承了李虎的这种言语类型。
進一步说,在叙事类型复合化与描述言语图像化的基础之上,《斗破苍穹》完成了当下作为类型的网络玄幻小说言语特征的塑造——去象征化的言语系统。
这里的“象征”是对波德里亚的符号理论概念的借用。在波氏的理论中,象征意味着符号与意义具有对应性,也就是符号能够产生特定的意义⑥。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尤其是经典文学作品,其言语本身作为符号系统,意在传达人生中呈现的“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⑦。换句话说,在经典文本言语中,可以去追寻其言语作为符号而具备的象征意义。实际上,这种言语的象征不仅存在于经典文本之中,严格来说,大多数现代小说的写作都理应具有这种象征意义。即使如典型的奇幻小说《魔戒》《纳尼亚传奇》与《地海传奇》等,其言语符号都有着深刻的象征意旨。同样,早期的仙侠小说,作者们也尽力地想要在文本中为言语符号与象征意义搭上一条桥梁,典型如《诛仙》中文本始终面对并讨论着善恶正邪之间的辩证意义。当然,中国网络仙侠文学由于多种原因使得言语符号的象征意义一直持续减弱,直到《斗破苍穹》出现,终于得以彻底完成文本言语的去象征化。简单而言,读者不必再去向文本要任何可能存在的微言大义,文本言语的直接意义就是文本的意义。
实际上,在描述言语图像化的特征中,这种去象征化呈现得最为明显。人物不再由描述言语所构建,也不是被作者创造的、与其他文本人物形象有着差异的独特性存在,而是随着描述性言语的消失,变成在故事讲述过程中任由读者想象的一种图景。这一过程显然颠覆了经典文本对于人物形象描述言语的象征意旨,显而易见,在言语符号的缺失处境中,象征是不存在的。然而,这种去象征化的言语并不意味着文本对于读者而言缺乏吸引力,或者缺乏意义。去象征化的言语系统是将经典文本中对于独特人物或者事件的描述意义直接转化为故事,只有在言语符号直接意义等同于文本意义的情况下,故事叙述上才能完成不同类型随意转换而不至于发生内面上的矛盾。试想一下,如果一套有着复杂象征意义的言情言语系统在寥寥数行之间迅速转换为激昂热血仙魔斗法,其人物的内面上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前面还在忧郁惆怅情绪悲悲戚戚,突然间就挥手斩妖除魔英姿飒爽——矛盾感。正是基于去象征化的言语,使《斗破苍穹》在各个类型故事之间随意切换而并无矛盾,更重要的是,去象征化的言语为另外一种复归提供了可能。
《斗破苍穹》在2009年的迅速爆红,其实是中国网络仙侠小说发展进化的集成表现。在几年的仙侠小说写作努力的基础之上,由李虎将当代网络玄幻小说叙事系统最终稳定下来。这既是当代网络玄幻小说在叙事形态上的进化,同时也标志着在这种进化之下的某种传统的复归。
二、复归:玄幻网络小说的“通俗”传统
《斗破苍穹》一方面奠定了当下网络玄幻小说叙事形式的基础,另一方面则展示出网络玄幻小说在某些内面特征上的向传统通俗小说的创造性继承与复归。
《斗破苍穹》所使用的叙事类型复合化写作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章回体小说《儒林外史》。如果说《儒林外史》与《斗破苍穹》在不同故事类型、人物图景之间相互转化在形式上的重要差异在于“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⑧的话,那么在晚清出现的章回体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用主角“九死一生”连缀众多类型差异的故事则可以说是标准的叙事类型复合化的写作策略。进一步说,学者对于章回体小说研究也提出了“故事集缀”的构型⑨。可以说,《斗破苍穹》叙事的复合化,是对传统通俗小说中惯用“故事集缀”构型的创造性转化。它在传统“集缀”基础上,添加了能够贯穿故事始终的主干系统。正是由于《斗破苍穹》突破了繁杂而缺乏连缀性的传统文化词汇术语,转而使用自己设计的更为严格的且成体系的当代玄幻系统,才促使小说在连缀多类型故事的同时克服了传统章回体的裁断感,保持了连载故事的完整性与情节的集中性。
实际上,在《斗破苍穹》之前,很多网络仙侠小说本身都对采用复合化叙事存在一定程度的抵触。中国网络仙侠小说的兴起与欧美奇幻小说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广义上欧美奇幻小说是一种通过“吞噬整个文本世界,连同读者在内”,进而形成的一种“包含了真实与虚构的对立”的文学存在⑩。《魔戒》《纳尼亚传奇》等经典模式的欧美奇幻本身就包含着历史与文化隐喻因素,文本本身也作为一个整体的故事存在,无论是在中洲大地上对抗邪恶,还是在纳尼亚的土地传颂基督神圣。欧美玄幻小说这种整体性直接地影响了中国网络仙侠类小说创作,不只是《诛仙》《九州》,即使追溯更早的小说比如《悟空站》《轻功是怎样炼成的》等诸多具有仙侠或者玄幻性质的小说,其在文本叙事中追求的整体性与隐喻性甚至不会亚于一般意义上的经典文学作品。可以说正是《斗破苍穹》的出现将过去所追求的整体性文本彻底转化为多类型故事缀合的复合型文本。
当然,《斗破苍穹》叙事复合化并非一蹴而就的,也不能称作第一独创。这种转变是经过近乎十年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逐步形成的,也是中国网络玄幻小说逐步脱离欧美奇幻文学影响,重新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发现并创造性转化自身文化资源的过程。
如果说叙事复合化是对通俗小说章回体的某种创化的话,那么《斗破苍穹》在文本言语上去象征则是多少意味着当代网络玄幻小说在言语趣味上向传统通俗文学言语的复归。
在传统通俗文学的文本言语中,往往包含着煽情、说教等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又与通俗文学文本言语的“时尚趋向”“都市心态”息息相关11。简而言之,传统通俗文学的文本言语是大众能够通过直接的方式理解其意义的语言,并且在这种文本言语中又包含了作者对于大众伦理行为的某种非前沿性的倾向。比如张恨水在《春明外史》中叙述了陆无涯与学生陈国英之间、赵钿与陶英臣之间以及胡晓梅和时文彦之间自由恋爱的故事,而张恨水对由新文化运动而起的自由恋爱在小说中加了不少暗讽的言语,以此希望读者确认他的倾向性。易而言之,通俗文学的文本语言具有意义上的直白性与伦理上的保守性。
如此看来,结合前文中关于《斗破苍穹》去象征化的言语特征,即文本言语的直接意义就是文本的意义,显然是通俗文学文本言语的特质在当代网络媒介下的复归。尽管这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优点,但是正是这种文本言语的特质才能在更广泛的程度去接纳城市读者,尤其是当代网络社会中的都市读者。“一代人现在伫立于荒郊野地,头顶上苍茫的天穹早已物换星移,唯独白云依旧。孑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摧地塌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躯体。”12这是本雅明所预言的深陷于现代媒介体验的个体之处境。在这种处境之中的个体“住在大城市中心”,“已经退化到野蛮状态去了——就是说:他们都是孤零零的。那种由于生存需要保存着的依赖他人的感觉逐渐被社会机制磨平了”13。当代网络小说的阅读主体与本雅明的预言相比,有着更为孤独与破碎的处境。被“社会机制磨平”的大众既无力亦无暇在繁复的言语背后去寻找意义的隐喻,只有去象征化的言语才能告诉他们,怎样的做法才是更为有效,也才更适应日趋零散化的都市生活。
实际上,对传统通俗文学文本言语而言,《斗破苍穹》去象征化言语的创化之处在于它的内质并非传统通俗文学的“敦厚婉讽”,而是建立在当代都市主体的去象征化白描上。比如,主角萧炎虽然不断给人一种所谓“莫欺少年穷”的刚直气概,但同时也是一个随时转化,可以看风使舵、见机而行的人物。这种本质上的矛盾无论是在通俗文学创作还是经典文学作品中,都应力图避免。但是去象征化的言语,却成功地将这两种来回变迁的态度变得浑然一体,这种浑然性使当代都市主体自认为的生活处境,代表人的曲折是生活的纯然功利而非伦理,因此当小说以最直接的形式将这種当代主体矛盾呈现出来之后,主体反而获得直接认同。换句话说,萧炎的矛盾其实就是阅读主体的内在矛盾。
因此,可以说《斗破苍穹》去象征化的言语是当代处境中对传统通俗文学文本言语那种煽情说教的再生,也是当代都市社会和网络社会生活中重新发现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与伦理情趣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两者可谓殊途同归。
三、当代网络玄幻小说的
“通俗化”与“化通俗”
《斗破苍穹》通过叙事类型的复合化、描述言语的图像化、去象征化的言语系统等三条途径,完成了对传统通俗文学的“叙事进化”和“传统复归”。在这一过程中,《斗破苍穹》所展示出来的与传统通俗文学文本特征的异同,实际指向的是二者之间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即“继承—延伸”的关系。换而言之,以《斗破苍穹》为代表的当代网络玄幻小说一方面继承了现当代通俗小说的内核,是“通俗化”的;另一方面,它又对现当代通俗小说加以发展和延伸,有着独特的“化通俗”的审美取向。
要廓清当代网络玄幻小说与现当代通俗文学之间的“继承”关系,首先要考虑“通俗化”的问题。即何为“通俗”,它又有什么样的特点。进而,再通过将“通俗化”的特点与当代网络小说的特点进行对比,发现二者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继承关系。
一般而言,现当代通俗文学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延续,依托于大众媒体和市场运作,主要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类型化的世俗化阅读14。其特点主要有五个,分别是大众文化的文字表述,具有强烈的媒体意识,具有商业性质和市场运作过程,具有程式化特征并有传承性,是当代社会的世俗阅读。换而言之,这五大特征即为“通俗性”,而满足上述定义的小说则可被称为“通俗化”的小说。
大众文化的文字表述指的是通俗文学具有大众文化的全部特征。《斗破苍穹》通过描述语言的图像化和去象征化的言语系统,将语言的象征性意味加以消解,使其能够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实现了文本意义与直接意义的重合,成为大众文化最直观的文字表达。同时,在这种去象征化的言语系统的影响下,《斗破苍穹》在大众伦理层面,也展现出了以约定俗成的价值判断来作为文本中是非衡量标准的取向。
具体而言,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最深处是以社会公允伦理作为其文化核心,这一文化特征在《斗破苍穹》里也有明显的体现。小说开头时,云岚宗弟子纳兰嫣然来到萧家,凭借着强大的门派背景强行要求与萧炎退婚。而“被退婚”刺激的正是根治于中国社会的家族意识的“羞耻意识”层面,所以后来萧炎才会不择手段地修炼,为的就是能在三年之约后凭借实力“一雪前耻”。这种知耻后勇的价值判断,正体现了传统通俗文学约定俗成的大众文化内核。用范伯群的话来说,也可称之为是一种“符合民族欣赏习惯”15的表达方式。
作为网络玄幻小说,《斗破苍穹》的媒体意识无须多言,其本身的存在就是互联网媒介发达的产物。而李虎作为起点中文网的写手,在文学创作平台上进行签约连载的行为也十分清晰地昭示了其商业性质和市场运作。
在“世俗化的阅读”方面,《斗破苍穹》面向的是全体互联网用户,无论学生、白领还是其他社会阶层。这一点与传统通俗文学类似,同样是追求阅读的最大化,力图覆盖所有读者阶层。对于“程式化特征和传承性”而言,《斗破苍穹》亦表现出与传统通俗小说一样的类型化特征,其在起点中文网的分类标签中被定义为玄幻类小说。但值得注意的是,《斗破苍穹》的玄幻是叙事类型复合化后形成的新的种类。它摒弃了从中国传统的魔神、志怪、仙侠、武侠等话语体系中寻找表达词汇,企图用一种全新的“世界观”来建构文本世界,这无疑是对传统通俗文学程式化在某种程度上的突破,因而可以看作是在“通俗化”基础上的一种“化通俗”的表现。
“化通俗”指的是当代网络玄幻小说在“通俗化”的同时,又在某些审美特征上展示出与传统通俗文学的不同。即在和传统通俗文学“通俗化”内核保持一致的基础上,网络玄幻小说将新的“时代元素”渗入其中,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审美特点,并最终在“继承—延伸”的关系中,将“通俗化”发展成为“化通俗”。
如上所述,从程式化和传承性的角度来说,《斗破苍穹》的玄幻叙事也属于类型小说的一种,符合现当代通俗文学的通俗化特征之一。然而由于玄幻类型本身对传统类型有所突破,玄幻就在“通俗化”的基础上变成了“化通俗”。同样,在大众文化的文字表述层面上,《斗破苍穹》所展现出来的道德价值判断,除了以传统文化作为核心外,还夹杂着西方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以主角萧炎在迦南学院中所成立的学生组织“磐门”为代表,每当磐门有难时,几乎都是萧炎凭着个人强横的实力将危机迎刃化解。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情节,无疑是伴随着大量美国影视作品的流入而渐渐渗透在大众文化之中,并最终通过网络小说进行了文字化的表达。因此,借由将大众文化的融合与变迁进行文字表达,当代网络玄幻小说在传统的“通俗化”基础上,完成了一次“化通俗”的蜕变。
就媒体意识和商业运作而言,当代网络玄幻小说在保留原“通俗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涉及产业更加复杂,运行链条更加周密的商业系统。依托辐射更加广泛的媒体(互联网),网络玄幻小说不但颠覆了传统纸质阅读的范式,完成了屏幕阅读和移动端阅读的构建,还在传统通俗小说“文本—电视剧—电影”的商业运作外,发展出ACGN16产业链。单就《斗破苍穹》一部作品所旁涉的商业产物就有电视剧、动画、漫画、游戏等数种之多。此外,近年来更有逐渐火热的“IP”17产业兴起(例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庆余年》等影视剧的改编及相关商业衍生物的出现),使网络玄幻小说的商业运作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总而言之,当代网络小说的全新媒体性和商业运作模式为现当代通俗文学的“通俗化”开辟出了新的可能性,展示出了“化通俗”的独特商业潜力。
最后,在读者层面,当代网络玄幻小说和传统现当代通俗小说间也有一个明显的“继承—延伸”关系。一方面,网络玄幻小说继承了传统通俗小说追求读者最大化的诉求,将受众层面定为所有社会阅读主体;另一方面,它又对传统通俗文学中阅读主体作为“探索者”18的功能进行了超越,将当代阅读主体的经验感受融入文本之中,使得小说本身充满着“当代情绪”。《斗破苍穹》中,无论是萧炎不断重复的那句“莫欺少年穷”,还是他对绝对力量的不断追求,为了修炼不惜见风使舵,甚至不择手段,这其中所渗透的情绪无疑都与当代都市主体自认为的生活处境有所暗合,既揭示了阅读主体的“内在矛盾”,又戳中了阅读主体的“痛点”,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预期和幻想。而这种创作方式,无论是在张恨水还是金庸这些最出色的传统通俗小说作者的笔下都是从未出现过的。也正因此,当代网络小说在“世俗化阅读”层面上表现出比传统通俗文学更强的即时性情感交互能力,也是在“通俗化”基础上延伸出“化通俗”特性的一种体现。
《斗破苍穹》借由“通俗化”和“化通俗”的双重特性,与传统通俗文学间产生了“继承—延伸”的关系。同时,由于《斗破苍穹》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其他当代网络玄幻小说在创作和书写过程中也纷纷效仿,在有意无意中加深了“通俗化”和“化通俗”的交织融合。可以说,正是因为“通俗化”和“化通俗”双重特征的并置存在,当代网络玄幻小说才成为现当代通俗小说在网络时代的发展和延续。用汤哲声的话说,网络小说实际上就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延伸。它把当下的一些世界文化放进来,把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一些人物的心情和感情放进来,进行一些重新的组合,就变成了网络小说。因此网络小说既有传统性又有独特性。
【注释】
①对于奇幻小说概念范畴、类型与言语的研究,以法国的托多罗夫为先驱,故使用他在《奇幻文学导论》中所用的概念词语。奇幻文学最初被译介到中国大陆时,有译为“魔幻”的翻译。
②需要说明的这并非意指《斗破苍穹》是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玄幻小说,而是说由于《斗破苍穹》强大的影响力,最终使“玄幻”这一文学类型与仙侠类型作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区分,并且影响到了后续十余年的同类型网络文学创作的走向与类型划分。
③不应否认的是《诛仙》等小说的世界观也是原创世界观,但是不难发现对于世界观的表达无论是在概念的范畴,还是在小说内部设定上都使用的是中国传统魔神、仙侠、宗教等文化领域所具有的概念。这是与《斗破苍穹》之间十分重要的不同。
④起点中文网:https://book.qidian.com/info/1209977。
⑤图三药尘长者式的道骨仙风与正气凌然,与图二邪魅的药尘有着明显的不同。图一则又以少女漫画的男主人物形象出现,亦与图二、三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
⑥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68页。
⑦12本雅明:《启迪》,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99、96页。
⑧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21页。
⑨张蕾:《“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⑩兹维坦·托多罗夫:《奇幻文学导论》,方芳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第130、131页。
11陈建华:《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第413页。
13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151页。
14汤哲声:《何谓通俗:“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概念的解构与辨析》,《学术月刊》2018年第?期。
15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總序》,载《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南京出版社,1994,第1页。
16ACGN是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Novel(小说)的缩写。
17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即知识产权。
18玛丽-劳尔·瑞安在《故事的变身》一书中认为,“探索”是主体作为旁观者的身份与作品进行交流的模式,其对作品本身不会产生影响。
(于经纬、张学谦,苏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