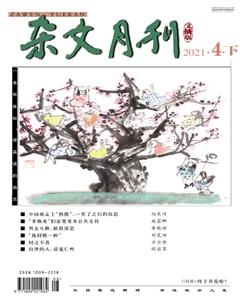“钱能通神”的背后
王兆贵
据《晋书·鲁褒传》记载,鲁褒因为世风贪鄙,于是便隐姓埋名而著《钱神论》。其中有云:“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馀,臣仆者穷竭而不足。”鲁褒的《钱神论》,也许是古代文字中,最早把钱与神联系起来的人。自此而后,“孔方兄”以及“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之类俗语,便在民间流行起来。
提起“钱能通神”,似乎只是一种戏说而已。若要仔细考证起来,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坊间闲话,而是源于唐人张固的一段历史笔记。
张固在这段笔记中说,宰相张延赏早就知道有一宗大案颇为冤枉,每每提及都扼腕叹息。待到他兼管全国财税收支时,就把负责此案的狱吏召来严加训诫,并责令说,此案拖延得已很久了,限你十日结案。
第二天,张延赏来到府衙办公时,发现桌上有一纸条:出钱三万贯,求你不再过问此案。张延赏大怒,催促狱吏要加大复查力度。第三天,纸条又来了:出钱五万贯。张延赏更为愤怒,命狱吏两日结案。第四天,又发现一纸条:出钱十万贯。事已至此,张延赏不由叹道,出钱至十万贯,可以买通鬼神了,没有不可挽回之事,我也不得不到此为止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张固所述“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比”。就是说,张固的记叙并非凭空虚构,有一定的可信度。正因为如此,张固的笔记文被收录入《新唐书》。
笔记中提到的张延赏,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名相张嘉贞之后,张延赏本人累任要职,由于政绩卓著,唐德宗时期被任命为宰相,继而兼掌朝廷赋税收支。
张延赏并不是一个贪财的昏官,其政声朝野皆有定论。他所以不得不接受“钱能通神”这一俗谚所隐含的魔鬼定律,是因為“出钱十万贯”者绝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其背后必然交织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凭他单枪匹马地与其斗法,殊无胜算不说,弄不好反误了卿卿性命,终究于事无补。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行贿往往不是简单的金钱往来,必然包藏有不可告人的用心。对于行贿者及其背后的利益共同体来说,不管行贿的代价有多高,但绝不会是亏本的投资。古代贿风为何难遏,是因为行贿能带来利益最大化;加之又有黑幕予以庇护,就会促使行贿者有恃无恐,铤而走险。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官场贪腐成风,显然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催生。行贿与受贿是官场腐败的两个共同要件,各取所需,相互利用。受贿与行贿是共同犯罪的对偶关系,有行贿才会有受贿,有受贿必有行贿;行贿者或许曾受人所贿,受贿者转而贿赂他人。不论是金银财宝贿赂,还是雅贿、色贿,说到底都是利益输送和交换。至于说盗用国库、假公济私、求职买官的行贿,就更加误国害民。
在我国历史上,将以财物买通他人的交易称作“赇”,意即贿赂。不论是“请赇”“受赇”还是“行赇”,均被列为犯罪。在我国古代,那些明智的君主和御史,在查处受贿案的同时,会将行贿者及其背后的利益共同体绑定该案一并查处,就连朝廷忠臣和皇亲国戚也不放过。据《尚书》记载,凡是向官吏馈送财物和接受左右亲信委托说情行私者“其罪惟均”,即行贿人员与受财枉法官吏同罪。《秦简》记载,“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贿赂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史记》记载,灌婴的孙子灌贤,因犯行赇罪,被剥夺了封地。《唐律》规定:“诸有事以财行赇,得枉法者,坐赃论;不枉法者,减二等。”《清史稿》记载,“例定以财行赇,及说事过钱人,审实计赃同科”。
时至今日,国家司法部门和纪检监察机构也正在不断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力度,坚持行贿与受贿统筹查办,严厉惩处主动行贿、多次行贿、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让行贿的黑幕大白于天下,形成强烈震慑的连锁效应,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