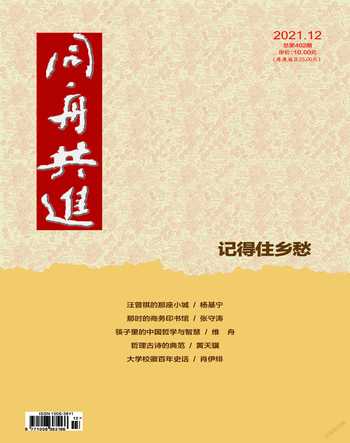张爱玲:临水照花的美食情缘
冯远臣
张爱玲给世人的印象通常是:微仰着头,扶着腰际,眼尾斜斜地扫过来,高傲孤绝似乎远隔于俗世之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对食物却情有独钟,她似乎把大部分的热情都留给了食物。
若说她是民国最走红的小说家可能尚存争议,不过若说她是民国最不挑剔的美食家,可能没有人会反對。民国文人的口味虽然变得多元,但主轴还是离不开中国味,人们留下的文字,多是千篇一律的中式料理。张爱玲的饮食习惯和她的穿搭做派一样颇为大胆,显得别具一格——当其他人还在吃天津饺子,饮中式黄酒时,张爱玲已经在用奶油刀将奶油均匀涂抹在英式司康松饼上了。
回望她的饮食经历,我们会发现,从德式吉士林面包到本帮菜“红烧划水”,甚至是平民小吃臭豆腐、油条,张爱玲几乎都有所涉猎,堪比今日的“美食博主”。
“报刊上谈吃的文字很多,也从来不嫌多。中国人好吃,我觉得是值得骄傲的,因为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艺术。”这段话出自张爱玲的散文《谈吃与画饼充饥》。对于吃,张爱玲的立足点是很高的,她将其提升到生活艺术的高度——吃不仅仅是填饱肚子,虽然也是相当一部分的终极目的,而吃出“艺术”来,“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了。
1920年,随着大清走入历史,那些晚清贵族也失去了依靠和炫耀的资本,就在那一年中秋,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栋房子,为清末重臣李鸿章所留。
张爱玲家世显赫,爷爷张佩纶是清末名臣,奶奶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
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又遭败绩,大清国被迫签下屈辱的《马关条约》,李鸿章因此成了民族罪人,门庭冷落。不久后,李鸿章去世,一年多后,张佩纶也抑郁而终。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女儿李菊耦嫁给张佩纶,李家的仆人也把饮食口味带到了张家。 张爱玲对安徽美食很熟悉,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样:合肥丸子与粘粘转。
所谓“合肥丸子”其实就是糯米圆子。做合肥丸子时,先要煮熟一锅不硬不烂的糯米饭,凉了后,捏成一个个小团,把调好的肉糜放进米团里捏拢,大小跟汤圆差不多,然后把糯米团放在蛋汁里滚过,再放进油锅煎熟,其外皮金黄酥脆,丸心滋润鲜美。这道菜唯有张爱玲的奶妈何干会做,何干就来自合肥乡下。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中回忆说,姐姐喜欢吃合肥丸子,连带着全家人都爱上了这道菜。
另一种让张爱玲难忘的安徽吃食是“粘粘转”,它是安徽无为的一种特色小吃。李菊耦嫁到张家后,李鸿章将无为的田产赠给她作为陪嫁。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张爱玲忆及姑姑老想吃一种叫“粘粘转”的食品,它是用青麦粒做成的,城里人可以称之为美食,但在乡下就不能被称为美食了——那可以称得上是“救命粮”。
饥荒年间,麦子成熟前的几个月里,乡民们早已把过冬储备的粮食吃尽了,还没有等到麦子成熟,为了填补上顿不接下顿的饥饿,便将麦粒割下来,放在石磨里一磨,青绿色的麦浆流进预置的木桶,再把麦浆倒进滚烫的开水里,一搅合,粘稠适度的新麦粥就算做好了。
但张爱玲谈的,是另一种更富情趣的吃法:“田上人家捎来的青色麦粒,就是没有成熟饱含浆汁的青麦粒,下在一锅滚水里,满锅小绿点子团团急转……”“小绿点子”就是剥去麦壳的青涩麦粒,直接下锅煮来吃,而不经过磨子碾磨。
张爱玲两岁那年,父亲张志沂通过民国交通总长的关系,在津浦铁路谋得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务,遂举家由上海迁往天津。
在天津的童年,大多与吃有关。小时候的张爱玲煞是可爱,她跟着大人到戏园子看戏,落下了满地的瓜子壳;夏日坐在洋房的院子里,“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背诵《孟子·梁惠王》下篇的时候,里面有一句“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獯鬻”(xūn yù,古指匈奴)这两个字最难写,也最难认,在佣人的帮助下,小张爱玲灵机一动,很快就想到了“獯鬻”的谐音就是“熏鱼”。能顺利地背诵这么古典深奥的句子,或者每天认识一两个字的时候,得到的奖励就是两块绿豆糕。
绿豆糕是著名的京式四季糕点之一种,它由绿豆粉、白砂糖、糖桂花与适量清水按一定的规格混合后蒸制而成,色泽浅黄,吃起来清香绵软,味道有豆沙、枣泥和玫瑰几种,是大人哄小孩子的美食。
张爱玲喜欢吃软、嫩、香、甜的食物,松子糖、云片糕、桂花蒸、酸梅汤、生煎馒头、糖醋小排是她的最爱,她在《童言无忌》中写道:“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
住校期间,宿舍附近有很多小商贩卖各种小点心,摊位在校舍周围凌乱地搭建起来,高声嘈杂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大饼油条同吃,由于甜咸与质地厚韧脆薄的对照,与光吃烧饼味道大不相同,这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有人把油条塞在烧饼里吃,但是油条压扁了又稍差,因为它里面的空气也是不可少的成分之一”。凡烧饼,必须得有芝麻附着其上,一口咬下,烤过的芝麻在唇齿间香气四溢,何等满足。
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张爱玲还提到在天津吃过的“鸭舌小萝卜汤”和“腰子汤”。“鸭舌小萝卜汤”是天津的一道特色菜,中医认为鸭舌有温中益气、健脾胃、活血脉、强筋骨的功效。张爱玲吃鸭舌,有她的经验——先咬住鸭舌头根上的小扁骨头,然后再“往外一抽抽出来,像拔鞋拔”。“汤里的鸭舌头淡白色,非常清腴嫩滑,到了上海就没见过这样的莱”。对鸭舌小萝卜汤,张爱玲用了“馋涎欲滴”来大加赞美。可是,今人查遍各种天津老菜谱及民国以来文化名人关于天津美食的随笔,均不见关于“鸭舌小萝卜汤”的记载,或许这道菜已失传,或许这是当年张家佣人们的吃法,也未可知。
张爱玲天津记忆中的另一种美味是腰子汤。即一副腰子与里脊肉、小萝卜同煮,里脊肉女佣们又称“腰梅肉”,大概是南京话,张爱玲一直不懂为什么叫“腰梅肉”,又不是梅干菜炖肉,多年后才恍然悟出是“腰眉肉”。腰上两边的一小块地方叫腰眼,腰眼上面一寸左右就是“腰眉”了,百姓生活里这语言上的神来之笔,令张爱玲深受触动,吃食中也可长不少学问。
南移后的张爱玲,上海曾是她活动的主要场所。
八九岁的时候,张爱玲的味觉愈发灵敏,有一次喝鸡汤,刚吃了一口就吃出了药味。家里人都说没有什么。母亲差人去问厨子,厨子回说这只鸡是两三天前买来养在院子里的,看它垂头丧气仿佛有病,便喂它吃了“二天油”——一种类似万金油一类的油膏。母亲虽没说什么,可张爱玲知道母亲对她的诧异与注意,心里得意洋洋,觉得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
有一段时间,张爱玲常去对街的舅舅家吃饭,每次母亲都会带去一份清炒的新鲜苋菜:“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同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乎乎的苋菜香。”
因为父亲不务正业,四岁时,张爱玲的生母就出走了,继母对她经常疏于照顾。来到上海,张爱玲初次尝到了生母亲手制作的菜肴,虽然当时经济拮据,远不如之前世家大族的风范,但张爱玲不介意,因为在那里,她感受到了慈爱与包容。1955 年,张爱玲移居美国,一天到唐人街买菜,看到店铺外陈列的大把紫红色的苋菜,不禁怦然心动,大概这道简单的家常菜,勾起了她对母亲温暖的回忆罢。
在上海的时光,是张爱玲一生中少有的平静时期,她文思泉涌,写下了许多著名小说,一时名声大噪。她享受成功、快乐的同时,仍不忘把“吃”记录下来。
张爱玲酷爱甜点,民国时期的上海,可说是全世界美食的聚集地,西式甜点多不胜数:“这司康松饼的确名下无虚,比蛋糕都细润,面粉颗粒小些,吃着更‘面’些,但是轻清而不甜腻。”“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起士林是天津的品牌,上世纪40 年代末,起士林到上海开设了分店,怀念家族荣光的张爱玲就变成了起士林的常客。她最爱一种方角德国面包,外皮厚脆,中心微湿,是“普通面包中的极品,与美国加了防腐剂的软绵绵的枕头面包不可同日而语”。
“老大昌”是俄国人在上海开的一家面包店,离张爱玲就读的圣约翰大学很近,课余饭后,是她最喜欢光顾的地方。她爱吃这里的十字面包,这种面包很小,呈半球型,上面略有点酥皮,底部嵌着一只半寸宽的十字托子,“这十字大概面和得较硬,里面搀了点乳酪,微咸,与不大甜的面包同吃,微妙可口”。张爱玲对这种俄式面包异常迷恋,有一回在香港的一条僻静小街上,她忽然发现一家“老大昌”,狂喜地翻找,却只发现寥寥几只两头尖的面包或扁圆的俄国黑面包。她买了一只俄国黑面包,回家发现硬得像石头,费了好大劲切开,“迎接”她的是里面的一根棕红色长发。
后来在美国,又听到“热十字小面包”的名字,她再次买下,以为就是老大昌的那种面包,但见到的却是粗糙的小圆面包,上面用白糖划了个细小的十字,尝过当然是失望,“即使初出炉也不是香饽饽”。
在张爱玲的记忆中,老大昌还有一种肉馅煎饼,名叫“匹若叽”,表面金黄,软软的像布袋的样子。因怕油煎食品不易消化,她并没有尝试。后来张爱玲在日本时,到一土耳其人家中吃饭,尝到了家庭自制的匹若叽,她觉得味道非常好。
飞达咖啡馆里的香肠卷,也曾在张爱玲的味蕾上开出花来。某日,好友炎樱坐在张爱玲公寓的阳台上,拿着相机随意拍著,边拍边问:“如果离开上海,你最想念的是什么?”张爱玲脱口答道:“飞达咖啡馆的香肠卷。”说这话时,张爱玲一手叉腰,头微微扬起,淡然的神情中夹着几分傲然。炎樱按下了快门——这就是张爱玲的那张经典照片。
垂暮之年的张爱玲,孑然一身在美国,那时的她更偏爱素食。她记住了一个营养学家说过的话:“鸡蛋唯一的功用是孵成鸡。”这都是胆固醇惹的祸,一个曾经随心所欲的人,不得不改变她之前的饮食习惯——戒掉绿豆糯糍、南枣核桃糕,改吃葱油饼,多喝豆浆、牛奶。就像她在《童言无忌》里说的:“我和老年人一样,喜欢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菜、酱萝卜、蛤蟆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
张爱玲丰富敏锐的内心世界,鲜有人理解,但在一次次与美食的碰撞中,她心底的柔软之处被触及,那些沉淀的记忆被唤起,逐渐变得清晰。也许她品的不光是美食,亦有人生中说不尽的百般滋味。
(作者系文史学者)